道教经典里“试”的故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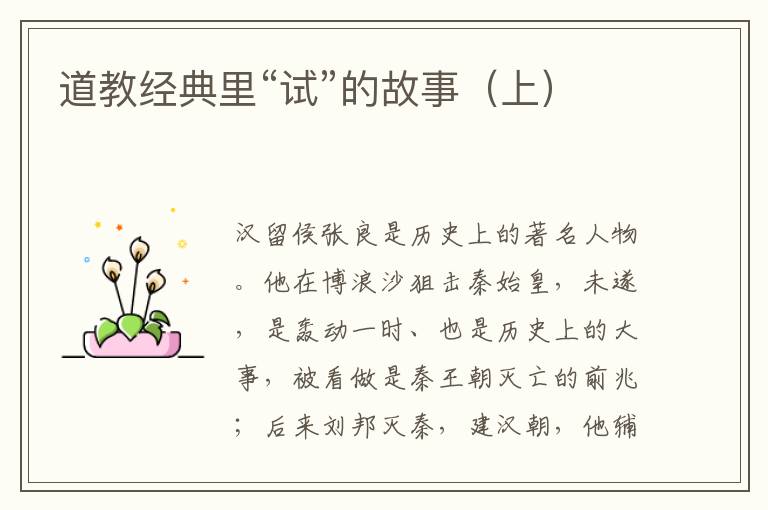
汉留侯张良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遂,是轰动一时、也是历史上的大事,被看做是秦王朝灭亡的前兆;后来刘邦灭秦,建汉朝,他辅佐有功,封留侯,显示他是智勇双全的能臣。而他后来又被纳入仙传,在道教经典里被说成是道教祖师天师张道陵的祖先,并被附会为道教经典的一位制作者。
道教史上的“造仙”活动中,许多真实历史人物被“仙化”了。这是“造仙”的途径之一。这样创造出来的神仙有些有一定的史料“根据”。如张良被“仙化”,就是基于司马迁《史记》里《留侯世家》里一段记述,写他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失败之后:
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尝闲从容步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縠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本来司马迁作《史记》,遵循“实录”原则,在秦皇、汉武《本纪》、《封禅书》等篇章里对神仙迷信大加挞伐。书中如这种神秘不经的记载是很少见的。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权威作者、权威著作的记述,后来张良被“仙化”、成为神仙传里的人物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段记载本意是表现张良当年虽然屡经屈辱挫抑却矢志不移、虚心受教、求得兵书态度之诚笃,终于感得黄石公授予《太公兵法》,使他后来得以辅佐刘邦取天下。张良活动在秦汉之际,其时道教还没有形成,后来被当做神仙来崇拜,这当然是“造仙”人们的“创作”。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里关于张良这二百余字记述,又给中国叙事文学、特别是道教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主题类型”。所谓“主题类型”,本来是指民间故事叙事主题表述上一定的情节结构模式。例如“中山狼”故事,救助坏人、反得恶报;或宗教主题的,如观音灵验故事,遇到水、火、刀、兵之类灾难、念《观世音经》或称观世音名号,立即得救,就都提供一种相对稳定的叙事结构。这样的“主题类型”可以衍化出种种变形,形成一种模式,被运用在叙事作品创作之中。有关“主题类型”的研究是十九世纪欧洲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开创的。相关研究从民间文学延伸到一般叙事文学创作领域。而由于民间文学创作中的“主题类型”会体现一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特征,相关研究在深层次上又就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遂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比较学派研究的重要内容[外国人的研究成果在我国发挥较大影响的有德国人艾伯华(Woifram Eberhard)1937年发表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有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的王燕生、周祖生中译本]。在我国,上世纪前半叶顾颉刚、钟敬文等前辈学人曾把“主题类型”观念引入民间故事传说的研究之中,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关于中国叙事文学主题类型研究具有总结意义的早期成果有钟敬文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932年刊布在《民俗学集镌》第一册《民俗学专号》;近年有宁稼雨编著《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所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道教养炼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在是否能够得到道行高超的“明师”的指导;相应的另一个决定因素则是学徒是否能够对“明师”绝对地信任。只有这两个条件“师资道合”,才能够达成师资授受的目地。在《史记》描述的张良的这段经历里,黄石公就是“明师”,张良是有心求道的学徒,黄石公对他加以考验,通过了,授予他经典,张良遂得以佐汉立大功。这种故事情节,后来即演变为一种“主题类型”,成为编纂仙传、创作道教文学作品的一种结构模式,遂创作出许多明师“试”弟子的生动故事。它们成为师资传授的样板,在宣教中发挥作用。
道教养炼中“试”的意义道教养炼,无论是求仙还是炼丹本来都是妄诞不经的,不可能通过事实验证。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个人修持,还是对外弘传,树立绝对的信仰心也就十分重要。编撰仙传本意是要给人树立求仙、成仙的榜样,也就要引导人树立坚定的信仰心。那种通过烦难艰苦的“試”而始终矢志不移、终于得道成仙的情节也就非常适合表达这种主题的需要。在这类神奇不经的故事里,所描写“试”之严酷往往匪夷所思,极尽夸饰之能事,非常人能够忍受;或布下重重疑阵,让人难以做出“正确”决断,不能不产生疑问而作罢;往往相对照地表现那些一心向道的弟子却能坚定、盲目地尊从“明师”指引,不离不弃地追随他,终于达到成仙的目的。这种“主题类型”的故事遂成为生动、感人而又能够达到诱人效果的作品。而这些故事里所表现的那种历经考验而无怨无悔、忠于理想目标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又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道教,通俗地说乃是教人成仙的宗教。教人成仙,首先需要答复的是平凡人是否能够成仙这个疑问。这就是道教思想史上所谓“神仙是否可以学得”的疑难问题。三国时诗人嵇康(224—263)是主张成仙要“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养生论》)的。就是说,他认为成仙不能通过“积学”即个人养炼达到,只有“特受异气”即那些具有先天禀赋的特异气质的特选人物才能够成仙。在他之后不到一个世纪、东晋著名道教理论家抱朴子葛洪(283—363)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明确主张神仙“可以学致”。这两种观点的不同反映了魏晋时期道教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实际人能否成仙、什么人能够成仙不只是教理层面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复基于对于“人性”的不同认识,反映平凡人是否同等地具有成仙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不同观点。神仙可学的观点内含着人性平等观念,显示对人性的本质的绝对性与超越性的肯定。这种观点对更广大信众开放了成仙的大门,也就有利于道教的弘传。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道教大发展,也正是佛教大乘涅槃佛性学说输入中土并广泛传播的时期。涅槃佛性学说主张人人“悉有佛性”,即使是断了善根的“一阐提”(即断了善根的极恶之人如毁佛、杀父母者)也有佛性,也能够成佛。道教的神仙“可以学致”的思想显然接受了这种佛性学说的影响。佛教和道教思想的交流促进各自思想的发展,从而给中国思想史贡献了宝贵内容,这是一个例子。
既然神仙“可学”,学仙又要有“明师”教导,弟子要绝对遵从“明师”教导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前面提到的葛洪是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人物。他在所著《抱朴子内篇》(道教发展到东晋时期无论是教理层面还是养炼实践层面都已成熟,《抱朴子内篇》对此前道教教理发展做出系统的总结,对于道教信仰的两个基本内容——神仙信仰和金丹信仰做了详密充分的论证,从而给道教进一步扩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乃是道教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有王明的《校释》本)里充分地发挥了神仙“可以学致”教理,指出:“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抱朴子内篇》卷二《论仙》)即是说,是否能够长生成仙,先决条件在“志”、个人的志趣,即达到成仙目标的坚定的信仰心。树立起信仰心之后,他进一步提出要“勤求”,即要精进努力,不懈地追求。《抱朴子内篇》里有专门的《勤求》篇。求什么?他指出:对于神仙“颇有识信者,复患于不能勤求名师”。这是说勤恳寻求的对象是“明师”。他进而又要求,得到“明师”就要绝对地信任、服从,“负笈随师,积其功勤,蒙霜冒险,栉风沐雨,而躬亲洒扫,契阔劳役。始见之以信行,终被试以危困,性笃行贞,心无怨贰,乃得升堂以入于室”(《抱朴子·极言》)。这就提出了求道成仙的成系列条件:立志、勤求、得到“明师”,信任“明师”。只有满足这一系列条件,求仙才有可能成功。而且道教发展早期,如所有宗教一样,基本形态是信徒召集弟子宣教,又往往是秘密传授的。这种做法作为传统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如《勤求》篇里指出的:“其至真之诀,或但口传,或不过寻尺之素,在领带之中,非随师经久,累勤历试者,不能得也。”这是说,无论是口头的经诀,还是书写在绢素上的经典,都要靠“名师”来给弟子传授,因此建立师资间绝对信任的关系也就成为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
“明师”在接受弟子、传授道法之前,当然先要考察弟子资质:对方是否为可教之材,立志是否坚定,对自己是否信任,等等,这就必须对弟子加以严格考验即“试”。这样,在记载传授仙道的故事里,就有许多师资授受间“明师”“试”弟子的故事。而从写作角度看,这些故事则体现为统一的“主题类型”。这些故事成为师资授受的典范事例,也是指导后人修道,特别是指引、告诫学徒必须树立绝对信仰心的教材;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成为有一定意义与情趣的文学作品。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