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运用《补叙的表现形态》文学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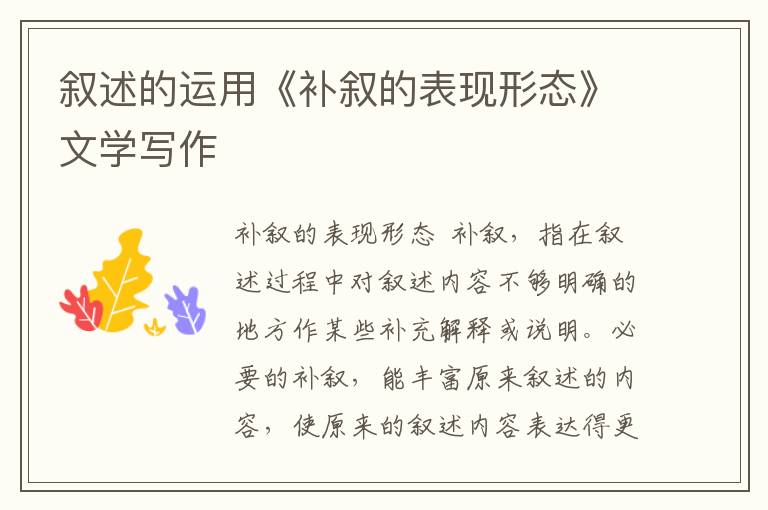
补叙的表现形态
补叙,指在叙述过程中对叙述内容不够明确的地方作某些补充解释或说明。必要的补叙,能丰富原来叙述的内容,使原来的叙述内容表达得更细致、完整。运用补叙,使文章结构完整,行文跌宕起伏,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从而能更好地表达主题。
鲁迅的《五猖会》叙述了作者幼年时因要去看五猖会而兴高采烈,忽然父亲叫他背书的情形,中间插入:“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这段话补充了原来叙述中对上学、读书种种情况的不足,使原来叙述的内容更易于读者理解。
王蒙的《手》,正是运用了必要的补叙,才使得故事情节有了连贯和完整的发展。作品里写高级领导接待一位死者的遗孀,他对死者并无印象,而死者的遗孀却虔诚而激动地一再道谢。领导先是担心死者的遗孀上门找麻烦,后听到来者只为了道谢并无它意,才将态度转为同情。但他送走那位遗孀后仍然想不起死者是谁。如果故事写到这里就让人一头雾水,莫名其妙了。然而,领导在5天后乘车被一个坑洼颠簸时,终于想起来了:
两年前,他担任厅长的时候,去省委开会,随着一个颠簸,车抛锚了。司机说,要半个小时才能叫另一辆车来。他没有法子,便走入附近的一个居民楼。恰好他的身患不治之症的一位下属的下属住在这所楼里。他去看望了他。他看到一个苍白的蓬首垢面的病人,因他的到来而显出笑容。他永远忘不了病人从被子下面伸出的细瘦枯黄带汗的手。那手握他的时候,竟比他的健康高贵的手有力得多。回家后为洗手打了三遍扇牌香皂。他没有说是因为车的引擎出了毛病。他没想到这个病人又活了那么长时间。
没有这段补叙,故事就不完整,“手”的象征意义就无从写下去了。由于有了这段补叙,作者写出结尾这段话就合情合理:“他不知道应该自责还是自慰。需要一种古板的诚实、冒着刺伤善良者的危险,退回他不配得到的感激?还是就这样接受了一个人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刻骨铭心的感情?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觉得掌心发热,确实有许多待援的手伸向了他。”这段话不仅对补叙的内容有针对性,也使作品的立意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再看台湾作家侯博仁的作品《戏正上演》:
“快!快来买!日本新进产品,一个五百,一个五百。”一个胖胖生意人在地摊上声嘶力竭地喊着,并且手里还不断地反复操作,最后重重地往地上摔,然后说:“这种东西不怕摔,不怕踩,什么都不怕。”他拿了几个分给前面的观众,“看一看,不一定要买。”
“太贵了,我那天在中坜,四百就买到了。”一个青年人看了一下,摇着头。
“少年仔,再仔细看看,这是日本货,不是杂牌货!”生意人一直逼近他。
“错不了,一模一样。”他一讲完,原先有拿东西看的,都放了回去。
“好!你拿来,如果一样,一个一千向你买,有多少,买多少!”生意人非常不悦。
“这可是你说的,大家都听到了。”他把烟丢掉,骑了车子就走。
人越来越多,大家都不想走,大家都想看戏。不一会儿,一声刹车,他走了进来。
“你们看看一样不一样?”他拿出了几个给观众验证,生意人也拿了一个。生意人无话可答。然后,他对着大家说:“我们做生意的,讲求的就是公道,就是实在……你说一个要一千元向我买,相信各位都听到了,我这边有一百个。”他把东西搬到前面,“放心,我不会这么狠,只卖你五个,算做一次小小警告。”观众一齐为他喝采,他拿了钱,整理好东西,准备要走。可是,又停了下来。“既然东西都带出来了,我也不想再拿回去,如果各位要,一个三百,要多少,拿多少。”观众围上来,他一手收钱,一手交货找钱,非常忙碌。“人爽就好,人爽就好,人爽……”他反复地讲。
夜已深,观众走了,剩下他们二人。
“今天卖了多少?”生意人问。
“你五个不算,共卖八十三个。”年轻人笑着,然后问,“明天到哪里?”
“新竹。”
作品的结局出人意料,这里也是采用了补叙。可见,补叙与插叙有所不同:补叙可以终篇,而插叙不能终篇,插叙后必须继续顺叙下去,此为二者在形式上的差异。在内容上,插叙插入的是基本事件发展之外的有关情况,而补叙补入的则是基本事件发展之中的有机环节,是中心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
【原典阅读】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
福克纳
一
艾米莉·格里尔逊小姐死的时候,我们全城都去参加她的葬礼:男人们出于一种对倒塌的纪念碑不无敬意的眷恋,女人们则大半为了好奇,想看看她那所房子里面的究竟。至少有十年了,除去一个兼作园丁和厨师的老仆,那里面没人窥见过一眼。
那是座很大的方形木房子,一度曾漆成白色,装点着七十年代凝重典雅风格的圆顶、尖塔和刻有涡形花饰的阳台,坐落在一条曾是本城名门世族聚居的大道上。但是汽车修配厂和轧棉作坊日浙扩展过来,甚至把这一带那些可敬的姓氏都淹没了;只剩下艾米莉小姐的房子,撑着它那衰败的风姿,高踞于一辆辆运棉车和加油站之上——一群现世宝中的现世宝。而现在艾米莉小姐也参加到那些可敬姓氏的代表里去了,他们躺在香柏森森的公墓里,躺在那些在杰弗逊战役中倒下的北方联邦和南部联盟的战士们一行行佚名坟墓中间。
活着的时候,艾米莉小姐一直代表一个传统、一种责任和负担,是这个城市世世代代必须承担的一种义务。那是从一八九四年某一天开始的,当时的市长萨特利斯上校——就是他制定了黑人妇女不系围裙不得上街的法令——豁免了她的税务,从她父亲死的时候起,直至永久。这可不是说艾米莉小姐竟肯接受施舍。萨特利斯上校编了个绕弯的故事,听起来好像是,艾米莉小姐的父亲曾借给本市一笔钱,因而本市公事公办,选择这种方式来偿还。只有萨特利斯那一代而且那么副脑筋的男人才编得出这种故事,也只有女人才会相信它。
到思想比较新的下一代当上市长和市参议员的时候,这种安排就颇惹起些小小的不满。一过了年,他们就寄给她一张税单。二月到了,却不见回音。他们给她写了封公函,请她得便到市行政司法官办公室来一趟。又过了一个星期,市长亲自写信给她,提议前去拜访或派车去接,得到的回答是一张纸条,用褪色的墨水,纤细流畅的笔体,写在一种古色古香的信纸上,大意是说她根本不再出门。税单也夹在里面,却只字未提。
他们召开了一次市参议会特别会议。一个代表团登门造访,叩动了那扇自从八年或十年前她停止教授瓷器画课程以来还没有一个客人走进过的大门。他们被那个黑人老仆请进了一间阴暗的大厅,大厅里有座楼梯升入更浓重的暗影中。屋里发出灰尘和那种经年不用的房屋的气味——一种窒人的、潮湿的气味。那黑人把他们领进客厅。客厅摆设着笨重的皮面家具。那个黑人打开一扇窗户的百叶,他们可以看到家具的皮面部开裂了;他们坐下的时候,一股轻尘从他们臀部下面懒懒升起,细小的尘埃在那道仅有的阳光中浮动回旋。壁炉前褪色的金框里立着艾米莉小姐父亲的粉笔画肖像。
她一进屋,他们都站了起来,这是个全身穿黑,矮小、肥胖的女人,一条细细的金链垂到腰际,消失在腰带里,拄着一根金头已经失去光泽的乌木手杖。她骨架纤小,恐怕正因为这点,在别人身上刚算得上丰满,到她身上却显得肥胖不堪。她看上去虚浮臃肿,活像在死水里浸久了的尸体,白生生的。她的一双眼睛深藏在脸上肥厚的皱褶里,就像嵌在一团发面里的两小块煤炭,当客人们陈述来意时,这双眼睛从一个个客人的脸上移过。
她没有请他们坐下。她就这么当门一站,静静地听着,直到讲话的人终于磕巴一下顿住了。接着他们只听到那只看不见的表在金链的末端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
她的声音干巴巴、冷冰冰。“我在杰弗逊没有税。萨特利斯上校给我解释过。或许你们当中哪位能设法看看本市的档案,你们就全清楚了。”
“但是我们看过了。我们就是市政当局,艾米莉小姐。您没有接到由市行政司法官亲自签署的通知吗?”
“我收到了一张条子,是的,”艾米莉小姐说,“或许他自命为行政司法官……我在杰弗逊没有税。”
“但是并无案可查,您明白。我们必须按照……”
“去问萨特利斯上校,我在杰弗逊没有税。”
“但是,艾米莉小姐……”
“去问萨特利斯上校。”(萨特利斯上校死去已经快十年了。)“我在杰弗逊没有税。托博!”那个黑人出现了。“送这些先生们出去。”
二
就这样她大获全胜,打得他们人仰马翻,正像三十年前在关于臭味那一仗中把他们的父辈打得人仰马翻一样。那是在她父亲死去之后两年,也就是她的情人——我们曾相信会娶她的那个男人——抛弃她之后不久。父亲一死,她难得再出家门;情人走后,人们几乎见不到她了。有几位太太曾不揣冒昧,前去拜访,却吃了闭门羹,而后那房子里还有生命的唯一迹象就只是那个黑人——当时还是个年轻人——挎着个买菜篮子出来进去。
“就好像男人——甭管什么样的——也能管好厨房似的。”太太们都说,所以当臭味越来越厉害时,她们并不感到惊讶。这臭味在粗鄙杂乱的世界和孤高倨傲的洛利尔逊家族之间成了又一种联系。
一个邻居,是位太太,向市长,八十岁的史蒂文法官抱怨。
“但是您要我怎么办呢,太太?”他问。
“怎么办?通知她不许再放这种臭味,”那女人说,“难道就没有法律了?”
“我相信没有这种必要,”史蒂文法官说,“大概是她那个黑人在院子里弄死了一条蛇或者一只耗子。我会警告他的。”
第二天,又有两个人来抱怨,其中一个男人说得很委婉:“对这事咱们真得想点办法,法官。我是世界最不愿打扰艾米莉小姐的人,不过咱们实在得想点办法。”当晚全体市参议员聚会——三个花白胡子和一个年轻些的,一个正在兴起一代的代表。
“再简单不过了,”那个年轻的说,“通知她把房子打扫干净。给她一段期限,然后如果她还不……”
“活见鬼,先生,”史蒂文法官说,“难道你能指着一位太太的鼻子说她臭气熏人吗?”
于是第二天夜里,午夜过后,四个男人溜过艾米莉小姐的草坪,像贼一样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沿着砖砌的墙基嗅个不停,在地窖口,一个人把手从背在肩上的口袋里掏出来做了个标准的播种动作,他们撬开地窖门,把石灰洒在那里和所有的棚舍中。他们再次穿过草坪时,一个原来黑着的窗口亮了,艾米莉小姐当窗而坐,灯光在她身后,她挺直的身躯纹丝未动,恰似一座泥胎。他们蹑手蹑脚溜过草坪,钻进街边洋槐树的暗影里。一两个星期后,臭味消失了。
那正是人们真正开始为她惋惜的时候。城里的人还记得老韦艾特夫人,她的姑婆,最后怎样完全疯了,大家认为格利尔逊家的人把自己的身价抬得过高了点。没有一个年轻男人能让艾米莉她俩看上眼。长时间里,一想到这家人,我们脑海里就有幅活生生的画面:背景上是身材苗条、浑身素白的艾米莉小姐,她父亲摆开架式的黑色身影在前景上,他握着根马鞭子背朝着她,洞开的前门给他们充当了画框。所以到她年近三十依旧孑然一身时,我们虽说不上高兴,却也觉得出了口气;就说有点家传的狂傲,那些结婚机会将是真个送上门来,她也不会一概拒绝的。
她父亲一死,风儿就传开来,说那所房子就是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就某种意义说,大家挺高兴。终于他们也能可怜可怜艾米莉小姐了。只剩孤单单一个人,再加一贫如洗,她也成为凡人了。现在她多少也会尝到为了几个大钱的得失,激起一阵兴奋或一阵失望的古老滋味了。
她父亲死的第二天,按照我们的习俗,所有的女土都准备前去拜访,表示吊唁并帮些忙。艾米莉小姐在大门口迎住了她们,装束如常,脸上没有一丝忧伤。她告诉她们说她父亲没死。一连三天她都这样,不管是牧师们还是医生们来访,竭力劝说她,要她允许他们把尸体入殓。就在他们几乎要诉诸法律和强力的时候,她顶不住了,他们赶快埋葬了她父亲。
那时候我们不认为她疯了。我们相信她这样做也是不得已。我们记起所有那些被她父亲赶走的年轻人,并且我们知道,一切都荡然无存,她想要牢牢抓住那个夺去了她一切的人,也是人之常情。
……
……
五
那黑人在前门口迎着第一批太太们并把她们领进去,一路她们压低了嗓子嘁嘁喳喳好奇的目光滴溜乱转,接着那黑人就消失了。他照直穿过那所房子出了后门,就再没见到。
两个表姐妹随即赶到了。第二天她们举行葬礼,满城人都来看艾米莉小姐,她躺在买来的一大堆鲜花下,挂在棺椁上方的那张父亲的粉笔画肖像意味深长地沉思着,太太们低声讲话,阴阴惨惨;一些老人——其中有的穿着刚掸刷过的南部联盟军制服——在门廊里和草坪上,谈论着艾米莉小姐,似乎把她当似他们同时代的人,相信曾和她跳过舞,也许还向她求过爱。像老年人通常有的那样,他们混淆了岁月的次序;对他们来说,整个过去不是一条越走越窄的道路,而是一片宽广辽阔的草原,那儿还没有暮年隆冬的足迹,只是最近十年来一段狭窄隘口似的路程才把他们同过去分割开了。
我们早已知道顶楼上有间屋子足有四十年没人觑过一眼,而且非得破门而入才行。他们一直等到艾米莉小姐体体面面地落了葬,再来打开它。
那股破门的猛劲儿震得整间屋子灰尘弥漫。一层薄薄的、气息辛辣的尘埃,像坟里的墓布,覆罩着这间陈设得又像新房的屋子各处:覆罩在褪色的玫瑰色窗帘和玫瑰色的灯罩上,覆罩在梳妆台上,在摆放得整整齐齐的精致的水品饰物上,在暗无光泽的男用银质梳妆具上,那银色已经晦暗得连上面组成图案的字母都看不清了。在梳妆台上那些什物中间,放着一个硬领和一条领带,好像才从身上解下来不久似的,被拿起来过,在尘土表面留下了隐隐的一弯额月。一把椅子上搭着一套上衣和裤子,仔仔细细叠好的;下面摆着两只鞋,对这里的事讳莫如深;另外还有一双随手抛掷的袜子。
那个男人就躺在床上。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呆立在那儿,低头看着那深邃莫测、没有血肉、齿牙龇露的笑容。那尸体显然一度曾以拥抱的姿态躺着,如今他的长眠既消磨尽了爱情,又征服了爱情的丑陋面,并使他永远戴上了绿头巾。在残存的睡衣下,他的腐烂的残尸已经无法从他躺着的床上移开;而在他的尸体上和他旁边的枕头上,都均匀地撒着一层耐心守候着的灰尘。
接着我们发现在第二个枕头上留着个脑袋压过的凹痕。有一个人从那上边捏起了点什么,大家向前凑过身去,一阵觉察不出的尘埃钻进鼻孔,又干又痒,我们看到了一根铅灰色的长发。
(选自冯亦代《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思考练习题
1.为什么说叙述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2.叙述有哪些常见的方式?各自的特点和作用是什么?
3.结合创作实践,谈谈如何运用倒叙。
4.简述插叙和补叙之间的差异。
5.结合创作实践,谈谈如何运用补叙。
6.谈谈《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的叙事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