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不辞长做水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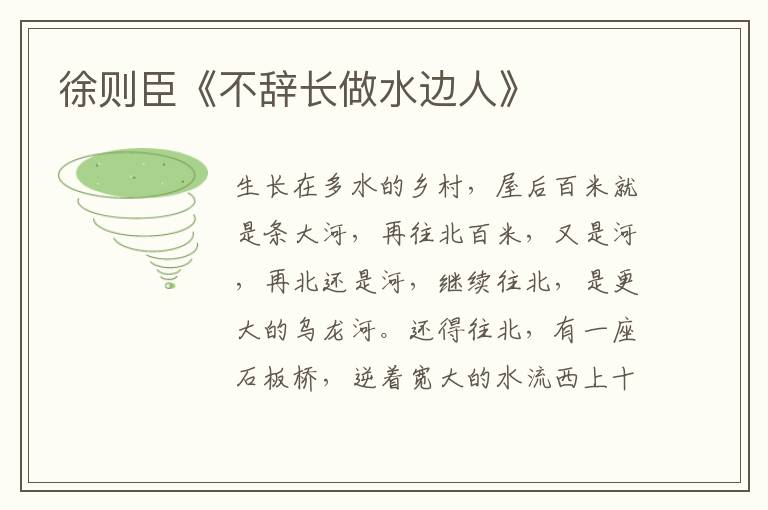
生长在多水的乡村,屋后百米就是条大河,再往北百米,又是河,再北还是河,继续往北,是更大的乌龙河。还得往北,有一座石板桥,逆着宽大的水流西上十里,是石安运河。运河的船闸在镇上,那座高得让人头晕的大闸,是我小时候理解我们镇的最重要的地标。名副其实的“零公里处”,只有想到那座闸,整个青湖镇才能在我的脑海里像沙盘一样徐徐展开。与此相同,我理解故乡,必须以一条条河流为参照:从这里到那里,是一条河的距离;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得跨过三条河;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至少有八条河那么远。没有水不行,如果哪条河断了流,我就会觉得对故乡的把握进退失据。不幸的是,在我离开故乡的这些年,一条河追着一条河消失。要么干枯,河床底下裂出惊心动魄的伤口;要么干脆沧海变桑田,有一天我从村后的小路往家走,突然找不到自家的老屋,该大水汤汤的地方长满平坦的麦苗。不过是一条河床造了个反,退水还耕,但世界真的就此改变了,我在屋檐后逡巡不已,担心离开一年后,进错了别人家的门。
所以,我眼热一切有水的地方。比如济南。
济南号称泉城。我必须以趵突泉为起点才能想象出整个济南城。我知道我的想象完全是一厢情愿,错得上了天,但还是忍不住让趵突泉长出无数的根须,联通黑虎泉、珍珠泉、金线泉、卧牛泉、马跑泉;然后让它们再继续联通,在城市幽深之地暗暗运行,奇经八脉般网络出一座完整的城市。由此,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一个别致的泉城呼之即出。我想象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是幸福的,院中掘井即饮,门外川流不息,青苔沿台阶逐年往上爬,一个娃娃长大,慢慢就有了成人的高度。泉水较河水更胜甘甜清冽,生在济南是第一有福人。
忽有一日,去到章丘,朋友力荐,到章丘要看名泉。宋人曾巩说:“岱阴诸泉,皆伏地而出,西则趵突为魁,东则百脉为冠。”百脉泉就在章丘。我基本上是个地理盲,看地图时必须默念“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才能确保不出问题,多少年里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名鼎鼎的百脈泉也在济南。朋友说,当然在济南,章丘就是济南的一个区,很多年前叫土鼓县。郦道元《水经注·卷八》称:“百脉水出土鼓县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谓之百脉水。”如此,百脉泉不在济南在哪里?那必须看。
去百脉泉公园,正值夏日的中午,太阳晒得头皮都揪到了一起。进了公园,往树荫底下一站,浑身的皮肤都舒展开了。我说等一会儿,我凉快一下。朋友说,在这个大公园里,这地方是最热的。好吧,我抽了抽鼻子,果然闻到了清冽的水气。在水边待久的人,这个问题上鼻子是不会跟你说谎的。我强烈要求直奔百脉泉。
曲径通幽后,但见一片滚水,三五成群地翻动水花,那些巨大的泉眼仿佛一朵朵永远在怒放的雪白牡丹。朋友说,那就是百脉泉。明白了,百脉百脉,百泉俱出,成就了这一片涌动的水。凑近了看,涌动的水花之外,一串串气泡从僻静处像珍珠一样冒上来。“方圆半亩许,其源直上涌出,百脉沸腾,状如贯珠,历落可数,故名。”泉泉相接,水水相连,据说水下的世界玲珑剔透,随便用棍棒往水底戳几个洞,众多沉睡的泉眼就苏醒了,一直戳下去,那将是何等壮观,整片水中,在一朵朵不懈盛开的巨型牡丹之间,挨挨挤挤的都是贝色的珠串。我把手伸进烈日下的水中,珠串击打指头,有一种执着刚烈的柔滑,鼻子没说谎,清凉沁入肌骨。资料上说,百脉泉水冬暖夏凉,长年恒温十七摄氏度左右,信然。
百脉泉西南约三十米处,有一眼“墨泉”。到墨泉这里,就发现量词“眼”太小了,也太安静了。这只动荡的“眼”得有一两个平方米,若不是周围圈上地栏杆框住了,我怀疑墨泉会比现在还要凶猛庞大。泉水像一头精力不竭的独眼困兽,绿森森、黑幽幽地一个劲儿地要破井而出。水从巨大的泉眼里往上翻滚,跃出水面近半米,形成一个沉郁的半球,绿得如此浓釅,完全是一只墨玉做成的圆球在滚动。章丘的朋友说,要是水量更大,这只墨玉做成的球冲上去一米不在话下。我站在墨泉边上,迅速脑补了一下,发现想象力有点跟不上:那哪里是个圆球,分明是一根直径一米的玉柱顶起了一个圆球,简直像神奇的大自然在诡异地玩杂技。
好了,继续往前走,还有很多泉。那盛开在水面上的五朵的泉之花是一组,成梅花状,故名梅花泉。据说是人为设计的,找好合适的位置,在水底扎出足够大的孔眼,一眼泉水就奔腾出来。这地方泉眼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如果你想这朵花有六瓣、八瓣、十五瓣,都没有问题,多扎几个眼就是了。过梅花泉,有一眼偏安一隅的娴静的泉水,旁边的石头上刻着“漱玉泉”。即使你不知道南宋李清照曾居住于此,也明白此泉与她有关,漱玉词嘛。
女词人李清照就生在章丘百脉泉畔的义仓,喝着百脉泉水长大,所以,在漱玉泉边,看见“宋代建筑、江南风景、民居形式”的李清照纪念馆就不必意外了。据说这是全国几处李清照纪念馆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中国文学史中,水是一条断不掉的文脉,江水、河水、湖水、海水,都曾隆重地参与到诗词歌赋里,《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屈原的汨罗江,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杜甫“不尽长江滚滚来”,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曹操的《观沧海》,《水浒传》中的梁山泊,鲁迅的穿行着乌篷船的运河,沈从文的湘水、沅水和《长河》,孙犁的荷花淀,汪曾祺的里下河,现在是李清照的泉,墨泉、百脉泉和漱玉泉。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养人,水更滋养文学。当年李家离百脉泉尚有一程,李清照的父亲,文学家李格非还是决定举家迁移,枕泉而居,想来不惟是为了汲水方便、图个清凉。也许他们也需要以水为坐标,从此展开对世界的想象,由章丘(土鼓)而济南,而山东,而中原,而整个中国,而俯仰天地之大、品察万类之盛。精神与生活之富足和丰润,词采与想象的深远与绚烂,傍泉而生,依水而立。遥想居于百脉泉边的李氏父女,每天从泉水跳珠间看见每一滴水中映照出的朝日和夕阳,内心该是万流涌动,沛然不绝的吧。
有一天,李清照带着使女在风发泉涌的湖中泛舟,边饮酒边作诗,不觉酒意上了头,酩酊不止,船进了田田莲叶之中。水深莲高,小船左右打转,绕不出来了。说话间黄昏已至。父亲李格非找到她,问她去哪了,女词人递上作业,曰《如梦令》。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顺便说一句,做姑娘的时候李清照酒量就相当可以,堪称女中豪杰。她喝的酒叫百脉泉酒,佳酿也。好水出好人,好水也能出好文,好水当然还能出好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