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效娟《铮铮铁骨玉中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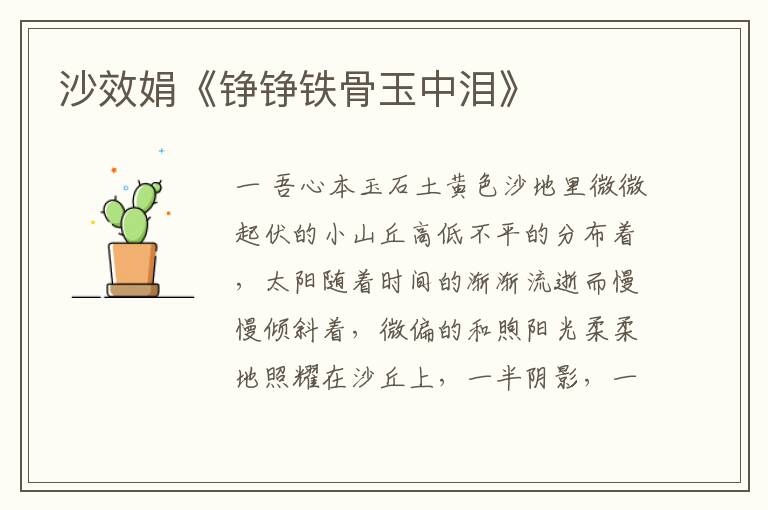
一 吾心本玉石
土黄色沙地里微微起伏的小山丘高低不平的分布着,太阳随着时间的渐渐流逝而慢慢倾斜着,微偏的和煦阳光柔柔地照耀在沙丘上,一半阴影,一半光亮 ,光暗分明。西去的商队穿着黄褐色的宽大袍子,骑着高大的骆驼,似紧紧串联起来的琉璃珠子般连绵不断。
这里是神秘的丝绸之路,也是我的魂之归处……
我是一块玉,虽比不上女娲娘娘用来补天的五彩石那般神秘,也比不上“天下共传宝”的和氏璧那般华贵,但经过千百年的温养,我也修了些灵气。我本是那乱石堆里的一块顽石,某一日,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指着我惊道:“此石乃为玉,乃灵玉也!”于是我从一块无人问津的破石头瞬间升华为稀世美玉。工匠们凿开我厚厚的石衣,打磨我凹凸不平的外皮,竟真是块玉!
老人将玉赠予对他有恩的班姓年轻人,倏尔已千年,我这顽石也修出了灵,成了精。可我依旧懒散,疏于修行。毕竟可以舒舒服服地躺着,我又何必自找麻烦呢?
我这懒散的老妖精虽说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这千年来也阅人无数。恩怨情仇,冷暖悲欢,凡人们总将那短暂的一生都纠缠其中,那短暂的岁月又能承担多少负重?
眼里看多了,心里便淡了。
我曾经以为我会在漫长岁月里无吝虚度,一如既往地袖手旁观,冷眼观望,却不料世事难测,我与这丝路,与班超已被命运之神的细线紧紧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
二 初见君之时
那天,我照常伏在桌案上那铺着红布的金边木盒中,一位年轻人正在桌案旁,手持素笔,全神贯注的抄写着堆积如山的文稿。他刚过而立,正是壮年之时,身材高大魁梧,面容说不上多俊美,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英气与豪放,粗布衣服却是穿出了一股侠气。不似文人,却类武将。我知,他叫班超,班仲升。
他面露倦色,我却从倦色中看出一丝不甘与无奈。他像是突然下定决心似的,将笔轻轻放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已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此语一出,旁边的人毫不留情地嘲笑道:“班仲升,汝谓何怪语哉!尔且一布衣,高中否尚未可知,何来封侯?”他并不因被嘲笑而窘迫或退缩,鹰隼一般锐利的眼睛里充滿着坚定,反驳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我闻此语,心下不以为意,这种夸夸其谈之辈我见多了,半途而废,强行而无功之辈也见多了。
人生薄凉难测,尔等小辈又何知!
但很快,我就发现我这个阅人千遍的老妖精这次竟然看走眼了。
他并不是三分热度于此,而是投入十分真情。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国事所累,他一介文人竟真的就毫不眷恋地舍弃了安稳的生活,仅携一把长刀,便踏入了那吞噬过无数条鲜活生命的战场。他的娘亲担忧儿子的安康,因我是祖上所传之灵物,便将我赠予他,以保平安,且寄相思。
我被挂于年轻将领的腰间,随他去踏遍黄沙,随他去征战万里。滚滚黄沙上曾抛洒过多少热血,不可知,悠远丝路里埋葬过多少铁骨,不可知。我只知,此人有凌云之志,亦有铮铮铁骨。
三 同君与共骋战场,丝路之上碎玉响
黄沙肆虐的咆哮声,将士厮杀的喊叫声,刀剑交锋的碰撞声全然纠缠成一团,哪里比得过曾经的墨香洇然,书卷留痕。我不知这位文人出身的年轻将领是否有悔意,心里隐约有些不安。抬眼望去,年轻将领骑着红棕色的高大骏马,那马的眼神坚毅果敢,同他一般。寒风刺骨,他仍穿着冰冷的铠甲。银色铠甲反射着皎洁凄清的月光,照亮了他的脸。他剑眉星眸,英气逼人,在落败的北匈奴面前露出不羁的笑容。
我被这笑容震撼了,是的,也许他生来就不该是在纸墨书卷间混迹的人。他有文人的聪慧,也有武将的果敢。他的聪慧不该困于纸笔间,在战场上更能一绝千骑,他就该是一匹战场上的狼。
丝绸之路悠远漫长,骆驼上挂着的银铃随着脚步的渐远而作响,混合着风沙的闷响,煞是好听。他骑在骆驼上,身子端正而挺拔,带着仅三十六名部下的精简队伍,在夕阳下缓缓驶向西域。
粗布军帐里,烛影摇曳。火光下他的脸坚毅而聪敏,他的身边围着一群部下,他们初到鄯善国,都不知这位司马将出何言,我也甚是不解。
他锐利的眼睛微眯,神色严肃道:“汝不觉鄯善王之礼渐薄?此必因北匈奴之使至鄯善王难择,不知归顺何处。醒者尚知未至之事,况此时已显乎?”
部下们面面相觑,都拿不定主意,只道:“仅凭司马吩咐!”
他在帐中踱了几步,忽然用力拍了一下手掌,眼珠微微转动,计策已在心中。
他厉声问旁边的鄯善侍从:“匈奴使者已至数日,今何在?”他本就长得高大挺拔,气势慑人,如今板起脸来更是怖人,如一头审视猎物即将扑杀过来的猛虎。侍者的脸瞬间变得惨白,狠狠地哆嗦了一下,颤颤巍巍道:“匈……匈奴使者现居国内,王以客事之。”
他冷哼一声,眼中仿佛燃了一团火,沉声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是夜,他带领三十六位部下,顺风纵火,拿起刀刃击杀匈奴使者,百余匈奴人被烈焰吞噬。他一手持银色的刀刃,冷冷地注视着愈燃愈烈的火光。
班仲升这个人不被局势所累,必先发制人。我的心狠狠地颤了一下,是了,此人必成大器!可又转念一想,又忍不住替他揪心起来:他擅自做主斩杀匈奴使者,又该如何同鄯善王交代呢?
果然,他没有让我失望,他舌灿如莲花,临危而不乱,用他的智慧与辩才让鄯善王臣服于大汉。他的才华终于充分的显露出来,他再使西域,平抚于阗,他巧用智谋,平定疏勒,这时的班仲升初露锋芒,意气风发,是一只欲振翅高飞的雄鹰,只待长风一起,便冲破重霄。
然而,世事总是变化得那样快。正欲高飞的雏鹰却被生生折断了稚嫩的翅膀。
“大人,先帝驾崩,太子刚刚即位,焉耆与龟兹二国于此时谋反,匈奴亦反,虽力抗,然……不能阻也,今吾军已无援矣!”一名将士单膝跪在地上,双手抱拳道。
我看见班仲升他满脸倦容,缓缓闭上眼睛,轻轻地揉着穴位,只道来一个字:“守!”
那跪在地上的将士微微起身,嘴张了张,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
烽火连天,硝烟四起,就连挂在他腰间的我也好些日子没睡过安稳觉,更何况是他!
守卫兵频频穿梭在他帐中,屡屡告急。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张英气十足的脸一天天憔悴昏黄下去,那双锐利的眼睛也深深地凹陷进去,强壮结实的身躯日渐消瘦成秸秆。
每次他听到越来越糟的情况,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长叹一声,仍用干涩的声音重复着那一个字:“守!”
我只是一块玉,没有心,就算有心,那也必然是硬邦邦的,没有温度的。我不知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这般坚守着,为了皇帝?为了朝廷?
那天,并不是放哨或守卫的将士来通报,来的是穿着锦服的汉朝使者。紧皱着眉头,坐在桌案旁研究战术的他,在见到朝廷使者的那一刻,眼睛散发着异样的光彩,那枯槁老树般憔悴的面容好像突然迎来了春天,枯木逢春。他放下地图,飞快走近几步,欣喜道:“可是皇上派来了援兵?”
身着繁复服饰的汉朝使者避过了他那热烈的目光,重重叹了一声,无可奈何道:“传皇上谕旨,班超等西域使者速速归朝。”
皇上弃了这块土地!弃了西域!
他满眼的不可置信,失魂落魄地低垂着脑袋,原本露出灿烂笑容的脸僵在了那里,弯成一个嘲讽的弧度。
“大人,”帐中的部下道,“既然皇上已下旨,我等必得奉旨归去。”
他没有言语,疲惫地摇了摇手,部下迟疑了一下,还是缓缓退去了。
夜里,他仍挑灯苦研地图,天渐始明,他没有睡下,而是自己一个人定定地望着漫着黄沙的远方。
归去那日,疏勒都尉不忍他离去,在他面前拔刀自刎。于阗的百姓不忍他东归,抱住马腿痛哭。那么多的眼泪在他面前滑落,那一刻我竟然也有落泪的冲动,可我忘了,我是块冰冷的玉,不懂情感,亦不会流泪。
他神色有些激动,原本惨白如纸的灰败脸庞也泛上了浅浅的红,嘴唇微微颤抖着,满心安慰的话都涌上了唇边,却没有发出一个响声。
“汉使莫归,莫弃于阗!”百姓们哭喊道。
我看到他眼里佯装出来的不为所动的强硬如墨水一般一点一点地晕开,变得虚弱,变得柔软……
突然他将头扭到一边,下定决心似的闭上了眼睛。铿锵道:“吾不归矣!”
身旁的部下闻此语,震惊了一下,慌张道:“大人,此乃抗旨啊!”
他不惊不慌,一派平静:“吾辈为大汉效力,定当以命报之,又怎可拘泥于形式!”
部下又道:“大人,即使吾等不归,形势衰微,已无力回天矣!”
他对身旁的部下摆摆手,一双敏锐的眼睛坚定地注视着前方:“虎狼之穴,尚不惧矣!吾意已决,尔休多言!”
部下轻轻叹了口气,恭敬地退守在一边。
百姓闻言,皆振臂高呼,欢声道:“汉使不弃我,国存有望矣!”
他在旁边淡淡地笑了笑,可我却清楚地看到了这浅淡笑容中的苦涩。心中愤愤道:“你们这些人啊,只懂得自己安身立命,可又曾懂得别人的无奈与苦楚!”
他将我轻轻从腰带上取下,提着那根红色的穗子把我举到眼前,黯淡的眼神好像闪了闪,他用手柔和地抚了两下,又拿起一块雪白的帕子将我身上沾上的黄沙细细擦掉,深邃的眼睛幽幽地看著我,喃喃道:“不知远方的阿娘可否安好,此番我已不归,恐不能尽孝也。”
他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君,无愧于民,唯一愧疚的也只有此处了。
他不打仗时,就将我放在那个铺着红布的小木盒里。他不在军营,守着营帐的士兵便趁着闲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司马可谓大丈夫也,此逆境也不折矣!”
一个士兵摇摇头道:“此言差矣!吾觉司马恐于阗难之也。”
又一个士兵撇嘴道:“吾觉司马欲立功封侯也。”
一瞬间七嘴八舌,原本安静的营帐瞬间聒噪了起来,突然一个将士猛咳了一声,霎时安静了。空气仿佛在此刻凝固了,班仲升正静静地站在营帐的门旁,脸色平静,没有任何的怒意,也没有任何的窘迫,好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淡然如初。眼神不曾泛起一丝涟漪。那些个方才吵闹的士兵瞬间烧的面红耳赤,眼神慌慌张张,黑黑的眼珠像铁球重重地沉下去,就是不肯抬起来。连呼吸声也刻意地放缓,唯恐一点火星便燎起整片原野。
他报之微微一笑,谦和地让他们退下了。
良久,终是无奈地舒出了一口气,左手扶额,右手持地图,秉烛夜研。
我不解,我这个见多识广的老妖精头一回见到这种人。朝廷不支持他,将士也不支持他,那么支持他的到底是什么?
我第一次违反了规定,干涉人情世故,入了他的梦。
梦里,笼着一层氤氲的烟雾,冷月的光华流泻满地。待烟雾散去,不是他那花红柳绿,繁花似锦的故乡。是西域,是那丝路。黄沙如春日柳絮般肆意飘散,西去商队的骆驼在那刺眼的阳光下愈拉愈长。不远处,军营连绵,锦旗上墨黑色的“汉”字潇洒霸气。他正在一座军营里,身着染了些鲜血的铠甲,一只手指着地图,侧身同身旁的副将商谈。
竟是在梦里也不肯放松吗?
我使了个术法,将那漫漫黄沙,告急战事通通隐去了。又化身成一名女子的样子走到他面前,他显得有些疑惑:“姑娘从何而来?”
我心道:“姑娘?若按我的真实年龄,你叫我声老祖宗也不为过。”我学着那大汉女子的样子,微微欠身对他行了一个礼,柔声道:“小女的出处并不重要,现小女有一疑惑,大人可否解答?”
他点头道:“姑娘但讲无妨。”
我缓缓道:“大人出使西域已数年矣,今国事衰微,数国夹而攻之,战事难胜,竟还想守于此?”
他看着我,眼中依然一片平静,坚定道:“是。”
我被那眼神与回答瞬间弄得无措起来,没有了装腔作势,故作文雅的心情,不加掩饰道:“为何?为那朝廷?可大汉已弃了此地!”
他淡然道:“朝廷已下旨使吾归,不为朝廷。”
我高声道:“不为朝廷,那为荣华?那为封侯之志?”
“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
我几近失态,咆哮道:“那究竟为何?”
他平静道:“只为坚守,只为男儿一身的铁骨。”
我愣在了那里,过了良久,才缓缓注视着他低声道:“大人可曾有悔?”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大丈夫当若此也,何悔之有?”他又抬头望向那大漠,认真道:“自丝路通矣,货物流转,交通频繁。当效张骞之辈,守铁骨,定四方,不枉此生也!”
两滴清泪从我眼中流出,原来玉也是会流泪的吗?
也许是我化为女子的缘故,那颗冷硬的心也变得柔软起来。我摸了摸脸上的液体,看着手指上沾的晶莹的水珠。原来世上还有这种事——没有受一丝一毫的伤,却痛不能抑。
他锋芒初露,便被折去双翼,他耗费心血,却迎来一道朝廷的归朝令。孤立无援,将士不解,他还在苦苦支撑,没有谁想去理解他,也没有谁愿意支持他。
班仲升,他们只道你铁骨铮,又何曾了解你的悲壮,你的苍凉!
皆知铁骨铮,谁知玉中泪。
我几步上前,眺望着那金色的海洋,清脆悦耳的驼铃声悠悠的传来,夕阳将西下,橘红色的余晖笼罩着这片广阔的天,刹那间连天地的曲线都变得柔和起来,霞光四散,光芒满溢,如诗如画。他守的便是这里,也注定会与这丝路密不可分。
我离开了他的梦,又化为了那块安安分分的玉。
自弃归后,他越发忙碌起来,读兵书,研地图,商战术,抚民心。须发渐渐变得花白,眼神却没有那归去时的落寞与神伤,又重新绽放了光芒。是的,他遂了自己的意,顺了自己的心,即使战局再恶劣,情况再艰难,他也尽了自己之力,无悔矣!
我跟他完全不同,我无为度日,得过且过。他不负年华,绝不苟且。可无甚相同的我们两个却被缘分二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也许,我的生命也该同他一般燃烧一次!
“大人,疏勒两城池重降龟兹,且与尉头国联合,欲乱!”汇报的部下道。
他思忖片刻道:“欲收二国,必将叛军首领斩杀,以定民心。且须败尉头军,以绝其反叛之心。”
他猛地起身,剑眉一挑,眼神凌厉,高声道: “众将士听令!集兵马,缉拿叛军!”
“是!”将士们个个精神抖擞,神情激昂。
他将我从盒子中取出,小心翼翼地挂于腰间,轻声道:“阿娘,愿得您再次庇佑,孩儿定当胜利!”
战场之上,两军混战,冰冷的刀刃反射的寒光冷入骨髓。他身着银甲,身后鲜红的斗篷在风中飘扬,仿佛是鲜血染就的。结实的头盔下一双锐利的眼睛扫视着敌军。他策马奔去,长刀也随之瑟然出鞘,一个闪躲,一记横砍,速度如此之快,寒光一闪,一个叛军便被斩于刀下。
将士们的热血瞬间沸腾了起来,蒸腾到了脸上,泛上了一大片红,他们精神振奋,高喊道:“大人威武!”
班仲升将刚染了血的刀微上举,指着天,下令道:“将士们,诛拿叛军,复我河山!”
“杀——”将士们喊叫着,精神抖擞,如同喝了酒一样,兴奋而无畏。
一瞬间,万马奔腾,尘埃飞扬,刀剑交锋,血花四溅。硝烟与血腥的味道溢开。
他们瞬间就以压倒性的优势占了先锋,无数叛军被斩于马下。
马上的班仲升露出了一个满意的浅笑,可就在敌军被打的节节败退之时,一个小兵出人意料地从他身旁杀出,冰冷的长刀已逼近他的胸膛,如此变故,躲闪根本来不及!
“嘭!”什么东西破碎了,不是他的心,是一块玉……
是我,破碎了……
他脸色瞬间大变,眼里满是疑惑与惊愕,但迅速便反应过来,反手一刀,那小兵便落于马下。
他不可置信地拿起挡在他胸膛前破碎的我,疑 惑道:“此玉我记得挂于腰间,怎又会突然出现于胸膛前?”又喃喃道:“想是阿娘保佑于我。”
傻瓜,哪里是你想的那样……不过,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奄奄一息地躺在他手里,本体已七零八碎,碎得干净。我静静地听着身边将士们胜利的欢欣声。真的没有什么关系了,我这个无用的老妖精也终于做了件好事。我的生命里终于也有了一团不灭的火。班仲升,你战事必将胜,必将闻名丝路,必将垂名千古!
四 铁骨定永恒,玉魂驻边疆
丝路终于在漫长时间里又重归于平静。
他正打算将命不久矣的我埋于丝路的黄沙中,旁边是一个已经挖好的沙坑,我乖巧地躺在他手里,再也没了那曾经的调侃的力气,如果是曾经的我,想必是会大叫:“小子,埋这么早作甚!我还没死透呢!”如今,只是默默地看着他,虚弱地笑笑。
他看着手心里的我,轻声道:“玉,你已相伴多年,今我战事大胜,叛乱已平。今后仍将守于丝路,可人生有限,待我归尘,你便替我守于此处罢。”
我已本体破碎,虽没有立即死,灵气会渐渐散尽,最终会变成一块没有生命的碎玉。
我埋于这丝路的黄沙里,依然陪伴着这块土地,如同这片神秘而广阔的丝路黄土里埋葬着的将士一般。嗯,我对自己这样的结局很满意,今后我将陪着他一起守这丝路,他去了,我便守着。
浅色的沙地里,微风拂过,平抚沙痕。四周平坦空旷,清净无音。一个个深浅不一的暗色足痕拼凑成了一段历程,一个记忆。只消片刻,它便会烟消云散,了无梦痕,脆弱得可怜。我经常会想,在这片土地上能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可是,他的确是做到了永恒。
他将自己最美好最繁茂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奉献给了这条丝路。
他坚守西域三十多年,人生有能有几个三十年?
人的一生是真的很短暂,如飘落的缤纷落英,落完了也便结束了。吾身为玉石却也愧不如他那铮铮铁骨硬。千年岁月,也不过流了那么一次泪,不为苦痛,不为命殒,只为他之坚守。
班仲升在神秘悠远的丝路上留下了永久的標记,也在这片黄沙中成就了自己精彩的一生。
他殒去了,也许还会出现同他一般的铁血男儿,毕竟这里是丝绸之路,又有什么奇迹不会发生呢?
(第一届“丝路陀影”大学生征文大赛二等奖)
作者简介:沙效娟,1999年生于山东临沂,现就读于兰州文理学院。总能在写作中汲取快乐,写作对我来说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2017年参加“丝路驼影”大学生征文比赛获得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