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洛夫斯基《我的一天——为《世界上的一天》文集写的短文》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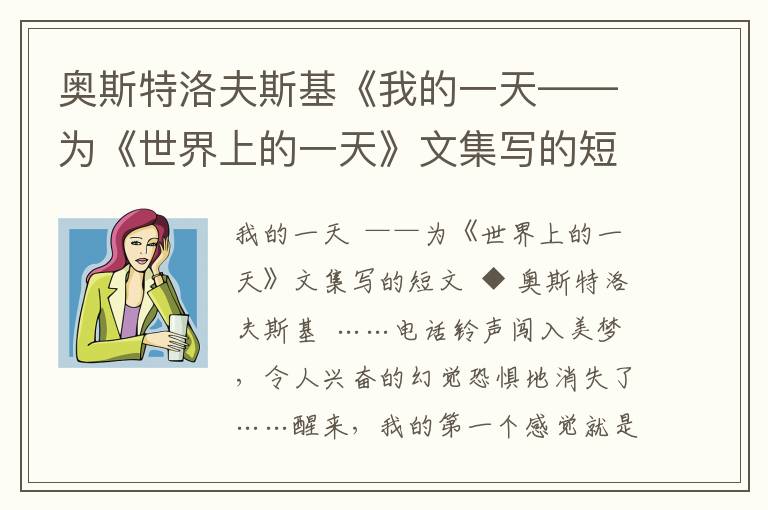
我的一天
——为《世界上的一天》文集写的短文
◆ 奥斯特洛夫斯基
……电话铃声闯入美梦,令人兴奋的幻觉恐惧地消失了……醒来,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这被瘫痪所钉住的身体疼得难于忍受。这就是说,几秒钟之前还在作梦,在梦中我年轻,有力,骑着战马象疾风一般奔向初升的太阳。我并不睁眼,这没有必要:在这一瞬间我正回忆着一切。八年前,残酷的疾病使我倒在床上,动弹不得,弄瞎了我的眼睛,把我周围的一切变成了黑夜。己经八年了!
肉体的剧烈疼痛,向我猛烈攻击,既残酷又无情。我本能地作着初步的反抗——紧紧地咬着牙。第二次电话铃声赶紧地跑来援助我。我知道,生活在号召我去反抗。母亲走进来。她送来早晨的邮件——报纸、书籍、一束信件。今天还有好几次有趣味的约会。生活要取得它应有的权利。痛苦滚开吧!清晨短时间的搏斗结束了,同往日一样,生活战胜了。
“快点,妈妈,快点!洗脸,吃饭……”
母亲把未喝完的咖啡拿走。我马上听见我的秘书阿列克山得拉?彼得洛夫娜的问安。她象钟一样准确。
人们抬我到花园的树荫下。这里一切都准备好了,预备开始工作。赶快生活。就因为这个,我的一切欲望才那样强烈。
“请读报吧,在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的边界上有什么消息?法西斯主义——这个带着炸弹的疯子——已经向这里猛袭了,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向什么方向扔下这个炸弹。”
报上说:国际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乱蜘蛛网,破产了的帝国主义的矛盾无法解决……战争的威胁象乌鸦一样盘旋在世界上空。日暮途穷的资产阶级已将自己仅有的后备军——法西斯青年匪徒——投入竞技场。而这些匪徒正在使用斧头和绳索,将资产阶级的文化很快地拉回中世纪去。欧洲非常沉闷,发散着血腥气味。一九一四年的暗影,甚至瞎子也能看见了。世界狂热地扩充着军备……
够啦。请读一些我国的生活吧!
于是我听到了可爱的祖国的心脏的跳动。于是在我面前便显现出一个青春、美丽、健康、活泼,不可战胜的苏维埃国家。只有她,只有我的社会主义祖国,举起了和平和世界文化的旗帜。只有她创造了民族间的真正友谊。作这样的祖国的儿子该是多么幸福啊!……
阿列克山得拉?彼得洛夫娜念信啦。这是从辽阔的苏联遥远的尽头给我写来的——海参威、塔什干、费尔干、第弗利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列宁格勒、莫斯科。
莫斯科、莫斯科呀!世界的心脏!这是我的祖国在和他的儿子中的一个互相通话,和我,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著者,一个年轻的、初学的作者互相通话。几千封被我小心保存在纸夹中的信——这是我最珍贵的宝藏。都是谁写的呢?谁都写。工场和制造厂的青年工人、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海员、飞行家、少年先锋队员——大家都忙着说出自己的思想,讲一讲由那本书所激发的情感。每封信都会教给你一些东西,都会增添他一些知识。看吧,一封劝我劳动的信写道:“亲爱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你的新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你快点写吧。你应当把它写得很出色。记住,我们等待着这本书哪!祝你健康和有伟大的成就。别列兹尼克制氩工厂全体工人……”
第二封信通知我说,一九三六年,我的小说将在几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印刷总数52万册。呵!这简直是一支书籍大军了!……
我听见:门外,轻微的喔喔声,汽车站住了。脚步声。问好、听声音,我就知道,这是马里切夫工程师。他正在建筑一所别墅,是乌克兰政府给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赠礼。在古老花园的绿树浓荫中,距海滨不远,将建造起一所美丽的小型别墅。工程师打开了设计图。
“这边是您的办公室、藏书室、秘书办公室、还有浴室。这半面是给您的家属住。有很大的凉台,夏天您可以在那里工作。周围阳光很充足。棕树,木兰……”
一切都预备好了,就为着让我能安心工作。我深深体会到祖国的关怀和抚爱。
“对于这个设计您满意吗?”工程师问。
“这太好了!……”
“那么我们就动工啦。”
工程师走了。阿列克山得拉?彼得洛夫娜翻开记录本子。现在是工作时间。在天黑以前谁也不到我这里来,都知道我在忙。几个钟头的紧张工作。我忘却周围一切。回忆着往事。在记忆中出现了动乱的一九一九年。大炮在怒吼……黑夜里火光冲天……大队的武装干涉者侵入了我国,于是我的小说的主人公,忘我牺牲的青年便和自己的父亲们并肩作战,给这种进攻以反击。
“四个钟头了,该停止啦!”秘书小声说。
午餐……一小时休息……。晚间的邮件——报纸、杂志,又有来信。我听人们念小说。阳光消失了。我看不见,但我感觉到凉爽的黄昏在移近着。
许多人的脚步声在沙沙地响。洪亮的笑声。这是我的客人们,我国英勇的少女们,女跳伞家,她们曾打破了世界迟缓跳伞的记录。同来的还有索契城参加新建筑工程的共青团员们。伟大建筑的隆隆响声竟被带进了这幽静的花园。我暗中想象着,外面正在怎样用水泥和柏油铺着我这小城的街道。一年前还是旷野的地方,现在已经耸立着宫殿似的疗养院的高大建筑了。
天黑了。屋里静静的。客人走了。人们念书报给我听。轻轻的敲门声。这是工作日程上规定的最后的一次约会。英文《莫斯科日报》的记者。他的俄语不太好。
“是真的吧,您从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真的,当过烧锅炉的工人。”
他的铅笔很快地擦着纸响。
“请您告诉我,您很痛苦吧?您想,您是瞎子呀,多年躺在床上不能动了。难道您一次也没有想到自己失去了幸福,没有想到永远不能再看东西、走路,而感觉失望吗?”
我微笑着。
“我简直没有时间想这些。幸福是多方面的。我也是很幸福的。创作产生了无比惊人的快乐,而且我感觉出自己的手也在为我们大家共同建造的美丽楼房——社会主义——砌着砖块,这样,我个人的悲痛便被排除了。”
……黑夜。我睡下,疲倦了,但很满意。又生活了一天,最平凡的一天,但过得很好……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