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浮世绘》杜帝散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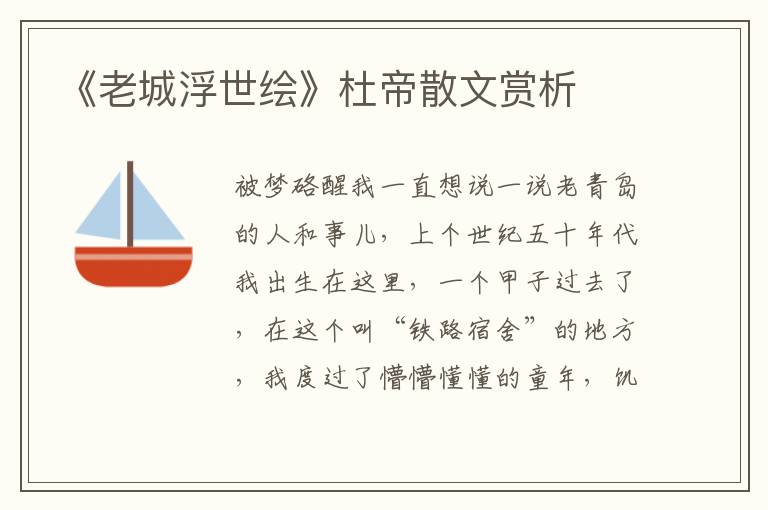
被梦硌醒
我一直想说一说老青岛的人和事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出生在这里,一个甲子过去了,在这个叫“铁路宿舍”的地方,我度过了懵懵懂懂的童年,饥饿和敏感的少年,成长期的记忆难以泯灭,那些场景和气息、画面与声音,多少年后带着不可抑制的躁动,带着快乐和忧伤,拥进我平静的生活,刺痛着岁月深处的经脉,许多次把我从梦中硌醒,我有时在暗夜里睁眼躺着,有时披衣坐起,怅惘不已。
许多年来,我围绕着居住的铁路宿舍,陆陆续续在笔下展开追寻和打捞。我知道,当一个人陷在回忆里难以自拔的时候,说明他老了。老态龙钟的特征和财富,便是在破碎的版图面前,不由自主地拼接镶嵌,收拢已经离散的岁月,描画过去寒酸而温暖的记忆。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曾在她唯一的长篇小说《姑娘和妇女们的生活》里说:“人们的生活……乏味,简单,令人惊奇,莫测高深。”我出生长大的铁路宿舍,何尝不是如此!一排房子,一堆邻居,一个社会,一颗星球,个体经验亦是集体记忆,阶段生活也是时代刻痕。童年少年的生活,既简单又复杂,既乏味又高深,它像一串散落在湖底的珠子,沉没了那么多年,仍然散发着时明时暗的光波,水纹涟漪不断。
芳大娘
芳大娘是我家的老邻居。说她老,是因为从我记事起,芳大娘就满脸皱纹,步态蹒跚,至今已过二十多年,芳大娘还是那样,满脸皱纹,步态蹒跚。仿佛她生来就是个老人,后二十几年没有变化,时间对于她只是掠过的风,未曾吹开或吹皱、未曾增多或减少她的老态。
其实芳大娘也有过浪漫的青春。她是一个老革命,听我妈妈讲,芳大娘年轻的时候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常常在敌我拉锯战中疲于奔命,她的几个孩子都是在战斗和行军中死去的。
我问过芳大娘,同敌人打仗,怕不怕?尤其她一个女人家。
一提到战争,说到过去的艰苦经历,芳大娘就滔滔不绝。她说她向还乡团扔过手榴弹,她当时很能跑,两个孩子就是在拼命的跑动中流产死掉的。还有一个孩子已经三岁了,结果在山里野营,给冻死了。当然也饿,孩子没东西吃,大人也没得吃,常剜野菜。
说起由地主、富农组成的还乡团,芳大娘恨得牙根咯吱咯吱响。
“还乡团用铡刀铡贫协的人,还用刺刀捅。”芳大娘说。
我问:“你们对还乡团怎么样?”
芳大娘说:“咱们也用铡刀铡,用砖头、石头砸他们的头,把头砸烂。有的还活埋。”
我问:“谁先动手?”
芳大娘说:“咱先杀他们,分他们的地,分他们的房子、牲口,分他们的金银财宝,连他们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拿走。不过,那时候的财主有的也不咋样,家里穷得只有一两头牲口,咱也给他分了,把他们赶到牲口屋去住。”
“那他们还能不报复?”
“就是呀,国民党扶持还乡团,共产党支持咱贫协,两边拉锯,逮着就杀,越杀越邪乎。”
芳大娘蠕动着没牙的嘴,脸皮耷拉着。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年轻时候还杀过人。
想到芳大娘杀人,我对她应该有的慈祥印象,好像抹上了一些恐怖的东西,我大睁着眼,老想到鬼怪电影里的妖魅。
芳大娘为革命立了功,在腥风血雨里颠簸了大半生,可她没有一官半职,也许是她不识字的原因,难以提拔,她所享受的最高待遇,就是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几十元钱的生活费,再就是她积极发挥革命余热,担任我们宿舍第七小组的治安干部,每晚颠着小脚,拿着手电筒,上街巡逻,说是抓小偷,还防止敌人和平演变。
前不久我回家,又见到了芳大娘,她拽住我,仰着脸,絮絮叨叨地说我长高了,又问我孩子,问我的工作。我说还是在写点稿。
“写稿?”芳大娘拽着我更紧了,她叫着我的小名,一再提到她为革命牺牲了四个孩子,她用脏乎乎的袖子抹了抹眼泪,又掀起油膩的蓝布褂,让我看她背上的枪伤。
“孩子,要写我,我可以向你讲上十天十夜,当初,我们和还乡团……”
她又扯上了,想到与还乡团杀来杀去,不知为什么,我很难产生歌颂这位革命老妈妈的冲动。
唉, 芳大娘!
扫街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妈妈虽然是解放前的老党员,但因为生了六个男孩,她放弃了区政府所属企业的公职,专职在家照料孩子,全家的经济收入只靠我爸爸和后来大哥有限的工资,其困难、窘迫可想而知。
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我很小就干各种家务活,生火做饭洗衣服就不用说了,买煤,买粮,买菜,还到山上去搂草,去海里挖蛤蜊,随同宿舍的大人到海边垃圾场去捡破烂,从工厂里倒出的垃圾里翻捡铁、铜、油线、煤渣。
为了给家里增加收入,妈妈还把打扫街道卫生的活儿接了下来,当时居委会从每户收取几分钱的卫生费,到月底发给打扫卫生的人,每月几块钱。现在看那点钱不过是一盒不上讲的烟钱,可那时候,我们太穷了,几块钱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可忽视的稳定收入。
按要求,扫大街要在居民没起床的时候,一般是黎明时分,这也正合我意。扫街毕竟是出苦力的活儿,我有点羞于见人。天将明未明,整个世界一片静穆,街道渺无人迹,我的心情就有些放松。可是太早了,也遭罪。冬天苦啊,从家里出来不久,手和脚就冻麻了。遇到下雪,雪厚得扫帚扫不动,我只好用铁簸箕铲,弯腰一趟趟地像推土机似的前行,寒风凛冽汗水照样淋漓。
秋天是满地的落叶。我们街道的房子是日本鬼子给铁路工人盖的,他们可能很重视绿化,房前屋后都是排排的树,有挺拔的杨树,还有粗壮茂密的梧桐树,秋天来临的时候,我感觉老天爷好像故意为难扫街的人,刚刚扫干净了,身后又是被风吹落的树叶。那时候每天早晨看着覆盖一地的落叶,痛苦极了。低下头扫,不想明天的事儿,一天天,落叶周而复始,直到天空飘落雪花,树叶才不挑衅了,寿终正寝。后来我爱好写作,周围许多诗友都以秋天的落叶为题,赞美,象征,辞藻华美抒情,我却始终写不出一行关于落叶的诗句,也许童年的经历干扰了柔美的诗意。
夏天扫街轻松多了,脏物少,凌晨不冷不热。只是起得太早,很困。记得妈妈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的时候,我真难受,眼睁不开,朦朦胧胧穿上衣服,到院子里抱起一把大扫帚,走出屋门。
世界很静,我能听到远远近近的鼾声。需要打扫的宿舍道路有四条,呈东西走向,有二三百米的样子。我从东头开始,“唰”、“唰”、“唰”地扫了起来。清晨空气凉爽,我抡起竹子编的大扫帚,由左至右,把地上的脏东西,例如纸屑、树叶、草皮,全部扫到右边,每扫过几十米,我就把扫在右边的垃圾撮到一个大筐子里。
刚刚扫完的街道,非常干净漂亮,黄土地上被扫帚划过整齐的扫帚印痕,像是一幅美术作品。我常常伫立回望,看着地上洁净的图案,我创造、劳动的愉悦,从心底甜甜地涌出。
扫街开始觉不出累,从东头扫到西头,接着从西头往东头扫,到了第三趟的时候,胳膊酸了,腰和腿隐隐的痛。最要命的,是饥饿感袭来,肚子里空荡荡的,胃揪心的痛。在我的记忆里,家里的食物总是不够吃,我和哥哥、弟弟轮流扫街,谁黎明出工干活,早晨饭会加半块饼子。这时候,我是那么地想念那半块饼子,想得我眼泪快流出来了。后来我真的哭了,空荡荡的街道上,眼泪无声地淌,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饿得意志衰弱,也可能是累得有些冤屈,反正,我扫街的后半段,有一阵儿是伴着泪水进行的。
天空慢慢放亮,有起床早的人已经出门了,我擦干泪痕,强打精神,和邻居打着招呼:“王大爷!”“上班啊李叔叔!”过去不会说“你好”之类文雅的词汇,只有干脆利落的称呼,所有的问候、温馨全在里面了。妈妈对我们兄弟管束教育很严,从小就教育我们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好习惯要一步步养成,让我们见了长辈态度要谦恭,主动热情打招呼,串门时要避开人家吃饭的时辰,人穷不能志短,等等。母亲的话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扫街以来,我和哥哥、弟弟都有过拾金不昧的光荣记录,有一次我在地上扫出来一张五斤的粮票,当时那个激動啊,真想留下,可我确实做到了“设身处地”,想到了丢粮票的家庭也许和我家一样,丢了五斤粮是多么可怕的灾难,于是,我像一个“英雄”一样,气宇轩昂地把粮票交给了宿舍主任。
我还在扫着街,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也只剩下半条街道,胜利在望。不过,这时我抡扫帚的胳膊已经麻木,握扫帚的手有些颤抖,只是机械地来回舞动,扫帚在半硬半软的土地上,“唰~”、“唰~”、“唰~”地呻吟。
扫街时间长了,我也从中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例如用什么姿势扫最节省体力,怎样巧妙用劲;遇到石块或土疙瘩,扫帚要轻轻上抬,掠走脏物而扫帚不阻;右边的浮土积多了,要垫回左边,不然会路面洼陷,一边高一边低。
我参军后部队经常打扫卫生,我扫街是连队的一把好手,他们看着我身后扫出的漂亮图案,啧啧称赞。战友们哪里知道,我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扫街专业户了,家里扫秃的竹扫把,不下几十把。多少年过去了,童年扫街时的饥饿、劳累感觉,始终难以忘怀。这些,我都没好意思向战友们说,可能是年轻人的虚荣心在作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