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裴启《语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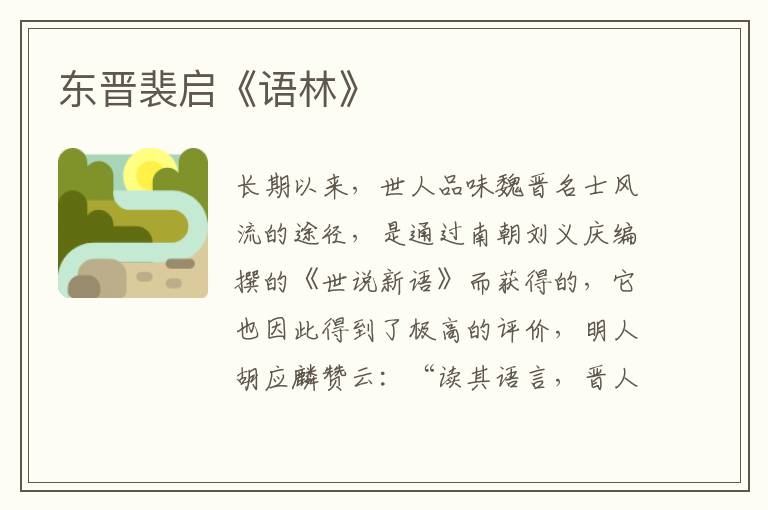
长期以来,世人品味魏晋名士风流的途径,是通过南朝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而获得的,它也因此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明人胡应麟赞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少室山房笔丛》)鲁迅称之为“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事实上,早于《世说新语》成书六七十年的东晋裴启编撰的《语林》,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名士教科书,它在记录魏晋名士风度方面起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对《世说新语》的成书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由于《语林》在隋唐之际便亡佚了,以致人们忽略了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 裴启与《语林》的盛行
《语林》的作者——裴启,在史书中没有关于他的传记,仅有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以及南朝宋代檀道鸾《续晋阳秋》提供了零星的记载,我们也只是对其生平略知一二。《世说新语·文学》第90则云: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
在《世说新语》中只是说《语林》的作者是“裴郎”,没有明确指出是裴启。《世说新语》问世后大约六十余年,刘孝标(462—521)为《世说新语》作注,引裴启《语林》中的故事,表明了《语林》的作者是裴启。《世说新语·任诞》第43则刘孝标注云:
裴启《语林》曰:“张湛好于斋前种松,养鸲鹆。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云云。”
刘孝标又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指出《语林》的作者是裴启。《世说新语·轻诋》第24则刘孝标注云:
《续晋阳秋》曰: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语林》是一部描写魏晋名士言谈举止、嘉言懿行的志人小说,此书在东晋时曾大为流行,名重一时。
关于《语林》的作者似乎还存在一些疑问,刘孝标也没有完全确定,《世说新语·文学》第90则刘孝标注云:
《裴氏家传》曰:裴荣字荣期,河东人。父穉,丰城令。荣期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撰《语林》数卷,号曰《裴子》。檀道鸾谓裴松之,以为启作《语林》,荣傥别名启乎?
《裴氏家传》认为裴荣撰写了《语林》,从其性格来说,“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似乎也适合撰写《语林》,这里的裴荣与裴启是否为一人,不能确定。两人的共同之处,除了姓氏以外,籍贯也是相同的,都是“河东人”,刘孝标说:“荣傥别名启乎?”他姑且提出了疑问。不过,后世文献(《隋书·经籍志》《说郛》《玉函山房辑佚书》《古小说钩沉》等)都是把裴启作为《语林》的作者。
关于裴启的社会身份,《隋书·经籍志》云:“《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隋书》说他是一名“处士”,何谓“处士”?颜师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一》曰:“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李贤注《后汉书·刘宽传》曰:“处士,有道艺而在家者。”处士是有一定才华,但是未仕或不仕的人。裴启是一名处士,这也是史书没有裴启传记的原因之一。
简言之,《语林》是东晋隆和年间(362—363)处士裴启撰写的一部描写名士言行的志人小说,曾一度很受欢迎,并且比刘义庆(403—444)的《世说新语》早六七十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名士教科书。
二、 《语林》与魏晋风度
何谓名士,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解读。“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后汉书·方术传论》)。魏晋时期的名士沿袭了东汉名士的特点,并发扬光大。魏晋之际,名士特立独行、清峻洒脱,表现出的是一种与众不同、举止不凡的风度,他们言词高妙、旷达不羁、精神超俗、不拘小节、鄙视世俗,为后世所景仰,因此被后世称为魏晋风度。最早有意识地把这种魏晋风度记录下来的,不是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而是东晋裴启的《语林》。
魏晋名士喜爱饮酒,他们也并不是单纯饮酒,而是将饮酒与人生体验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发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感慨。例如《语林》云:
王大叹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酒自引人入胜耳。”(《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八)
王仲祖酒酣起舞,刘真长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北堂书钞》卷一百七)
刘伶,字伯伦,饮酒一石,至酲,复饮五斗,其妻责之。伶曰:“卿可致酒五斗,吾当断之。”妻如其言,伶咒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莫可听。”(《艺文类聚》卷七十二)
一些名士饮酒时不注意礼节,只是一味追求一时的快乐或麻醉,刘伶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典型。当然,名士们热衷于饮酒,甚至于沉湎,并不完全是为了喜好,有时也是为了逃避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而借酒浇愁,表面上他们放纵、洒脱,内心却又常常十分苦闷。宋人评价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事故。”(叶梦德《石林诗话》卷下)饮酒是一种放纵,也是一种解脱,他们通过酒来麻醉自己,以逃避这个无力改变的社會现实。
名士的行为方式也往往异乎寻常,例如《语林》云:
王武子葬,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既作驴鸣,宾客皆笑。孙曰:“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宾客皆怒。(《世说新语·伤逝》第3则刘孝标注)
再如《语林》云:
戴叔鸾母好驴鸣,叔鸾每为驴鸣,以乐其母。(《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九)
“作驴鸣”,对于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而言,是有所顾忌的,但是魏晋名士并不受此拘束,表现了他们的标新立异与特立独行。
魏晋名士注重潇洒的仪表、优雅的气质,社会上也十分倾慕。《语林》云:
(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张孟阳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世说新语·仇隙》第7则刘孝标注)
王右军目杜弘冶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九)
有的名士注重语言的表达艺术,有时令人忍俊不忍,有时使人思绪万千,例如《语林》云: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州门外。须臾,周侯已醉,著白袷,凭两人来诣丞相,历和车边。和先在车中觅虱,夷然不动。周始见遥过,去行数步,复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顾择虱不辍,徐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量地。”(《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一)
顾和在丞相府门前抓虱子,安然自若,周顗指着顾和的胸脯问道:这里面装着些什么?顾和依然捉虱不辍,从容不迫地答道:这里面是最难捉摸的地方。这一问一答,似有所指,又耐人寻味,令人回味无穷。魏晋名士没有矫揉造作和哗众取宠,却表现了他们的恬淡、从容与幽默。
通过《语林》的佚文,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名士的风度,使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魏晋时代。《语林》本来可以与《世说新语》相媲美,但是由于它后来亡佚了,淡出人们的视野,因此,魏晋风度确实是有赖于《世说新语》而得以传承。
三、 谢安与《语林》
东晋裴启在撰写《语林》时,描写了许多当时名士们的嘉行轶事。记载当时的人或事,有可能得到当事人的褒獎,也有可能开罪于当事人,《语林》在流行时,其内容得罪了大名士谢安,遭到了致命一击。《世说新语·轻诋》第24则云: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其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
《世说新语·轻诋》第24则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云:
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垆,司徒王珣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平,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
《语林》中记载了一些谢安的言语,当事人谢安予以了否认,他之所以否定《语林》,一般认为是“记谢安语不实,为安所诋,书遂废”(《中国小说史略》)。事实上,《语林》关于谢安的记载并没有不实之处,谢安否定《语林》是因为裴启赞扬了与谢安反目成仇的王珣。不过,毕竟谢安是大名士,讲究自己的身份,他没有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压制《语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这显然指《语林》记载的内容不实,而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受社会认可的。因此,其负面效应很快显示出来,《语林》受到社会的鄙视。对于这件事的真相当时人无从查证,但从社会影响力来看,人们更倾向相信谢安,而不是裴启。《语林》很快由被社会推崇转向被社会排斥,并在隋朝时便散佚了。
四、 《语林》与《世说新语》
《语林》与《世说新语》颇有渊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相同,叙事方式相似,它们都是以名士为描写对象,都是通过简短的语言描写名士们的言谈举止。二是《世说新语》吸收了许多《语林》中的内容,清人马国翰在辑佚《语林》时云:“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取之甚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我们通过与周楞伽辑佚《裴启语林》作对比,《语林》有82则故事与《世说新语》中的故事相同或相似,占现存《语林》185则的44%,也就是说,《语林》中接近一半的故事被《世说新语》所吸收或借鉴。毫无疑问,《语林》是《世说新语》成书的最重要的故事来源。例如《语林》云:
王经,少处贫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语之:“汝本寒家儿,仕至二千石可止也。”经不能止,后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流涕辞母曰:“恨昔不从敕,以致今日。”母无戚容,谓曰:“汝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何负哉!”(《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一)
《世说新语·贤媛》第10则云:
王经少贫苦,仕至二千石,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母都无戚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
《语林》与《世说新语》关于王经及其母亲的故事的记载一致,仅有个别字的差异,而且未见其他书籍记载,这则故事当为《世说新语》摘录于《语林》。所以,在阅读《语林》中的故事时,给我们的印象是许多都是似曾相识,这是因为《世说新语》摘录了许多《语林》中的故事。
《语林》更多的是裴启的原创,更接近第一手资料,而《世说新语》基本上属于“纂缉旧文,非由自造”(《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因而更能凸显《语林》的价值。作为最早的一部魏晋名士教科书,《语林》也是研究魏晋时期政治、社会、文化、风俗等的重要资料,这是不应被忽视的。
五、 《语林》与唐宋类书
类书是采辑若干古代典籍中相关事物的记载,将其依类或按韵编排,以备检索文章辞藻、掌故事实等,兼具“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双重性质,它对于保存中国古代的散佚之书起到了重要作用。
保存《语林》中佚文的唐宋类书主要有《初学记》《艺文类聚》《白氏六帖事类集》《六帖新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续谈助》等,其中以《太平御览》为最多,共165条。还有一些故事是《语林》独有的,也就是《郭子》《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均未记载,因此文学价值颇高,例如《语林》:
王右军少尝患癫,一二年辄发动。后答许掾诗,忽复恶中,得二十字云:“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诵之,读竟,乃叹曰:“癫,何预盛德事耶?”(《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六)
再如《语林》:
桓宣武性俭,着故裤,上马不调。裤败,五形遂露。(《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六)
虽然通过唐宋时期的类书,《语林》的面貌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语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同一则故事,唐宋类书之间的记载也不尽相同,甚至差异较大,“邓艾口吃”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1 邓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为云‘艾艾’,终是几艾?”答曰:“譬如凤兮凤兮,故作一凤耳。”(《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四)
2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太平广记》卷二)
《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成书于同一时期,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即使如此,它们记载了同样来源于《语林》的故事也有差异。關于“邓艾口吃”的故事,戏言“‘艾艾’,终是几艾”的是宣王司马懿,还是文王司马昭,两书记载是不同的。而陈寿《三国志·邓艾传》中,并未记载究竟是宣王还是文王,究竟孰是孰非,并不能确定。
同一部类书,在引用同一故事时,也有一定的差异,例如:
1 《语林》曰:何平叔,美姿仪而绝白。魏文帝疑其中捋,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太平御览》卷二十一)
2 《语林》曰:何晏,字平叔。以主婿拜驸马都尉。美姿仪,帝每疑其傅粉,后夏月赐以汤饼,大汗出,以朱衣自拭之,尤皎然。(《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四)
3 《语林》曰:何晏,字平叔,美姿容。帝疑其傅粉,赐汤饼,令晏食之,汗出流面,拭之转白。(《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五)
4 《语林》曰:何平叔,面绝白,魏文帝疑其着粉,夏日唤与热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时帝始信之。(《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
另外,《语林》中的故事,很多被稍晚于它的《世说新语》吸收,相比较而言,《语林》原创的成分更多一些,而《世说新语》多为“纂缉旧文,非由自造”。这也正是《语林》的珍贵之处。
六、 《语林》的亡佚与辑佚
唐初《隋书·经籍志》首次著录《语林》,但宣称这部书已经亡佚,此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书目再无著录,因此,在修撰《隋书·经籍志》的唐代初年就已散佚。
不过,后人又通过辑佚的方法,《语林》得到了部分恢复,虽属吉光片羽,但弥足珍贵,从中我们依稀可以见到魏晋小说的面貌以及魏晋风度。元末明初陶宗仪在《说郛》中辑得《裴启语林》一卷,共21则。清人马国翰从《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唐宋类书中辑得152则,收入其《玉翰山房辑佚书》。鲁迅在1909年秋至1911年底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散佚了的魏晋六朝小说,辑录共36种,近8万字,命名《古小说钩沉》,其中裴启《语林》共180则;今人周楞伽在前人的基础上,共辑得佚文185则,此书命名《裴启语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为目前最完备的《语林》辑本。
对于《语林》的辑佚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这些佚文,对于窥探东晋志人小说有重要意义。但是,辑佚很难做到涸泽而渔,即使能做到涸泽而渔也很难做到准确无误,散布在各种类书中的条目也大都经过了增删,甚至有的面目全非,因此,对待《语林》的佚文需要有一个审慎的态度。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