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中国传统的“弃儿”与叛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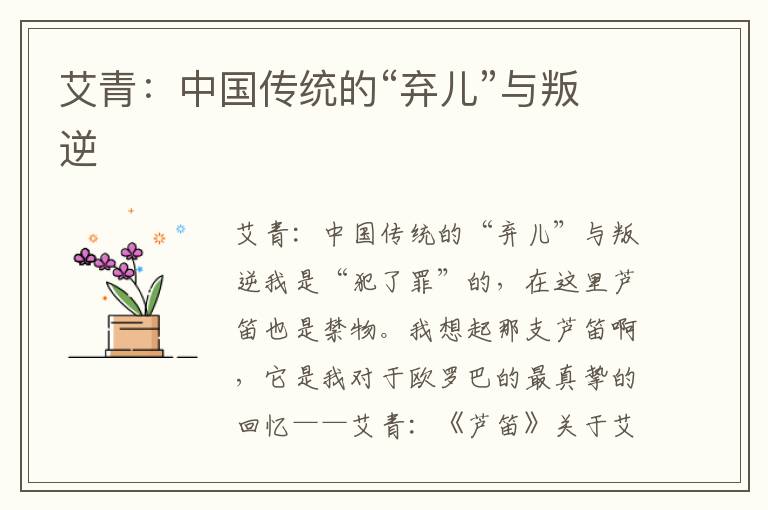
艾青:中国传统的“弃儿”与叛逆
我是“犯了罪”的,
在这里
芦笛也是禁物。
我想起那支芦笛啊,
它是我对于欧罗巴的最真挚的回忆
——艾青:《芦笛》
关于艾青的描述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他与中国现实主义新诗艺术,他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艺术,他与中国新诗的“散文美”取向,他对40年代中国新诗的影响……然而,作为中国30年代走向西方现代诗艺的诸多诗人中的一位,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与当时影响颇大的纯诗选择拉开了距离,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与中国式的现代派诗人如此不同,这些问题仍然期待着我们做出切实的回答。而这些回答显然又都集中在这么一个问题上,即诗人艾青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当中国式的现代派诗人在中西交融的理想旗帜之下折回到中国诗歌传统的纯诗之路时,同样接受西方现代诗艺的艾青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中突破了这一传统,支撑着他对“散文美”的追寻,这种突破最终确立了他在40年代诗坛的地位。发现艾青的胡风回忆了他读到诗集《大堰河》时的感受,他认为这部作品“感情内容和表现风格都为新诗的传统争得了开展”。胡风简短精当的判断启发我们对艾青的诗歌艺术选择做出更深入的说明。
1.“弃儿”艾青
正如胡风是通过《大堰河》认识了艾青一样,艾青的诗歌艺术似乎将永远地与大堰河——这位贫苦朴素的农妇联系在一起了。然而除了对诗人阶级情感的渲染之外,我们似乎还缺少对“大堰河”意义的更深入的开掘。艾青因为“克父母”的恶咒而只能在大堰河那里去寻找一点宝贵的母爱,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培育着一种“地主儿子”对劳动人民的情感,它同时也引导了诗人艾青对人生、对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最真切的感受:一位无辜的孩子,就是因为那场身不由己的出生艰难而丧失了父母之爱,成为父母的“弃儿”,家庭无法收容他这个弱小的生命,父亲、母亲成了“叔叔”、“婶婶”,他只能寄居到另一个毫无干系的农家,这是怎样的创伤和屈辱呢?
传统中国对人的规范和塑造是由家庭内部的人伦训育开始的,但艾青所面对的现实却是,他固有的家庭粗暴地拒绝了那种习见的“温情脉脉”的训育。5岁的“弃儿”艾青终于回了“家”,但迎接他的却是父亲无缘无故的打骂与呵斥。在诗人幼小的心田里,忧郁的阴云由此更加浓重地弥漫开来了。
艾青说:“我长大一点后,总想早点离开家庭。”父亲的冷漠和歧视中断了他受哺于传统人伦关系的可能性,他力图挣脱家庭的包围,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对传统人伦关系及其道德观念的抗拒,叛逆与倔强因此在艾青的精神世界里生长起来。到后来,艾青留学巴黎的时候,一方面是父亲断绝了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他顽强地打工过活,两方面的力量都在加固着诗人的叛逆之路,以至到了父亲病危和去世这样的时刻,艾青竟都拒绝回家“尽孝”。在诗中,他坦言道:“我害怕一个家庭交给我的责任,会毁坏我年轻的生命。”“我走上和家乡相反的方向”,“在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我的父亲》)。在家中,艾青是长子,一个拒绝承担“家庭责任”的长子,这在现代中国作家的“长子”行列中,也是沙见之极的,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他对自我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体验首先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一个和谐的家庭可能会让他感到舒适,也可能从中学会顺从和忍让,学会牺牲自我的“适应”;相反,一个冷漠的家庭可能会让他备感孤独,但也可能会激发叛逆与反抗之情,并决定他在以后的人生中保持自我的独立。从叛逆之路上走过来的艾青确乎保持了更多的个性与自我。如果将反叛家庭的艾青与相对温和的另一位诗人田间作一对比,看一看他们各自最终的文学取向,那肯定会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
反抗父性权威似乎先天就包含着一种文化的内蕴。艾青对父亲的背弃和挑战同时与他的文化反叛交相辉映。“从高小的最后一个学期起,我就学会了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的旧文艺。对于过去的我来说,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是比李白、杜甫、白居易要稍稍熟识一些的,我厌恶旧体诗词,我也不看旧小说、旧戏。”“我所受的文艺教育,几乎完全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艺和外国的文艺。”这个故事也经常被后人提起:艾青上初中时的第一次作文,便援用了胡适的名言作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又中他猛烈地抨击了文言文。老师批语道:“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没想到,艾青竟敢在老师的批语上打一个大大的“叉”!
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将古典诗词背得滚瓜烂熟的艾青照样成了诗人,而这样的“一知半解”恐怕恰恰保证了他拒绝传统文学压力之后的一种心灵的自由,艾青不是在反复诵读中国古诗的过程中触摸世界并最终成为诗人的,他的诗歌灵感是在对世界的直接感触中获得的,他甚至首先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借重画家的眼睛和手在后来写出了流动的诗行,这样的诗人似乎更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味道。
2.先锋派艺术的反传统
今天人们比较容易注意到绘画艺术对艾青诗歌的影响,却可能会忽略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即艾青原本无意走进诗歌艺术的殿堂,他在孩提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是对美术的浓厚兴趣:一位无意成为诗人的画家最终竟成了诗人,这样的艺术之路不也是逸出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吗,艾青18岁进入杭州西湖艺术院绘画系,半年后在林风眠院长的建议下赴法留学。他此时的初衷和以后不时流露出的意趣都一再证明成为画家才是艾青最执著的愿望,而诗歌好像倒有几分“业余”的味道——众所周知,就是在北京解放的时候,艾青因受命接管中央美术学院,他“又一次燃起对重新搞美术工作的希望,这个希望是很强烈的”。如果不是后来的变动,很难说我们就不会再看到一位美术家艾青。
但更有意义的在于艾青所选择的美术之路对他的诗歌艺术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恰恰在30年代的其他诗人那里很少看到。
在巴黎,艾青失去了父亲的经济支持,他半工半读地学习着绘画。半工半读使得他没有机会进入正规的艺术院校,只能到画室里去买票学画。当时的巴黎街头正汇聚着各种才华横溢又富有叛逆精神的先锋派艺术家,于是,他爱上了“莫内、马内、雷诺尔、德加、莫第格里阿尼、丢飞、毕加索、尤脱里俄等等。强烈排斥‘学院派’的思想和反封建、反保守的意识结合起来了”。半工半读也给了艾青更多的自由读书的机会,他读着汉译的俄罗斯文学,读着法译的俄苏诗歌,读着法国和比利时的现代诗歌,渐渐地,他“开始试验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瞬即消逝的感觉印象和自己的观念之类,学习用语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形体,美的运动……”一个无意成为诗人的画家就这样成为了诗人。同样,在1934年的中国上海,当美术家艾青已经无缘继续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活动,无力再为“春地画会”出力的时候,他进入了生平第一次的诗歌写作高潮,而且在那么一个飞雪盈天的清晨,创作出了一首长达百行的佳作《大堰河——我的保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
你的关闭了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
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
我是地主的儿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
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艾青以从大堰河那里所感染来的忧郁诉说着世道沧桑、人生变幻,在大堰河不幸的命运当中也渗透着诗人自己作为传统伦常“弃儿”的所有辛酸和屈辱,这些复杂的情感以一种不可遏制的姿态奔涌而出,完全冲出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和谐理想的阻碍,那份厚实的忧郁,那自由不羁的散文式语句,与当时盛行于诗坛的现代派诗歌和左翼诗歌大相径庭。这就是一位传统的弃儿走向叛逆的宝贵成果!
抗战以前的艾青诗歌已经显示了这种反叛中国诗歌传统的基本特色。
艾青诗歌的特色与他走进艺术殿堂的独特方式,与他旅法三年的人生境遇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艾青未能进入法国正规的艺术院校,接受严格的学院式教育,但这样的偶然恰恰又使得诗人叛逆的个性在巴黎的“拉丁区”找到了知音,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反学院派的叛逆性追求鼓励艾青向着自由、健旺和血性充溢的方向发展。绘画如此,用“语言捕捉”感受的诗也同样如此。在艾青诗歌的几乎每一幅画图中,我们都能感到一位现代艺术家所特有的骚动和挣扎:巴黎有过他勃动向前的意志,马赛留下了他爱恨交织的诅咒,乡村“透明的夜”煽动着浪客的野性,透过监牢的狭小的窗口,他目睹那“白的壳的/波涛般跳跃着的宇宙”(《叫喊》)。中国的现代派诗人们认同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反叛传统这一选择,接着又顺着他们的思路折回到了中国自身的传统,而艾青所认同的却是他们反传统这一行为本身,并由此强化了对中国自身传统的反叛,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艾青诗歌的骚动和挣扎完全打破了中国诗歌寻找平衡与静穆的理想,凸现了一个现代中国诗人的全新的人生感受。
当然艾青也舍弃了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中的某些内容,比如它对人的潜意识世界的揭示,对人的形而上问题的叩问以及与此相关的神秘主义色彩等——对于一位从“遥远的草堆堆里”冒险闯入现代都市的中国人而言,这些纯生命意义上的话题似乎还是玄虚了一些,艾青所关心的是现代人的生存的苦痛和精神的搏击。正因为如此,他同时也阅读着俄苏文学,阅读马雅可夫斯基与拜伦、雪莱、惠特曼,他们的豪情同样能够掀动一位正在追求人生、反抗社会压迫的中国青年。艾青的诗歌也特别地感染上了凡尔哈仑的忧郁,这位比利时现代诗人同艾青一样有着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骚动和不安。农民式的忧郁和不屈反抗、不懈追求的努力构成了凡尔哈仑一生丰富的诗歌内涵。“我一生在诗上最喜欢或受影响较深的是凡尔哈仑的诗。”艾青如是说。
3.艾青的“芦笛”
无论是对西方现代艺术叛逆精神的认同,是对苏俄革命诗歌的接受,还是对某些现代西方诗艺的扬弃,艾青都把它们作为自己追求自由、追求个性独立的一部分,后来的人们都依照胡风的概括,将艾青称为“吹芦笛的诗人”。“芦笛”这一语象来自法国诗人阿波里内尔(G.Apollinaire)的名句:“当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在这里,芦笛正代表了诗人的独立与自由。在《芦笛》一诗中,艾青写道,阿波里内尔的芦笛是他“对于欧罗巴的最真挚的回忆”,“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矜的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能够旁若无人地吹奏自己的歌,这是诗人的勇气,也是诗人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读《大堰河——我的保姆》就会发现,这首诗在当时之所以如此动人,恐怕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描写了一个贫苦农妇的遭遇,更重要的是其中流淌着诗人难以遏制的内在激情——一位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在一位朴质憨厚的农妇那里找到母爱,而她却与自己的生活道路有着这么巨大的差异,这爱与痛、恋与怜、悲与悔的复杂嵌合,汇成了一股滔滔不绝的诗情之流。当同一时代众多的中国诗歌在“走向社会”的道路上走失了自我的情感和思想,艾青的这首诗却以诗歌最重要的特质——自我之情唤起了人们阅读的快感,温暖了无数日渐干涸的诗心。
西方现代艺术的熏陶也使得艾青诗歌注意对印象的捕捉和对意象的提炼。在艾青所熟悉的后印象派画家高更和凡·高那里,印象是渗透着艺术家情感的象征与暗示。而引起他很大兴趣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同样倡导主客观的“契合”,着力营造“象征的森林”。这都对艾青自身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他的处女作《会合》一开篇就带上了印象派绘画的意味:“团团的,团团的,我们坐在烟圈里面,高音、低音、噪音,转在桌边,/温和的,激烈的,爆炸的……”在《巴黎》、《马赛》等诗里,艾青运用繁复意象表达错综情感的能力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可贵的是,这样的意象艺术没有堕入陈旧的物我和谐的意境当中,它仍然奔涌在诗人无规则的语言之流里,任由语句在长短参差中裹挟冲撞,生动地映现了现代中国人的复杂感受。
仅就以上这几个方面的特点来看,艾青诗歌足以在中国诗坛上独树一帜,他的叛逆,他的独立与自由,他的意象艺术以及他自由流放的诗句都与当时的许多中国诗歌(包括现代派诗歌与左翼诗歌)大相径庭。艾青之于“密云期”中国诗坛的位置不禁让我们想到了田间。的确,田间的早期诗作——他的情感与意象以及自由的诗行——都似乎有着与艾青相似的选择,不过,平心而论,就诗的感受、艺术探索的开阔与深远来看,艾青留给我们的成果还是要丰富一些。难怪我们读胡风的《中国牧歌·序》和《吹芦笛的诗人》,总能感到两文之间的一点微妙的差异,前者是理性的,仿佛一位高瞻远瞩的批评家面对着一位艺术新秀,满怀爱怜却又不忘谆谆教诲,后者却情绪激荡,仿佛一位苦苦求索的独行者猛然间发现了一位难得的知己,那么激动,那么兴奋,他似乎忘记了学术批评的惯例,只作品读性的玩味,流连在艾青一首又一首的诗歌当中。前者理性地概括着甲乙丙丁,后者简单得只剩下感觉的直写了!
4.在抗战中走向成熟
从抗战爆发直到1941年到达延安,艾青的步履遍布了大江南北,颠沛流离的生活体验再一次拓展了诗人创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他在反叛中国传统诗歌理想、建设新诗现代观念的道路上迈向成熟。
三类崭新的意象出现在艾青的诗歌中,它们分别是“北方”、“战争”和“乡村”。北方的苦难和它的土地一样广阔厚实,看惯了江南明山秀水的艾青从中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心灵撞击,吱呀的独轮推车,古老的风陵渡口,灰黄的沙漠风暴,还有那驴子、骆驼、乞丐,这一切都与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沉痛的记忆联系着,北方让艾青“沉实”起来。为死难者画像,画下那一张破烂的“人皮”,画下那城市的火焰,画下“吹号者”和“死在第二次”的士兵,酷烈的战争给诗人留下了前所未有的血色风、景。而后方的乡村和旷野,那水牛,那小马,那青色的池沼,又总是让诗人浮想联翩,想起生存的艰辛,想起文明的含义,还有自己那割舍不去的土地的“根”。与那些单纯的自我抒发式的浪漫主义诗人不同,艾青所追求的是自我之于世界的更大的辐射力和涵盖力。这样,正是在“移步换景”的过程中,世界丰富的景观充实了艾青的诗感,壮大了他的诗歌精神。
艾青诗歌深度的掘进亦得力于抗战。抗战中的人生复杂而混乱,撑满了诗人的心灵。在这里,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亢奋与颓顿常常是不分彼此地绞缠在一起,撕扯着人也升腾着人。艾青这一时期的诗作继续显示着他把握和处理繁复感情的能力,一对对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诗情”与“诗力”流转在他的笔下:土地的淳朴和悲凉,农夫的愚蠢和执著,战士的惨烈和崇高以及人的死亡和再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的现代魅力得到了尽情的展现。
艾青的诗歌实践还与他自觉的理性探索相互应和着。总结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他张扬着一种充满力量的动态的“诗美”,“存在于诗里的美,是通过诗人的情感所表达出来的,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烁。这种闪烁犹如飞溅在黑暗里的一些火花;也犹如用凿与斧打击在岩石上所迸射的火花”。他总结自己为自由和独立而奋斗的历程,提出:“旧世界的最主要的是发言的自由——而这些常常做不到,因为任何暴君都知道:一个自由发言的,比一千个群众还可怕。”他深刻地指出:“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但“所谓‘体验生活’是必须有极大的努力才能成功的,决不是毫无感应地生活在里面就能成功的”。他充分肯定意象、象征、联想和想象在现代诗歌创作中的意义,同时又竭力宣传新诗的口语化与散文美,“最富于自然性的语言是口语”,“由欣赏韵文到欣赏散文是一种进步”,“散文是先天的韵文美”。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包含着他对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严肃思考:“目前中国新诗的主流,是以自由的、素朴的语言,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致相近的脚韵,作为形式;内容则以丰富的现实的紧密而深刻的观照,冲荡了一切个人病弱的唏嘘,与对于世界之苍白的凝视。”
1941年以后的延安生活似乎给诗人艾青带来了某种稳定性:一个中国人伦传统所遗弃的孩子在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模式中建立着自己稳定的生活,他勿需再漂泊流离了。伴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诗人艺术追求上的叛逆的锋芒也出现了明显的“钝化”——尽管在进入延安的诗人当中,艾青的自我意识和现代艺术精神是保留得最多的一位,但他依然真诚地希望将固有的理想交付给一个憧憬中的未来,并且为自己这一并不完全熟悉的未来做好牺牲的准备,让新时代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时代》)。对于这个时候的艾青,我们似不便再用“弃儿”和“叛逆”的模式来加以描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