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节选)》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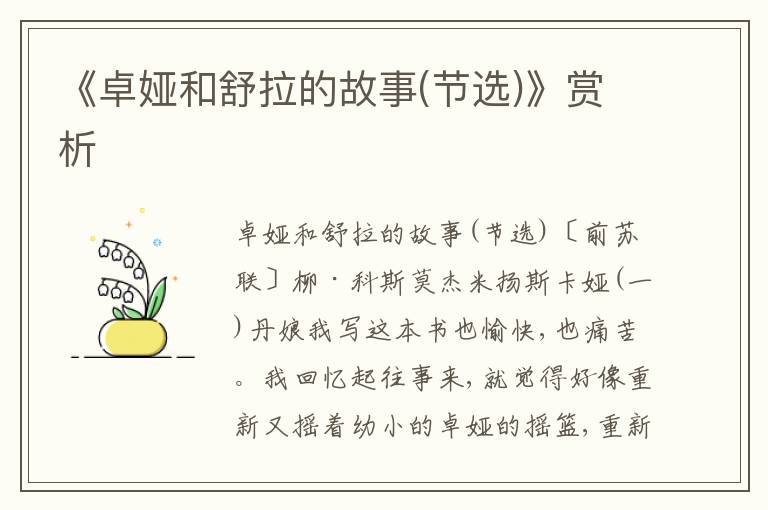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节选)
〔前苏联〕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一)丹娘
我写这本书也愉快,也痛苦。我回忆起往事来,就觉得好像重新又摇着幼小的卓娅的摇篮,重新怀抱着三岁的舒拉,重新看见我的孩子们,看见他俩在一起,活活泼泼,充满了希望。
剩余下的需要叙述的事情越少,我就越痛苦,接近了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越显然,我就越难找到需要的话……
卓娅去后的每一天,连最琐碎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
她走后我和舒拉两人的生活就完全变为期待了。在过去,舒拉回到家里看不见姐姐的时候,他向来问:“卓娅在哪里?”现在他的第一句话是:“没有信吗?”以后他就不把这句问话说出来了,但是我在他的眼神里永远可以看见这句问话。
有一次他很兴奋,很高兴地跑进屋来,并且紧紧地搂抱了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有信吗?”我马上猜中了。
“岂止有,看看是什么样的信呀!”舒拉喊着说,“你听:‘亲爱的妈妈!你现在好么,精神好么,没害病吗?妈妈,如有可能,就是给我写几行字也好哇。我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一定来家里看看。你的卓娅。’”
“哪一天写的呀。”我问。
“11月17日。这就是说,我们等着卓娅回来吧!”
我们又开始等待了,不过现在不像之前那样担心了,而是抱着愉快的希望等待着。我们时刻地等待着,昼夜地等待着,始终在准备一听见推开门的声音就跑去迎接她,我们时时刻刻地准备成为幸福的人。
可是11月过去了,12月过去了,已经要到1月底了……再也没有过信或是别的消息。
我和舒拉都有工作,一切家务事都由他担当起来了。我看出来了:他想在所有的事上都代替卓娅。如果他先回到家来,他就为我温上汤菜。我看见过他在夜间起来给我加被,因为那时候木柴得来已经困难,我们尽可能地节省燃料。
有一次——这是在1月底——我很晚才往家走。通常都是这样,我每逢很疲倦了,就仅仅无意地听到一些路人谈话的片段。那一夕在街上处处听人们说:
“今天您读《真理报》了吗?”
“您读了里多夫的那篇文章吗?”
在电车上有一位脸色憔悴、眼睛很大的青年女子对自己的同伴说:“多么动人的一篇通讯啊!多么好的姑娘啊!……”
我了解了今天的报上一定登着什么不平常的东西。
“舒拉,”我回到家里说,“今天你读了《真理报》吗?据说在那上边有一篇很使人注意的通讯。”
“读了,”舒拉眼不看我,简单地回答道。
“关于什么事呀?”
“关于一个青年女游击队员丹娘。德国人把她绞死了。”
屋里很凉,我们已经习惯这样了。但是这会儿我觉着我的内脏全凉了,全紧缩了。我想:“这不知是谁家的女孩子,家里也一定等待着她,一定也替她担心呢……”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无线电广播,先是一些关于战争的报告和劳动战线上的消息。忽然广播员说:
“现在我报告登在今天(1月27日)的《真理报》上的里多夫的一篇通讯。”
于是悲伤愤慨的声音就开始述说,在12月上旬在彼得里斜沃村德国人怎样杀害了女游击队员、青年团员丹娘。
舒拉忽然说:“妈妈,我把它关了,行不行?明天我需要早起。”
我觉着奇怪:舒拉向来睡得很酣,大声说话和无线电声音全不妨碍他睡觉。我本来很想听到完,但是我终于把扩音器关了,对他说:“好吧,你睡吧……”
第二天我到青年团区委去了:可能那里知道关于卓娅的什么消息。
“任务是秘密的,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信。”区委书记对我说。
又过了几天难熬的日子,在2月7日(这个日子我永远忘不了),我回到家来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妈妈,青年团区委请你到那里去一趟。
我想:可等到啦!一定是卓娅托谁带来了消息,也可能是信。
我像飞似的跑往区委去了。那一夕很黑,刮着风,电车没开驶,我差不多跑着,常常滑跌,起来仍继续跑,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一点儿关于惨事的思想。我没预料到有什么坏消息,只是想知道:几时我能看见卓娅?她能快回来吗?
到区委以后,他们对我说:“你们走岔啦。您回家去吧,莫斯科团市委的人到您家里去了。”
“快,快知道卓娅在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是走,而是跑回家去了。
我推开门就愣在门槛上了。有两个人离开桌子起身迎我来了:齐米列捷夫区文教局局长和另一个不相识的、脸上表情严肃并且微微紧张的青年人。由他嘴里冒着蒸气——屋里冷,谁也没脱大衣。
舒拉靠窗站着。我看了看他的脸,我们的视线遇着了,我就忽然了解了……他扑向我来了,并且还碰倒了什么东西,可是我好像腿被钉在地板上,丝毫不能动了。
这时我就听见有人说:“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您读了《真理报》上关于丹娘的那篇通讯了吗?那是您的卓娅……日内我们到彼得里斜沃去。”
我颓然倒在有人送过来的椅子上了。我没有泪,也没有呼吸。我只希望快快地剩下我一个人,在脑子里总是这一句话:“她牺牲了……她牺牲了……”
……
舒拉把我安置在床上,并在床边坐了一整夜。他没有哭。他的眼睛没有泪,只是向前凝视着,双手紧握着我的手。
“舒拉……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好容易我才说出来。
一向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舒拉,这时候就倒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
“我早已知道……我全知道,”他呜咽地重复说,“那时候《真理报》上有照片啊!脖子上带着绳子……虽然是另外的名字……可是我了解是她……我知道这是她……我不愿意对你说。我想,我可能错认了……我就想是我错认了。我不愿意相信。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给我看看。”我说。
“不!”他呜咽地回答说。
“舒拉,”我说,“还有很多事摆在我前边哪。我还要看见她哪。我要求你……”
舒拉由上衣的里袋里掏出了自己的日记本子:在洁白的一页上黏着由报纸上剪下的四方的一块。这时候我看见了她的骨肉相连的、亲爱的、受尽折磨的、不动的脸。
舒拉还对我说了些什么话,可是我没听见,忽然我耳朵里听见了他的一句话:
“你知道她为什么说她叫丹娘么?你还记得丹娘·索罗玛哈吗?”
那时候我就回想起来了,并且马上了解了一切。是,毫无疑义,这是她回忆着很久以前牺牲了的姑娘,才报了自己的名字是丹娘……
(二)在彼得里斜沃
几天以后我往彼得里斜沃去了。现在我记不清楚是怎样去的。我只记得柏油公路达不到彼得里斜沃,汽车走了差不多五公里土道,都是拖过去的。我们来到彼得里斜沃几乎全冻僵了。人们把我带进一所农舍里,可是我究竟没能暖和过来!内心里冷。尔后我们到卓娅的墓地去了。孩子已经被掘出来了,我马上就看见了她……
她在地下躺着,两手直垂着,头向后扬着,颈上带着绳子。她脸上的表情是完全镇静的,脸完全被打伤了,在一边面颊上有打伤的黑痕。全身被刺刀刺烂了,胸脯上有凝结了的血。
我在她身边跪下看着她……我掀开了她的光滑的额上的一绺头发,这被伤毁了的脸上的镇静又一次地使我惊讶。我不能放掉她,我不能使我的眼睛不看她。
忽然一位穿着红军战士大衣的姑娘走到我身边。她温柔地,但是坚决地搀着我胳膊把我扶起来了。
“咱们到屋里去吧。”她说。
“不去。”
“去吧。我曾和卓娅在一个游击队里。我告诉您……”
她领我进入一所农舍,挨着我坐下,就开始述说。我勉强地,像穿过云雾似的模糊地听着她。有些事我已经由报纸上知道了。她对我述说:有一组青年团员(游击队员)怎样越过了战线。他们在德国人占领地区的林子里住了两个星期。他们在夜里出来执行队长交给的任务,白天他们在雪里睡觉,烤火。他们携带了五天的口粮,可是分用了两星期。卓娅曾和同志们分食最后的一块干粮,最后的一口水……
这位姑娘的名字是克拉娃。她一边说,一边哭。
……以后到了他们返回根据地的时候了,可是卓娅总是说做得太少。她请求队长许可她潜入彼得里斜沃村里去。
她放火烧了德国人占据着的农舍和部队的马厩。过了一天,她接近了在村子的边缘的另一马厩,在那里有二百多匹马。她由背囊里取出了盛着汽油的瓶子,把汽油洒在目的物上,弯下腰去正要划火柴,这会儿一个卫兵由后边抓着她了。她把他推开,掏出了手枪,但是没来得及放响,德国人打落了她手里的武器并发出了警号……
克拉娃沉默了。那会儿农舍的女主人,看着炉中的火,忽然说:
“我能告诉你们以后的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也听了她的述说。但在这里还是让我们读彼得·里多夫的通讯好啦。他第一个写了关于卓娅的记事,他首先来到彼得里斜沃村,他追寻着新鲜的踪迹,了解了和问明了德寇曾怎样用酷刑摧残她以及她是怎样牺牲的……
(三)经过情形
……他们把卓娅带进来了,对她指示了板铺。她坐下了。在她对面,在桌子上放着电话机、打字机、收音机和摊着司令部的文书。
军官们渐渐地聚拢来,他们命令房主人(沃罗宁)退出室外。老太太踟蹰不去,一个军官就对她叱责:“老婆子,滚!”并且捣了她的背。
德寇军一九七师三三二步兵团团长留得列尔中校曾亲自审讯卓娅。
沃罗宁坐在厨房里究竟还能听见屋里的事。一个军官发问,卓娅(她就是在这会儿报的丹娘的名字)不迟疑地、大声地、不谦逊地回答。
“你是谁?”中校问。
“我不告诉你。”
“是你放火烧了马厩吗?”
“是我。”
“你的目的?”
“消灭你们。”
沉默。
“你在什么时候通过了战线?”
“在星期五。”
“你来得很快呀。”
“那么还愣着是怎么着?”
又曾问谁派卓娅来,她的同伴是谁。他们曾要求她交出自己的同伴来。隔着门传来的回答是:“没有”,“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不说”。以后在空中有皮带的哨音和鞭打在身上的声音。几分钟以后,一个青年小军官由屋里跑到厨房,两手抱着头,闭着眼,堵着耳朵,直坐到刑讯终了。连法西斯的神经都受不住了……
四个体壮的男子解下皮带打卓娅。据房主人计算,他们打了二百下,可是卓娅始终没发出任何呼疼的声音。以后她仍是回答“不”、“不说”,只是她的声音比以前低了……
留得列尔刑讯卓娅的时候,一个叫卡尔·鲍尔连的士官(以后被俘了)曾在场。他在自己的口供里曾写道:
“你们人民的小女英雄始终是坚毅的。她不懂什么是背叛……她冻得发青了,伤口流着血,可是她什么也没说。”
卓娅在沃罗宁家里过了两小时。审讯后他们把她带到了瓦西里·库里克的农舍里。卫兵押解着她,她仍然是被剥去了衣裳,赤足在雪地上走。
她被带进库里克的农舍的时候,在她的额上有大块紫黑色伤痕,在她的臂上和腿上全是伤痕。她气喘不息,头发蓬乱,在汗珠遮盖着的高额上黏着一绺一绺的黑发。姑娘的双手在背后绑着,咬破了的嘴唇肿了。一定是她在受刑的时候自己把嘴唇咬破了。
她坐在凳子上。德国卫兵守门站着。她安静不动地坐着,以后她要求喝水。瓦西里·库里克走近了水桶,但是卫兵抢到前头去,他拿起桌上的煤油灯送到卓娅嘴边。他想用这个说明应该用煤油灌她,而不是用水。
库里克开始为姑娘求情。卫兵最初一点也不通融,后来才让步了,许可给卓娅水喝。她贪婪地喝了两大杯水。
一群驻守在这屋里的德国兵包围了姑娘,肆意地取笑她。有的用拳头触她,有的用燃着的火柴烧她的下颚,还有一个兵用锯刺她的背。
兵士们取笑够,就睡觉去了。那时候卫兵端着步枪对准卓娅,命令她站起来走到室外去。卫兵在卓娅身后跟随着,他的刺刀差不多就触着了卓娅的背。后来他喊了一声“向后转!”他又往回去的方向带着卓娅走,仅仅穿着衬衣的卓娅,赤着脚在雪地里来回地走着,直到那个刽子手自己冻得再也挺不下去,需要回到温暖的屋里的时候,才让卓娅回屋里去了。
这个卫兵由下午十点钟看着卓娅直到下半夜两点钟,每隔一小时他就带卓娅到外边冻15到20分钟……
新卫兵接岗了,他许可了不幸者躺在凳子上。
库里克的妻子偷了个空和卓娅谈话。
“你是谁家的呀?”她问。
“您问这个干什么呀?”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我是莫斯科人。”
“有父母吗?”
姑娘没回答。她一动也不动地躺到早晨,她再也没说什么话,并且虽然脚已经冻坏了,一定很疼,可是她并没呻吟。
清晨,德国兵们开始装置绞架。
库里克的妻子又开始和卓娅谈话:
“前天是你吗?”
“是我。德寇烧死了吗?”
“没有。”
“可惜。焚烧了什么呀!”
“他们的马烧死了。听说,兵器也烧毁了……”
上午十点钟军官们来了。其中的一个又问卓娅:
“你告诉我,你是谁?”
卓娅没回答。
“你告诉我,斯大林在什么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卓娅回答说。
以下的审讯,房主人没听见——他们被由屋里推出来了,在审讯完了的时候才放他们回去。
德国兵们把卓娅的物件拿来了:一件短袄,裤子,袜子。她的背囊也在这里,里边放着火柴和盐。帽子、皮上衣、毛绒上衣和皮靴全没有了。士官们已经把这些东西分赃了,手套落在军官厨房里的红发厨子手里了。
他们给卓娅穿上了衣裳,房主人帮助卓娅往发黑了的腿上套上袜子。他们把没收来的她的汽油瓶子和一块写着“纵火犯”的木牌挂在她的胸前,就把她带到立着绞架的广场去了。
刑场上由十几名亮着刀的骑兵、一百多步兵和几个军官包围着。
地方居民奉命在这里集合看行刑,但是到场的人很少,也有的到场站一会儿就溜回家去了,以免亲眼看这惨不忍睹的事件。
在由绞架上放下来的绳套下边,叠着两只木箱。他们把姑娘抱起放在木箱上,把绳套套在她的颈上。一个军官拿着他的“柯达”照相机开始朝着绞架对光。警卫司令向刽子手打了一个等待一会儿的手势。
卓娅利用这个机会向着集体农场男女农民大声清脆地喊道:
“哎,同志们!你们为什么愁苦地看着哇?你们壮起胆子来,奋斗吧,打法西斯,放火烧他们,用毒药毒他们吧!”
旁边站着的德国人挥动了手,不知是要打她,还是要堵她的嘴,可是她挡开他的手继续说:
“我不怕死,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幸福啊!”
摄影师由远处和近处都对绞架拍照,现在他又在对光,打算由侧面拍照。刽子手们急躁地望着警卫司令,警卫司令就对摄影师喊了一声:
“快,快!”
那时卓娅就转身对着警卫司令和德国兵士们大声喊道:
“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两万万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全绞死。有人替我报仇。兵士们!趁着还不晚,快投降吧:胜利迟早是我们的!”
刽子手扯紧了绳子,绳套勒紧卓娅的咽喉。卓娅双手挣松了绳套,用足尖挺身站着,用全力喊道:
“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斯大林一定来到!……”
刽子手用他的钉着马掌的皮鞋踹着木箱,木箱在踏实了的、滑溜的雪上“嘎嘎”响着。上边的木箱“咚”的一声落在地下了。人群闪开了。有人惊绝地吼叫一声,马上又沉寂了,由林边立刻传出一个回声来……
(四)舒拉
我和舒拉两人的苦难日子开始了。我们不再等待了,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在过去,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希望和信念的——我们希望团圆,相信我们能再看见和搂抱我们的卓娅。每次走近邮箱的时候,我都抱着希望看看它:它可能给我们传来关于卓娅的消息。现在我们由它前边走过去连看也不看它了,我们知道,在那里没有寄给我们的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可能给我们带来欢喜的东西。
我父亲由杨树林寄来了一封非常悲伤的信。卓娅的死严重地打击了他,他在信里写道:“我不了解。怎能这样?我,老头子,倒活着,可是她没有了……”这几行字里含着多少无法解除的痛楚和悲伤啊!全篇信上都是泪痕,有几个字我始终没有能认出是什么来。
“可怜的老人们……”舒拉读完信小声地说。
舒拉现在是我的依靠,我仗着他活着。他尽可能多抽出时间陪伴我。他在过去像怕火一样怕表示温情,可是现在却对我很温柔了。现在他总是用他从五岁以后再也没用过的“好妈妈”三个字来称呼我。现在他已经注意过去他所忽略的事了。我开始吸烟,他就注意到了:如果我吸烟,那就是距离落泪近了。看见我找纸烟,他就注视着我的脸,走近我说:
“你怎么啦?不要这样。我请求你,我请你不要这样……”
如果夜里我不睡觉,他总能感觉出来。他走近我,坐在床边,默默地抚摸我的手。他走后,我就觉得我是被抛弃了,无依靠了。舒拉成为家长了。
……
舒拉要走。他要上前线,并且无论什么也拦不住他。他对我什么也没说,一句话也没告诉我,并且他还未满十七周岁,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要走。
我并没想错。有一天下午我回家来,我还在走廊里就听见了喧吵的谈话,打开门后我看见五个人在一起坐着:舒拉、瓦洛嘉·尤里耶夫、沃洛嘉·奇托夫、聂杰里柯和尤拉·布娄多,每人嘴里衔着一支纸烟,屋里烟雾腾腾。在这以前我向来没有见过舒拉吸烟。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只问了一句。
“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舒拉很快地,好像拿定主意了似的回答我,“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就要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了。我们已经被录取了。”
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了……
舒拉在夜里坐在我的床边说:“好妈妈,你想想,请你想想吧!没有关系的人都给你写信说:‘我们一定替卓娅报仇。’可是我,卓娅的亲弟弟,能留在家里吗?我有什么脸见人哪?”
我没说话。既然那会儿我没找到可以拦住卓娅的话,现在我又怎能找到什么话拦住舒拉呢!
……
1942年5月1日,舒拉走了。
他指着自己的朋友这样说:“人们都不送他们,你也不要送我,好不好?不然的话,他们是要觉得委屈的。你就祝我一路平安吧。”
我恐怕我的声音不服从我,所以我仅仅默然地点了头。儿子又搂抱了我一次,热吻了我一次,就由屋里走出去了。“砰”一声房门关上了。这一次就完全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几天以后由杨树林寄来了信,父亲在信里写道:“母亲逝世了。她没能经得住卓娅死耗的打击。”
(五)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消息
舒拉差不多每天给我写信。他和他的朋友们被编在一个班了,他玩笑地称呼这个班为“莫斯科第二〇一校第十年级乌里扬诺夫斯克分班”。
他在最初的一封信里这样写着:“唉,妈妈,什么我也不会!连按规矩在行列里走步子都不会。比如,今天就踩了人家的脚后跟了。也不会给队长敬礼,为了这个人们不能夸奖我呀。”
光阴在过着。在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像野兽一样工作着。我已经很好地熟悉了步枪、手榴弹、七星手枪。日前我们到射击场演习由坦克里射击去了。我的初步成绩还算正常:由坦克里的炮和机枪射击四百和五百米距离的目标,我的成绩是‘好’。现在你认不出我来了:现在我会很好地给队长们敬礼了,走步子也走得漂亮了。”
在接近考试时期的时候,舒拉在每一封信里都恳求我:“妈妈,如果可能的话,你给我找来一条宽皮带;如果更可能,找一副武装带。”几天以后仍是:“妈妈,你好好找找!你想,如果我的皮带一点儿也不像样,我还像一个什么军官呢?”舒拉小的时候的固执的眼睛通过这些字行注视着我。他在童年时候,如果他极希望得到什么,他就这样,差不多也用这些话要求我。
现在我眼前放着一百封舒拉的信。我由第一封到最后一封地重读它们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的孩子怎样成长,怎样壮大。
(六)“我很愿意活下去”
1943年11月24日给我送来了新的辛酸。在报纸上登出了五张照片,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波塔波夫村外一个被苏军击毙的希特勒的军官身上找到的。德国人把残害卓娅的景况和她的最后几分钟全拍了照片。我看见了雪中的绞架,看见了我的卓娅,看见了我的女孩子在德寇包围之中,看见了挂在她胸前写着“纵火犯”的那块木牌……也看见了那些残害她的人。
……可是舒拉一直没有信。又过几天,我打开《真理报》,忽然在第三版上看见了这样的消息:
“前方军报,10月27日(电讯)。某部正在激烈战争中,扫荡着德寇第一九七步兵师的最后残匪。1941年11月在彼得里斜沃村残杀了英勇的女游击队员卓娅的,就是这一个师的官兵。在《真理报》上刊登的五张德国人残害卓娅的照片,掀起了我们的战士和军官的新的愤怒的热潮。在这里,卓娅的胞弟、青年团员、坦克手、近卫军少尉舒拉正在英勇奋战,为姐姐复仇。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卡威’坦克在舒拉同志的指挥下首先闯入敌人阵地,击毙和用齿轮轧毙很多希特勒匪徒。少校维尔什宁。”
舒拉活着哪!
为姐姐报仇哪!
从此我又常接到舒拉的信了,但不是由和平的乌里扬诺夫斯克,而是由最火热的战场上寄来的。
1944年元旦,很响的门铃声把我惊醒了。
“这是谁呀?”我纳闷地说,开门之后,意外的事就使我愣住了!舒拉站在我眼前了。
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巨人了,英俊、宽肩,穿着带有严寒气味的军大衣。他的脸由于风吹和疾行发红了,冰霜在他的浓眉和睫毛上融化着,他的两眼欢喜地闪烁着。
“为什么这样看呀,不认识我了吗?”他笑着问。
“我看这是伊利亚·木罗米茨俄国民间传说中的大勇士来了!”我回答说。
这是最出乎意料的、最宝贵的新年礼物。
舒拉也无限地欢喜。他一步也不离我,如果他需要到街上去买香烟或散步,他一定像小孩那样请求:
“咱们一块儿出去吧!”
他每一天重复几次同样的话:
“你告诉我,你生活得怎样?”
“我都给你写去了……”
“写算什么呀!你讲给我听吧。人们还照旧给你写信吗?你把信给我看看……来,我帮助你写回信……”
这样的帮助正是需要的,无数的信件依然像河水一样地流来。人们直接给我写,往卓娅的母校写,往报馆写,往青年团区委写。
(七)壮烈地牺牲了
4月20日我在信箱里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是舒拉的战地邮政号码,但是地址并不是他的笔迹写的。我怕拆开这封信,拿着它愣了很久。以后终于拆开它读了最前的几行。眼前发黑了。我换了一口气之后重新又读,仍是读不下去。以后用尽所有的力量,咬紧牙,勉强读完了。
1945年4月14日。
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
很痛心地给您写这封信。我求您:集中勇敢和坚毅。
您的儿子、近卫军中尉亚历山大·阿那托利维奇在反德国侵略者斗争中壮烈地牺牲了。他把自己的青春的生命献给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了。
我告诉您:您的儿子是英雄,您可以因他而骄傲。他曾忠实地保卫祖国,他堪称为他的姐姐的好弟弟。
您把您的仅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儿女,都献给祖国了。
在哥尼斯堡郊外的战役中,舒拉的战车在4月6日首先强渡了30米宽的水渠,猛轰敌人,消灭了敌人的炮兵队,炸毁了军需仓库,并击毙希特勒匪军官兵60人。
4月8日他的战车首先闯入克尼根·路易金堡垒,俘敌350人、完整坦克9辆、汽车200辆,并获得燃料仓库一处。在战斗中,舒拉由战车指挥员升为中队指挥员。他虽年轻,但是指挥中队很胜任,并且在执行一切战斗任务上都可称为模范。
昨天他在争夺哥尼斯堡西方的非布鲁定克鲁格村落的战斗中牺牲了。那一村落已经落在我们手里。您的儿子在最前头的队伍中间闯入了那个村落,击毙希特勒匪徒40余人,并轧毁反坦克炮四门。爆炸的炮弹永远地夺去了您的亲爱的,也是我们的亲爱的舒拉的生命。
战争与死亡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死于我们的胜利的前夕,就令人特别惋惜。紧握您的手。希望您勇敢。
(衷心尊敬您和同情您的近卫军中校列盖札)
……
4月30日我飞到了维尔纽斯,由那里乘汽车到达哥尼斯堡。空虚,周围的一切都被破坏了。片瓦无存。哪里也不见人影。以后来了一串一串的德国人:他们徒步走着,推着独轮或四轮小车,载着家产,他们不敢抬头,不敢正视……
以后涌现了我们的人的洪流,他们是返回故乡的。他们有乘马车的,有乘汽车的,有步行的,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欢喜的,幸福的。由这一切都可以看出:胜利并非道远路遥,它很近了。它就挨着我们了。
舒拉问过我若干次:“妈妈,你怎么想象胜利那一天呀?你以为那是在什么时候?真是在春天吧?一定在春天!倘若在冬天,那么,雪是一样要融化的,花一样要开的!”
现在胜利临近了。这已经是胜利的前夕,幸福的前夕。可是我坐在我的孩子的棺材旁边,他像活人一样躺着:容貌是安静的,明朗的。我没预料到我们会这样见面。这实在是超过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事……
后来,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舒拉的脸,往上看了看,我看见了另一个青年的面孔。我仔细地看他,可是想不起来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他:那时很不容易思索什么,回忆什么了。
“我是沃洛嘉·奇托夫。”青年小声地说了。
马上我就想起了那年4月,当我回到家来遇到舒拉和他的朋友们在高兴地谈话的那一个晚上。“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我们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我仿佛又听到儿子的声音了。
“其余的人们呢?”我勉强地问。
沃洛嘉告诉我说,尤拉·布娄多和瓦洛嘉·尤里耶夫牺牲了。他们也像舒拉一样,没等到胜利就牺牲了……多少青年,多少好人都没等到这一天就牺牲了!
……
……恐怕我不能有系统地、详细地把在哥尼斯堡的两天的事述说出来了。但是我记得人们曾怀着什么样的敬爱谈论舒拉。
我听见人们的一些话:“他勇敢……是一个谦虚的人,是多好的同志呀!年轻,可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我永远忘不了他!”
以后我就回来了。舒拉的坦克的射击手萨沙·斐基柯护送着我。他一路上像照顾病人那样照顾我,像儿子那样关切我;不问我他就猜到了需要做什么。
……
5月5日在诺伏捷维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娅的坟的对面又添了一座新坟。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仍在一起。
这是胜利之前四天。
5月9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着人像长河一样流过去:走过的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个整个家庭,全是狂欢的、幸福的。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
……
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再看见蓝天了,不能再看见鲜花了,他们永远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们为了别的孩子,为了在渴望已久的这一刻在我眼前经过着的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训练提示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前苏联作品。它从一位母亲的角度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己的两个儿女为了祖国,为了和平,离开课堂,走上战场,牺牲在敌人的绞架上和战火纷飞的胜利前夜。他们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书写了什么是英雄,什么是生命的永恒。书中有母亲对儿女的亲情、惦念、痛苦与欣慰的真诚袒露,情感细腻、自然,生活细节丰富,是一部难得的动人的自述体作品。我们仿佛从中看到了充满朝气和坚毅的卓娅,在漫天风雪的夜里,光着脚,身着单衣,带着满身的伤痕,在敌人的刺刀威逼下行走在野外;我们看到卓娅脖子上套着绞索,却仍大声怒斥敌人,呼唤人民起来斗争;我们看到年轻的舒拉闪动着温柔的目光劝慰母亲;我们看到身着军装的舒拉指挥着坦克屡屡冲毁敌人的堡垒,冲向敌群;我们看到母亲望着女儿被处决时拍摄的照片心痛无比;我们看到母亲坐在儿子的棺材旁注视着已经离去的年轻指挥官——为了祖国和自由,母亲在短短的时间里失去了至亲至爱的一双儿女。她虽有普通人的心痛与悲哀,更有英雄母亲的坚忍与胸怀。当时全苏联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给她写信要做她的儿女。20世纪50年代,英雄的母亲还来过中国,受到我国人民的尊敬。当时,也有不少中国青年纷纷给她写信表示要向她的儿女学习!
这部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应当还有两点:一是它记录了真实的时代、人生历程、人物心理;二是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英雄人物,也使我们体验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激起我们反对战争的强烈心声和坚定信念。
值得关注的是,书中不仅写出了卓娅和舒拉这两位青年英雄,同时也表现了战地记者彼得·里多夫及舒拉的同学们等等同样在战争中献身的英雄们(因为篇幅所限,我们没能选取这些内容)。正是彼得·里多夫这位《真理报》的战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前去采访,首先报道了卓娅的英雄事迹,起到了在残酷斗争中鼓舞人心的作用。然而,他却牺牲在胜利前夜,是在波尔塔瓦郊外的飞机场,他要看看战士们如何抗击来袭的敌机就由掩蔽部下边跑出来了,他打算写一篇记事,一切都想亲眼看一看。这是一位真正的战地记者!遗憾的是,他没能兑现给卓娅母亲的承诺:战后一定写一部关于卓娅的书。
我想,我们之所以要选择这部自述体的作品,不只是为了训练学生们对这类作品的表达技巧,更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历史,知道今天,感悟责任。
1.应当阅读全书,了解时代、地域与人物。对卓娅和舒拉有一种全方位的了解,才能热爱人物,抓住人物,表现人物。
2.把握自述体的语言表达特点。
3.把握母亲的心理、心境的变化,应注意分寸,不能基调一沉到底。
4.叙述中的基调、风格应统一,但也要随不同内容、情绪有微调。
5.表达语速不宜快,因是回忆性质、哀痛心境。
6.注意区别叙述语言与书信内容的表达。书信语言表达也要有人物感。
7.注意作品中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的转换和有机结合。
8.可将作品语言做适当修改,进行润色、“移位”等处理。
9.书中的不同人物,都要有相应的语言声音造型,但重在神似。
母亲:用女中音来表现,声音温厚,音色不宜亮,语言内在、多感、稳实。
卓娅:声音明亮、有力度,语言坚定、热烈、内涵深。
舒拉:声音年轻、热情,语言活泼,富于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