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古长沙片鳞》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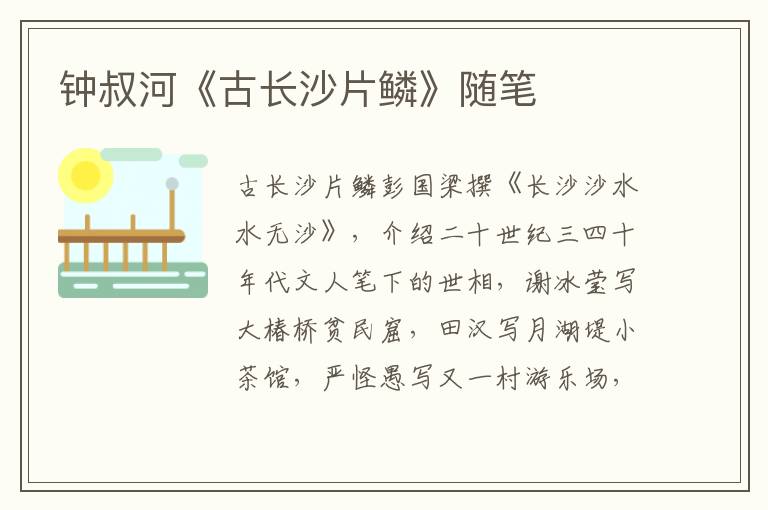
古长沙片鳞
彭国梁撰《长沙沙水水无沙》,介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人笔下的世相,谢冰莹写大椿桥贫民窟,田汉写月湖堤小茶馆,严怪愚写又一村游乐场,都颇有看头,差不多比得上《清嘉录》和《燕京岁时记》一类古人笔记中的描写。
欲知古时本地风土人情,本来只能看笔记,因为这才是当时文人的自由创作,与官修“正史”只记录帝王将相们“相斫”不同。长沙没有《扬州画舫录》和《汉口竹枝词》这样的专书,只有从平常浏览中发现一鳞半爪。
《荆楚岁时记》成书于千五百年前,书名涵盖了长沙,书中写明是长沙的却只有一条:“四月八日,长沙寺阁下有九子母神,是日市肆之人无子者供养薄饼以乞子,往往有效。”记得日本投降后初到长沙,住玉泉山观音庙旁,常见人来庙里烧香求子,四月初八为菩萨生日,香火特盛,许愿还愿者特多,倒不限于求子了,供品则多为水果米糕,并不见薄饼,这和送子娘娘取代九子母一样,都是风俗既在传承又有变化的例证。
宋朝文莹的《湘山野录》作于湖北荆州,长沙亦只寥寥数条,都是写官场的。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倒是写过长沙僧寺开当铺,自称长生库,说六朝时有个姓甄的人“尝以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束苎中得金五两,送还之”,结论是“此事亦已久矣”。束苎即成捆的苎麻,里头的五两银子,猜想是哪个和尚私自藏匿来不及转移的,可见清净之地未必干净,佛寺搞创收由来久矣。
周密《癸辛杂识》也是南宋有名的笔记,云:“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钱)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日(潭指潭州即长沙)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穆陵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做得出皇宫内院御用工匠做不出的东西,说明当时长沙银匠的工艺水平确实是“甲天下”的。但这手艺好像未能传下来,民国时这里的著名银楼余太华、李文玉等,都是江西师傅在掌本了。百工之事本是市廛中很重要的一条风景线,我做过几年木匠,对此类记述尤其感到亲切。
记长沙工匠手艺的,还有民国时杨钧的《草堂之灵》,卷九“记巧工”第一个就是丁字湾的石工邹自运。丁字湾距长沙四十里,盛产麻石(花岗石),这本来只是一种建筑材料,很粗,邹却能将整块石头雕成养鸟的笼子,“精细与竹制者相埒”。“他石匠刻成石马,忽损一耳,请救于邹,邹取铁锤将完好之耳亦行敲去,观者大骇,不知所为,乃徐徐刻垂耳状,较前美观,众人皆服。”有大官宦家想为自己建一座“乐善好施”的牌坊扬名,邹说:“这四个字是不容易做的啊。”要价千二百两。宦家斥其索价太高,他笑道:“工价可以商量,不过我早就晓得,这四个字是不容易做的啊。”其手艺固然巧,辩才则更巧了。
笔记虽然可以写风土人情,写的仍多是作者熟悉的士大夫生活,像上面这些市井和草野间的事情,尤其是限于一地的,就得耐烦披沙拣金,若偶有所得,就格外喜欢。曾读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乃是清朝道光年间长沙一位翰林公的读书笔记,卷六最后一条却介绍了好几首“吾乡土歌”,极为精彩。其二云:
好马不吃回头草,好客不吃路边茶
蜜蜂子不采罢园花
原注:“罢,犹落也,言园中花之将落者也。”其三云:
十里长亭赶送郎,郎去求名到他乡
郎送姐的金心戥,姐送郎的好茴香
其五云:
不曾见灯花会结果,不曾见铁树会开花
好马不受两鞍辔,好船不用两桨划
好女儿不吃两家茶
结语云:“隐语双关,古心艳语,俨然汉魏遗音”,给“吾乡土歌”以极高的评价,真实地将其记录下来,不删不改,态度比“大跃进”时的“采风”好得多。
此书卷九还记过长沙正月初九的“玉皇暴”,三月的“观音暴”,九月的“重阳暴”,说“吾乡谓狂风起为暴”,到现在这还是长沙居民要防备的,所谓“三月三,九月九,无事莫到江边走”也。卷八考订《楚辞》“些”字,“以吾乡音叶之,实读若‘俄’去声,至今长沙一带,每语收声必有此字,其辞涉哀郁者,尤非此不能达也”。上回黄永玉来长沙讨论过这个“些”字,为了说明问题,曾拿了本《山带阁注楚辞》给他看,可惜《思益堂日札》当时不在手边。
(二零零七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