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艳《阳台上的夏堇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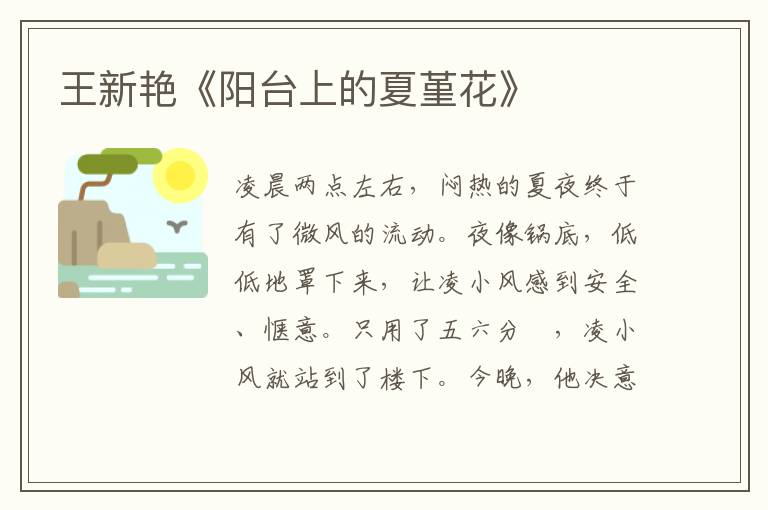
凌晨两点左右,闷热的夏夜终于有了微风的流动。
夜像锅底,低低地罩下来,让凌小风感到安全、惬意。只用了五六分鐘,凌小风就站到了楼下。今晚,他决意要有新的突破。
凌小风深深吸了一口气,均匀的中等体型就像镶进了一根无形的绕指柔钢筋。二十岁,正是身体柔韧性最好的年龄,更何况他还不断地锻炼。这是凌小风最得意的。
只用几个动作,凌小风已经攀住了阳台上的防盗窗棂。阳台最东边的第二三根窗棂他早已做过工作,此刻,只轻轻一拨,一条足以让他通行的路便打开了。
凌小风知道,那盆夏堇就在脚边,这会儿正像她的主人那般,优雅而含蓄地开着花。他仿佛闻到了一种清香,正袅娜地扑向他的面颊。
他轻轻拉动阳台与卧室间的推拉门,一只脚无声地迈进去。
凌小风是奶奶的一棵秧苗,跟着奶奶在农村长大。他记忆中的父亲,高大严肃,至于长的什么脸型和眉眼,他早忘了,可父亲的络腮胡子扎在他脸上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凌小风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个冬天,母亲的脸冻得通红,眼泪被冻成了冰凌,被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拖着,挣扎着上了一辆警车。凌小风眼瞅着那辆警车闪着警灯,神气地消失在村头,母亲的哭喊像陀螺,在他荒芜的心田上旋转。那年,凌小风四岁。爷爷走得早,凌小风一出生就没见过爷爷是什么样子的。从此,奶奶一个人带着小风过日子。在凌小风眼里,奶奶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奶奶乐于助人,村里人有什么事总爱去问奶奶。奶奶总是笑眯眯永不嫌烦地回答着乡邻的问话,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奶奶会插花鞋,会做棉衣单衣,会做漂亮的灯笼和草戒指。谁家女儿出嫁,能得到奶奶亲手做的一双绣花鞋穿在脚上,这姑娘才会觉得自己的幸福看得见,摸得着。村上的婶子、大娘做棉衣前,总会捧着布让奶奶剪裁,觉得只有奶奶裁的棉衣才更合身。夏天时,奶奶用草梗做出很多款式的草戒指,用彩线点缀上,漂亮极了。每逢过年,奶奶自己动手,制作很多灯笼,画上五颜六色的花草、兔子等图案。奶奶做的绣花鞋、草戒指、花灯笼,被凌小风带到集市上,一会儿就卖光了。奶奶的屋里总是很热闹,一群穿红着绿的女子,总爱凑在奶奶的身边。虽说小风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有爸爸妈妈陪着,可小风有奶奶。奶奶说,她是小风的雪被,小风是她的麦苗。
也许是奶奶给小风的太多了吧,小风总想弄懂别人和自己不一样的秘密。小风想知道,别的小孩为何有父有母,而自己却只有奶奶。小风想知道为何要上学,学好了去做什么。小风想知道,长大以后,要和奶奶分开吗,谁管奶奶。小风想到这些时,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秘密,却从不对大人说。初中毕业后,小风再也不想上学了。他想去干一件大事——寻找爸爸妈妈。那年,村里有个小伙伴谢顺子也下了学。谢顺子同样也是无父无母的孩子,打小跟大伯生活。凌小风和谢顺子一拍即合,两个十六七岁的大男孩去了县城打工。
在县城里,他们学过剪发,贴过小广告,当过搬运工,做过小区保安。在金穗小区当保安时,一天,谢顺子气喘吁吁地跑来对凌小风说:哥儿们,你那事儿有眉目了呢。
什么事啊?凌小风一头雾水。
你的大事啊,寻找你爸妈。谢顺子一副得意的样子,就像凌小风的爸妈就是他谢顺子的爸妈一样。
怎么?你问到线索了吗?凌小风两眼发光,呼吸也急促起来。
谢顺子端起桌子上的一杯水,咕咚咕咚地喝完。凌小风赶紧又给他倒满。
谢顺子瞪着小眼睛,神秘兮兮地说,咱这个小区是高档小区,我平常给你留心着呢,问了很多人,今天终于从一个大爷的嘴里知道了一些。你爸凌子春,说出这句,谢顺子突然住了口,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压低声音说,你爸凌子春是抢劫团伙主犯,是因为抢劫被枪决的,这是你吃奶时候的事了,关于这些,咱们村的人也有知道的。枪决你爸的人有好几个,最关键的是当时刑警队的副大队长张杠。听说,执行枪决的两个武警行刑时手打颤,子弹跑偏,两枪后,你爸还大骂警察,是张杠补上了致命的一枪。你妈也是团伙成员,因为涉案数额小些,当时又没被抓现行,再加上你正吃奶,她就逃过了。没承想,等你长大些后,你妈把你扔给奶奶,重操旧业。结果被警察给逮住了,送进了监狱。过了几年,她出狱了,看来是没回家。其实,那次你妈做的数额并不大,全怪逮她的警察。这两个警察我给你翻出来了。一个还是张杠,另一个是当年刑警队的野丫头马葵花。如果不是他们俩,你至少是个有妈的孩子。不像我,一出生,爸妈就得了治不了的病,撇下我双双走了。凌小风,此仇不报非男人,这仇你得报。说到这儿,谢顺子顿了顿,瞅着凌小风的眼睛说,我帮你。
谢顺子一口气说完,眯着胖脸上的小眼睛观察凌小风的表情。
凌小风说,怎么个报法,你倒给我说说看?可能是奶奶从未给凌小风灌输这些思想的原因,也可能是奶奶的爱让凌小风打小就没觉出自己失去太多,这会儿,凌小风显得比谢顺子还木讷。
哥儿们,你可别跟我说,你压根儿没想过报仇这事儿。谢顺子打小被大伯一家虐待,心里的恨比荒原上的草还多。在他心里,已经多次替凌小风想过寻亲报仇的事。
夜里,凌小风躺在床上,回想起谢顺子白天和他说过的话。报仇,报仇,这两个字像从脑子里浮起的一个又一个透明的泡沫,不断地浮出来,又不断地破灭。离开奶奶,外出打工的日子,凌小风越来越强烈地渴望找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打小,凌小风就从村人们口中知道了些关于爸爸的情况,虽说都是碎片式的,零零散散,可聪明的凌小风稍一用心就把这些碎片给拼上了。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爸爸了。可妈妈呢,妈妈去了哪儿?她忘了小风的存在了吗?她忘了这世上还有一个亲骨肉了吗?得找到那两个警察,他们肯定知道妈妈的下落。凌小风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闲暇时,凌小风在谢顺子的帮助下,找到了公安局的家属楼小区——警苑小区。这是一个别致而清新的小区,5A级的物业挂牌,自动识别车辆的大门起落杆,院子里黄色的停车线,不断闪动的监控探照灯,进出楼道门时不约而同的随手关门,都说明这儿管理的规范和戒备的森严。
谢顺子鼓励凌小风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辞职来这儿干保安。凌小风以沉默的形式默认了谢顺子的话。金穗家园的工作辞掉后,懷揣一肚子心事的凌小风率先走进了警苑小区门岗值班室。
来这儿做保安?不知道程序吧,得先考试再政审。你想来就来啊?卫门值班室的一位中年男子毫不客气地说。
考试?考什么啊?凌小风吃惊地问。
考理论考体能考应变力,多着呢。另一个值班员语气稍稍缓和了些。主要是政审,你家族史上没有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的人是最基本的一项内容。门卫不屑地说。
凌小风一听,喊上谢顺子离开了警苑小区。
张杠,张杠。马葵花,马葵花。蝉在纹丝不动的树枝上嘶鸣,一枚又一枚绿叶在焦灼地期待着夜风的到来。凌小风觉得张杠和马葵花就如这蝉鸣一般,搅得他日夜难安。他发誓一定要找到他们俩中的一个。为了寻找心中的目标,凌小风接触了大批的老人,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情,他谎称自己的命是被一个叫张杠的警察救的,他正在寻找张杠报恩。凌小风在救助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后,在老人儿女的帮助下,获得了张杠及其家人的最新消息。原来,张杠在五年前的一次抓捕任务中,被犯罪嫌疑人连捅五刀,伤及重要部位当场死亡。他的妻子女儿和老母亲住在城东的翠苑小区。
翠苑小区位于县城的东半部分,是年代久远的老式居民小区。里面的住户多,人员杂。凌小风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做起了外卖小哥,兼做鲜奶店的送奶工。这样一来,凌小风有机会把翠苑小区的家家户户尽收眼底了。穿着外卖小哥黄黑相间的统一服装,骑着黄黑相间的摩托车,自由出入于各个居民小区,凌小风很是惬意。
在翠苑小区,凌小风经常瞅着行人的神态,谨慎地选择人选,小心地问一句张杠家在哪儿住。慢慢地,他确定了张杠家就在小区最南排最东边单元的二楼东户。掌握了这些情况以后,凌小风在张杠家所在楼的对面,一家叫超兴的繁忙快餐店做了服务员。
阳台是一家子生活的缩影。隔着十米左右的距离望过去,对面的居民楼上,每家的阳台情况各异。有的天天挂着窗帘,只到晾晒衣物时,阳台才露出真面目;有的阳台上种着花花绿绿的植物,有老人经常在打理;有的把阳台改装成了书房;有的阳台是专门供男人抽烟的地方……在翠苑小区,凌小风看得最多的还是张杠家位于二楼的阳台。这家阳台上有一盆夏堇花,开得袅袅娜娜,和偶尔在阳台上闪现的女人相映相衬。
这天,谢顺子跑到凌小风面前卖关子。原来,他竟然打听出马葵花调离了这个小县城,去了遥远的哈尔滨安家落户。
寻仇乃至寻亲的线索终于有了眉目。凌小风感到身上紧绷的一股子劲儿瞬间松弛下来。他想,至少他们中的一个人被找到了,母亲的消息也快了。凌小风买了一架望远镜,趁没人注意时,站在快餐店的一隅,用更多的精力观察翠苑小区张杠家有夏堇花的阳台。
阳台上的衣服一般是三到四天换一批。奇怪的是,这些衣服全部是女人穿的。看来她们家没有男人。也就是说,自张杠死后,这个家再也没有了男人。凌小风瞅着对面张杠家的阳台在心里分析。大女人四十多岁的年龄,体型偏瘦,梳着中长发,远看很有气质。她出现在阳台上,一般是踮着脚晒衣服或收衣服。女孩十二三岁,身材高挑,梳着高高的马尾辫,她出现在阳台上的次数很少,偶尔有几次,凌小风看到她在护理那盆夏堇花。倒是老女人,经常出现在阳台上,有太阳的时候坐着,没有太阳的时候站着,向远方望啊望。
夏天的一个周末,中午,凌小风送快餐来到了这座楼下。未曾想,下来取快餐的正是张杠家的女孩。女孩穿着向阳中学蓝白相间的校服,眼睛忽闪忽闪的,睫毛很长,白皙的圆脸上,有一颗明显的黑痣点在嘴上角。女孩一口一个小哥哥地叫着,十分有礼貌,凌小风的心忽而有了春水的感觉,还起了涟漪。她叫的快餐是一份素馅的饺子。小风心想,一份饺子,如果有时间很快就会包好的。看来,这女孩的母亲平时工作挺忙。
有母亲,真好。凌小风和谢顺子闲下来时经常讨论这个话题。谢顺子说,小风,现在,电视台上不是有一个节目叫“等着我”吗,你也报个名吧,说不定,你妈妈也在等着你的寻找呢。凌小风一只手挠着后脑勺,一只手随意地擦着桌子说,也许,我妈正在寻我,让我等着呢,何必去电视台抖搂这些个陈谷子烂芝麻的发霉事。谢顺子冲着他撇了撇嘴,眼神马上换成了斜视的角度。
张杠这个名字还是经常出现在凌小风和谢顺子的对话中。有一次,凌小风打工的快餐店里,一桌吃饭的客人谈到了张杠。待到确认他们谈的是警察张杠时,凌小风支起了耳朵。
他就是太敬业了,何必这么认真呢,如果不是紧追着那名犯罪分子不放,他也死不了这么早。甲说。
媳妇还在医院工作呢,也没救过来。撇下老的老,小的小,好惨啊。乙说。
他女儿在我们班上,学习很棒,是棵好苗子。我一定让她成材。丙说。
凌小风的心动了一下。他没出声,耳朵却伸到了那桌人中间。
夏夜,繁星满天。大女人收起衣服,抱在怀里,站在阳台上久久不肯离去。对面的凌小风举着望远镜一直瞅着她。她刚下班吗?她在思念张杠?她们家有什么事发生吗?一滴泪从她的脸上划过,接着是一串一串的泪水。
早上七点四十,阳台上的大女人下来了。她穿一件米色连衣裙,米黄色平底鞋,手上提着一只小巧的白色皮包,步行走出小区大门。
凌小风一路跟踪着大女人,直到她走进县医院的大门,走进内科病房。凌小风的心一直怦怦地跳个不停。
向阳小学上学放学的时间,凌小风远远站着,瞅向大门。他看到阳台上的女孩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出来了,周围跟着和她一般大小的三四个女同学。待这群孩子稍稍走远些,凌小风问旁边的一个男孩,你知道前面那个梳马尾辫的女孩叫什么吗?
她呀,谁不知道啊,张杠的女儿,张星。张杠是谁你知道不,大名鼎鼎的刑警,专抓坏人的。男孩说话的样子十分神气。
凌小风的心再次颤动了一下,像被什么扎了一般。他想起爸爸的胡须,想起妈妈的泪水被冻成的两条长长的冰凌线,想起教室里的温暖,想起和同学们嬉戏的场面。再望向张星的背影时,凌小风的目光里竟有了三分肃杀。
老人守着阳台,光阴守着岁月。阳光照在阳台上,把金线一样的光铺洒开来。老女人喜欢上午坐在阳台上望她心中的山水,期盼未归的人。下午,夕阳西下,快餐店里开始忙碌时,正是老女人在阳台上打瞌睡的时光。凌小风会时不时瞟一眼阳台,边想心事边干活儿。不知为何,每次看到老女人在阳台上打瞌睡的样子,凌小风就会想起乡下的家,想起家里的奶奶,想起奶奶做的各种好吃的东西,还有奶奶亲手做的草戒指、绣花鞋、红灯笼。奶奶的身体还好吗?有人陪着她吗?离开家的时间太长了啊。
谢顺子见凌小风迟迟不肯下手,鄙视地冷嘲热讽道,做男人要有血性,骨头里要补点儿钙,杀父之仇都不报的人,在社会上还怎么混?
凌小风通过长时间对张杠家阳台的观察,还有对大女人和女孩的跟踪,心里的认知已不是最初的样子。谢顺子的煽风点火,使凌小风心海里渐渐平静的复仇波涛重新撞击着他的心岸。他把自己的这种感觉告诉了谢顺子。谢顺子说,你小子有种。不过,要做好准备,不打没把握之仗,一定掌握透情况,想好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及退路。有几次,等所有的窗子都关灯后,凌小风和谢顺子趁夜深人静时,悄悄潜入对面楼下。谢顺子望风,凌小风无声无息地爬上张杠家的阳台,双手抓住栏杆,就那样吊在那儿,听夏夜热浪的声音,听每个窗口汇来的梦呓,听旷野里的虫鸣,听树叶与夜的对质,听花朵思念蜜蜂的心曲。直到天色将明,他才悄然离开。几次对张杠家近距离的接触,凌小风神不知鬼不觉地留下了进路和退路。
凌小风无声地从阳台进到卧室里,他明白今天是大女人值夜班的日子,家里只有老女人和女孩。突然,一声痛苦的呻吟把他惊呆了。
适应了卧室里的黑暗后,凌小风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老女人半躺在床上,脸冲外,好像很难受的样子。瞬间,凌小风的眼前闪现出奶奶帮助村人的画面。凌小风果断地打开了床头灯,见老女人的睡衣都被汗水湿透了,床边还有一堆呕吐物。对面的卧室里没有任何动静,凌小风知道那是张星的卧室,也是他今天的目标。凌小风却背起老女人,朝对面的卧室看了一眼,匆匆下了楼。他明白,长时间以来,谢顺子和他费尽心思做的所有计划和努力都白费了。
凌小风背着老女人,脚下如生了风。他急匆匆打了一辆的士,赶到县人民医院,把老女人送进了急诊室。看到老女人被醫护人员围起来抢救,凌小风跑到内科病房,对一个小护士说,麻烦你告诉童燕大夫一声,她婆婆病了,在急诊室。
凌小风慢步走出医院的大门。东边,旭日升起前的红云铺满天空。他想快点儿见到谢顺子,和他说说刚才戏剧性的一幕,他想知道谢顺子脸上的表情。他还想马上回家,抱一抱久别的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