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妮《我的新兵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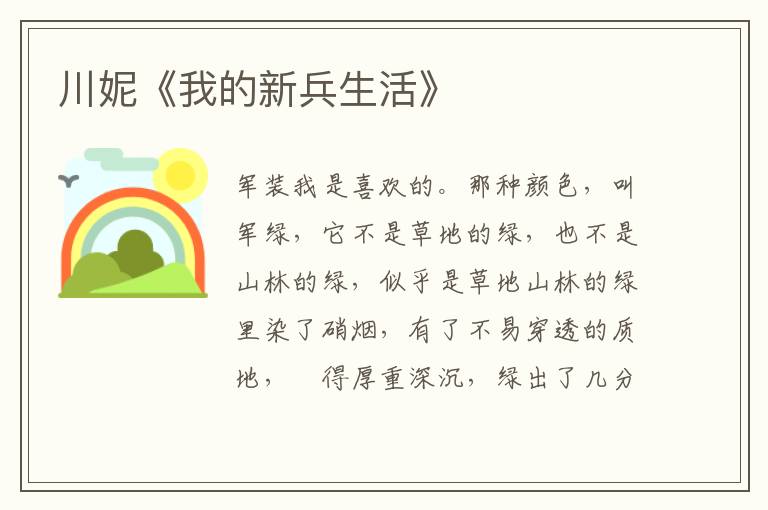
军装我是喜欢的。那种颜色,叫军绿,它不是草地的绿,也不是山林的绿,似乎是草地山林的绿里染了硝烟,有了不易穿透的质地,綠得厚重深沉,绿出了几分思想。就像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子,经历了一番生活的磨难,善良依旧,又于单纯之外,添了坚强,让人不敢轻慢。
1984年之前的军装,虽然经过了1974年和1978年的两次小改变,总体风格还是“六五”式的,它的特点被人概括为:一颗红星头上戴,一面红旗两边挂。“六五”式军装的式样是最简洁的,装饰也极简,只有软帽子上的红色五角星和领子两边的小面红旗。后来的军装式样,完全背叛了这种极简主义风格,走向了繁复。“六五”式军装的裤子肥肥大大,衣服也不收腰,穿在身上,像罩在面口袋里,一米六六的身高,看起来只有一米五八。但是,扎上腰带就不一样了。宽腰带的金属搭扣啪嗒一声,镜子里的形象立马惊天大逆转。一尺八的腰,束在棕色的硬皮宽腰带里,所有的青春气息,都有了一种欲盖弥彰的效果。那条宽腰带,是点化我们青春的秘密武器。睡觉的时候,我们会把宽腰带放进床头柜里,小心保护着。我们最用心对待的,还有穿在军装里面的土白布衬衣。衬衣刚发下来的时候泛着黄,穿在身上粗粗拉拉刺着皮肤。但是,土白布衬衣越洗越白净,布的质地也越洗越柔软。露在外面的白衬衣领子,是判断老兵和新兵的重要标志。很快就有老兵教会我们拼命洗衬衣,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衬衣洗得像老兵那样,又白又柔软。
站军姿和队列训练,我也是喜欢的。在大太阳下面站军姿,是入伍训练的第一课。用教导员的话说,这是我们从老百姓变成军人的门槛。迈过了这个门槛,你就是军人,哪怕没穿军装,往那儿一站,也有一股子军人的范儿。训练我们的班长都不说“站军姿”,他说的是“拔军姿”。军姿训练的第一要素,就是要站得挺拔。收腹挺胸抬头,下巴往里微微收住,双手下垂,中指紧贴裤缝,目光平视前方。拔军姿的时候,千万不能偷懒,不要以为躲在肥大的军裤里,腿的肌肉就可以悄悄放松。训练有素的老兵班长,一眼就能看出谁在偷懒。班长手里拿着一个三角形的木架子,专门用来对付偷懒的人。班长讲解着动作要领,绕到背后,用手里的三角形木架,对着小腿轻轻一推,偷懒的人一下子就会膝盖着地。训练男兵的班长比较喜欢用这一招整治偷懒的男兵,训练女兵的班长要温和得多,不会滥用手里的三角木架。
训练我们班的那个班长是安徽人,长得白白净净,说话轻言细语,看见我们偷懒了,就说,解散,休息休息。休息一两分钟,我们的精神足了,也不好意思再偷懒了。拔完军姿,接着学向左向右看齐,向左向右向后转,然后学原地踏步,齐步跑步,最后是拔正步。这些动作,齐步最难。教我们走正步的时候,安徽班长已经跟我们混熟了。有一天,在柳树下休息的时候,他拿出几张照片给我们看。黑白照片,分别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六七岁、八九岁、十二三岁的样子,最后一张,差不多是十八九岁大姑娘的样子了。安徽班长让我们猜那个女孩是谁,我们想都没想,就说是他妹妹。因为照片上的女孩,跟他有同样小巧的鼻子、厚厚的嘴唇,还有细长的丹凤眼。他摇头。我们大胆了一点,说是他青梅竹马的女朋友。他依然摇头。那我们就猜不出来了。一个正常的人,肯定不会在皮夹里珍藏一个不相干的女孩照片。他突然红着脸告诉我们,那个人是他。我们的惊呼,被安徽班长用强有力的手势制止住,变成了一咏三叹的疑问。安徽班长告诉我们,他的上面是三个男孩,家里从小把他当女孩养,高中快毕业了,才剃了头发穿男孩的衣服。我们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叹息之余关心起一个最要紧的问题,他打扮成女孩去上学,上男厕所还是女厕所?他说当然上男厕所啊,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他是男生。集合号响起,我们心里的各种问号只好拉直切断变为省略号。第二天,我们满腔热望要把省略号重新变成问号,可惜安徽籍班长不再搭理我们,他突然变得严肃了,除了下口令,不再跟我们聊天。尽管如此,这个长着一副女孩面孔的安徽籍班长,依然是所有班长里面最温和的。
新兵训练结束后,所有训练我们的老兵班长,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令新兵们闻风丧胆的夜间紧急集合,我其实也是喜欢的。夜间的紧急集合,从来不会提前通知,而是突然在某一个深夜,响起急促的哨声,把我们从黑沉沉的睡眠深渊里唤起。五分钟,穿衣服打背包,跑到操场集合报数。集合完毕,黑夜里围着操场跑五圈。匆忙中没有把背包打好的人,背包在黑暗中散落一地,班长的强光手电照过来,照出一张哭丧绝望的脸。紧急集合是新兵的灾难和悬疑大片,充满不确定性。训练过半之后,每晚睡觉之前,我们都会根据老兵传授的经验,猜测会不会有紧急集合。在那些感觉会有紧急集合的夜晚,我们在教导员查房的时候按照要求睡下,熄灯号响
过,我们再爬起来摸黑穿好衣服,打好背包,靠在背包上和衣而卧。听到号声一跃而起,背起背包就要出门去争第一名,抬头却发现天已经亮了,刚才吹的是起床号。折腾了几次,都平安无事,等到我们不折腾了,放心坠入深睡眠的酣甜之乡,紧急集合号却像噩梦般吹起来。慌乱中,一切都是错的,背包打得乱七八糟根本背不上,衣服扣子扣得上下错位,袜子顾不上穿,光脚穿了鞋抱着背包狂奔去集合。没等开跑,背包已经洒落一地。班长的强光手电照过来,狼狈地低头把地上的被子水壶鞋子卷到一起,哄笑声中,强忍着才没有哭出来。班长下达了跑步口令,咬牙抱着背包跟着队伍跑,终于知道自己距离一个合格女兵还有十万八千里。跑完回去,检查背包,东西都在。暗暗松了一口气,令我们闻风丧胆的紧急集合,总算经历过了。
终于到了武器训练阶段,这才是我最期盼的。一人发了一支步枪,练瞄准。这是真的枪啊,枪管冷幽幽的,枪托的楠木质地坚硬,木纹典雅。拿到枪的瞬间,立马模仿着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潇洒地把枪端起来,指着旁边的人,不许动。三个字才说完两个,班长已经飞奔过来,把枪口举向了天空。班长的呵斥冰雹一样滚到脸上,再说一遍,任何时候,枪口不准对人!然后就趴在草丛里练卧姿装子弹和瞄准,标尺上的缺口和准星和标靶的十环,三点成一线,击发。瞄准练多了,备感无趣。在枪的掩护下,半睁着眼睛看那只惊慌失措的蝴蝶。
实弹射击那天,早早去了射击场。发子弹之前,教导员强调了无数次,一定要注意安全。十个人一组,十把枪已经放置在射击位上,一个人十发子弹,五发练习,五发算考试成绩。依然卧姿装子弹,这次是真装。子弹的黄铜弹壳冷冰冰的,把子弹推进弹夹,双手突然颤抖了一下。我掌握着一把可以致人死命的武器啊!这个可怕的瞬间,多少潜伏的恶魔会被唤醒?我赶紧吐出一口浑浊的气体,闭上一只眼睛,标尺的缺口、准星,远处的十环靶靶心,瞄准,击发。装子弹,瞄准,击发。打第一发子弹的时候,肩膀被后坐力狠狠地撞了一下……五发子弹很快打完了。考试的五发子弹,我打得更快,取得了四十六环的优秀成绩。
打过实弹,新兵训练就结束了。
也有一些讨厌的事情。第一件是剪头发,每个人都要剪,必须剪,哭哭啼啼,哭爹喊娘,各种苦情戏,根本没用。教导员说,哭什么哭,这是纪律。女兵不准留长发。可是,为什么呢?教导员从鼻子里哼出一股冷气,纪律懂吗?纪律就是必须执行,没有为什么。纪律的铁面孔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当兵的日子越久,我们就越明白,纪律有多么无情。纪律就是那炉锻铁的火,为的是把形状各异的铁锻打成需要的样子。进了军营便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锻打,经历淬火,才能成为合格的兵。
第二件讨厌的事情,是叠被子。被子必须叠成棱角分明的正方形。检查内务卫生,被子是最重要的检查内容。为了把蓬松的棉花被子叠成有棱角的正方形,我们虚心请教了老兵。老兵的经验是,必须把被子压薄,抽屉,砖头,没事就拿来压在被子上,被子压薄了,棉花压死了,就好叠了。还有,叠的时候喷点水。我大着胆子问了一声,为什么非要把被子叠成正方形呢?好好的棉花压死了,睡起来不保暖也不舒服啊。老兵像看外星人那样看着我,鼻孔哼出一股冷气,说,有本事你不叠。我当然不敢不叠,通过剪头发一事,我已经知道了纪律的厉害。可我内心是抗拒的,除了管卫生的副班长恨铁不成钢,非要帮我用砖头压被子,我自己从来没有认真把被子里的棉花往死里压过。我的被子,一直是被人嘲笑的面包卷,每一次都给班里的内务卫生拉分。
从纪律和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可能直到离开部队,都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女兵。
离开部队之后,不管喜欢还是讨厌,这些往事,我一直珍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