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物三题》马砚田散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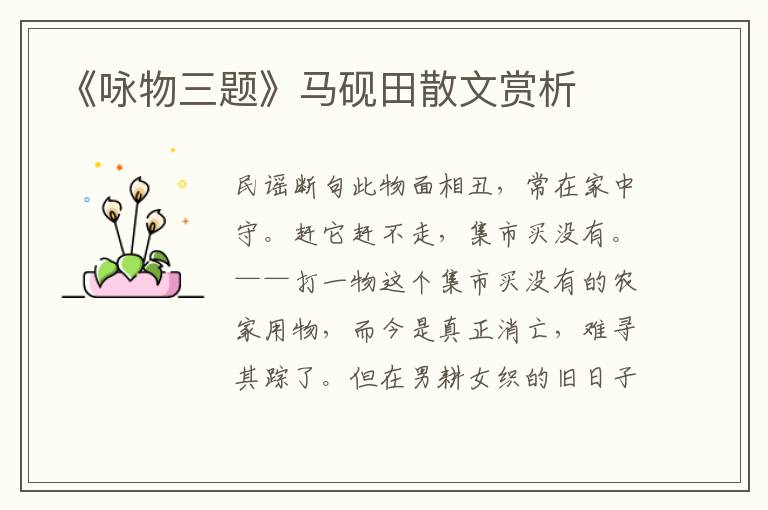
民谣断句
此物面相丑,常在家中守。
赶它赶不走,集市买没有。
——打一物
这个集市买没有的农家用物,而今是真正消亡,难寻其踪了。但在男耕女织的旧日子里,是村村普及,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就在农家里藏身暗处,要不咋叫常在家中守呢。那个时候,没有电饭锅,连热得快也没有。所以,没有这个物件的人家,就不被人认可为人家。又因为它是农家自制、自用的一件不是家具的家具,所以至死也不曾有过学名,一辈子的土名就叫掏灰耙。它的清白和不可类比处,是从没有趟过市场这场浑水,所以从未出卖过自己。一根竖竖直直的木棍,头上顶一块方方正正的小木块,就是此君的肖像。
掏灰耙,它的家史很有来头。它与先人发明的钻木取火,有直接的递进关系。先人把火钻出来后,就知道煮熟食了,不再茹毛了饮血了,人就开始吃人的食物了。炊烟就日复一日升起来。薪火升起前,掏灰耙是主打,它就一耙一耙把灰烬掏尽。所以,它没有空闲梳洗打扮自己,为了别人吃一口热饭,它每天都朝自己脸上抹黑。又因为灰烬里偶有余火,它还时时受着皮肉之苦。时间久了,就被烧灼得体无完肤。还因为它得到了农人的家传,具备了农人的好品行,即使被烧得坏了筋骨,它也从不吭一声,用无言来包容并不完美的生活。
掏灰耙不曾有过童年,它只是当过童工,这个童工,曾和我的童年相伴。那样的日子里,倦鸟归林,垂挂南山的夕阳来照。陶渊明和更多爱诗但不会写诗的陶渊明们,刚刚用完掏灰耙,就烧起了东篱下那一束菊香,水中清味,煮起了山胆海魂。然后就是那一弯瘦月,映照着男耕女织的劳动身姿。对了,自然就有爱情。在女方眼里,热爱劳动,善待日月,这样的婆家里,比拥有财富、生活更敞亮、更充实。这个时候,你如果羽扇纶巾地走来说乡愁,农人会责备你多嘴。躲在暗处的掏灰耙,也会黑着脸,给你颜色看看。用劳动换回的心安和快乐,是掏灰耙年代最重要的社会特征。
后来,电来了。电就接管了旧火的所有权力。赶也赶不走的掏灰耙们,只能跟着老去的岁月,集体兵解。电真是万能,电门一插,饭菜皆熟。空调一开,又换了一个季节。眼一眨,又“闪婚”了。这快捷且殷实的日子,令人昏昏欲睡,不思进取。连个体之间的情感交流,都疏淡了。人与人之间最强大的第三者,是被电激活的利益,这个利益就轻易从人们心里舒走亲情和暖意。至于食物的味道,是火烧还是电煲,有着生活品味的农人说,电是快,火是香。用火烧出来的自然土香,只能留在记忆里了。无言作为离去的留言。从此,没有货币也能活下去的历史,随着掏灰耙的黯然谢幕而烟消云散。
今天,当我们越来越深入科学的腹地时候,曾经为农家生活助力的石碾、纺车、水井、犁铧们,这些当年故乡的骨髓,被人抽干了。同期被放逐的一些小不点,也曾经是故乡手脚的,如掏灰耙、驴掌钉、铁顶针,亦散了伙,临走,通讯地址也没留下一个。只遗下几间旧屋舍,故乡,只剩下一个骨架了。故乡,别的东西丢了就丢了,在我们手里丢掉的东西难于数计。那一句民谣呢?那一句男耕女织的劳动号子声呢?
也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浮躁不安、见异思迁的年代,对一些旧人旧物的舍弃,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有时候在废水池旁,你会看见一些尚能穿用的衣物、家具甚或散币。这些实物稍稍摆放齐整些,几乎就是一个地摊了。但被人眼也不眨一下,就当垃圾扔掉了。丢了就丢了。我就等来捡拾的人。但是我又一次失望。在这一点上,人们像打了商量似的一致,有人丢弃,无人捡拾。一个路人跟我说:现在是随手抓钱的年月,你偏偏蹲在此处,像一根只知守不知动的掏灰耙。诚实倒是诚实,问题是,现在没人喜欢诚实。快了,你也快变成掏灰耙了。听到这里,我就想起多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季,一位赤脚踩踏冰雪的少年。他当时想说出口的最大心事,就是眼下被人扔掉的那一双鞋子。双脚就无端摇动起来,摇得一颗心疼。
掏灰耙,在领导“新潮流”的“高端”商品面前,你就认命吧。我建议你和下堂的糟妻结个伴,远走他乡罢。而面对你们的离去,我没有足够的勇气说一声祝福。但是,掏灰耙,请留步,劳你最后为我清除一次灵魂上的灰烬。
面塑
提及面粉,对民以食为天的民来说,不少人脑子里很快会出现两个以上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食物。第二个概念,还是食物。
当面粉还不是面粉的时候,那个时候,它还是大田里的一株寻常植物。准确地说,是一株人们耳熟能详的农作物,人们叫它小麦。小麦是面粉的前身,也可以说是先驱者。
当面粉躺在了面板上,蜕变成了一团面团,它就由人随意来切割,变成了形态各异的食品:包子、饺子、烧麦、馒头、花卷、面条、葱花饼……
忽然有一天,面粉长出脚来,自己从食材的范围内出走,走进了艺术的苗圃,而成为一种工艺品的原料,生发出动物的四肢和形态来,着色后游乐生命的肌肤和迹象,并且成为能够存留百年生命空间的艺术珍品,就让人啧啧称奇了。这些走进人们日子里的花鸟鱼虫,同时走进了袖珍版的唐宋山水,身边就吹来魏晋之风。这种工艺品,从艺术形式上来分类,叫面塑。它是滦河右岸麦田里的一株文化的穗子,将被移栽进乐亭文化这座百花园里。
面塑,自古有之。旧时,在五行八作中的社会底层,有它的容身位置。只因其收入低微,又很难学成,所以,学者寥寥,学成者甚少。至今日,此业承继者近绝迹。有个叫王建国者却是涉身犯难的一个个例。
王建国,原籍乐亭县古河乡刘庄子村。生在书香世家。幼随父亲温习书法、读诗书,闲时就习工笔花鸟。扎下了艺术的灵柩。后师承艺术大家、在国内外颇负盛名、人称面塑蝈蝈王的王亮先生。积习有年,建国先生对面塑艺术的心得,亦有深意:一是心成,二是手感。心成后而手感成。谓之手发由心。其心,是献身面塑艺术的决心。心成,才能由旧成新,由无成有,由死成活。佛家以成象征智慧,成在心中。面粉离案,成形聚神,建国分与众人,未曾独享。
王建国的心成,还有实例在。在拜师仪式上,作为收山弟子,他都把头磕破了,浸发血丝。王亮老先生面容上的默许,直译的意思是:孺子可教也。灵猴有血泪,西天取真经。面里四百味,面里问人生。十年经济上的零收入,十年甘苦道谁知?这不是面壁十年,而是十年壁面。文化是有味道的,汗酸味。从王建国身上,我读出了乐亭文化的味道。而今,他的面塑作品,已成气候。备受界内人士推崇。推向市场后,日渐占有上额。不日走出国门,也不再是虚言。
天凉好个秋。在王建国手里,有一棵长在秋天里的白菜。白白嫩嫩。难怪飞累了的蟋蟀,选中了它作歇息的场所。另一只落单的雄性,心里就想着好事,就想让白菜作新房,成就合卺的仪式。长在头顶上,两根长长的须枪,差一点就抖起来。农人都是节俭之人。何况清苦久了的王建国,离手的,就只一棵白菜,还有两只相守相望的蟋蟀。让人多看几眼,觉得都是奢侈。让人觉得,没有面塑者的参与,面板上边边角角的面料,简直是一种浪费。一虫一世界,一草一菩提。至于一只草虫,是否隐藏着禅机,我不想说。不想说,或许正是王建国先生的面壁精神。他在面塑着这个世界,也在雕塑着自己。
在泥土上独坐
如果只有几口猪的年岁,并且也就是那么一点点的经历,你就没有能力猜透无岁的土地。不经历老霜旧雪,又怎么能跟得上泥土的感悟呢?
在泥土上独坐,静下心思,使我联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称得上永久的东西,少极。就说人吧,就有晚上脱鞋上床、早晨不再穿鞋下床的先例。自然,这张床还是有人照样去睡,那条路呢,也有人继续走下去。
在泥土上独坐,久了,你就和植物结下了缘分。冬来,冻土寸进,更多的植物,不是到了必经期,就是一株一株对春天的变节。它们不再效忠春季。在冬季,欲寻觅植物的完美,只能说是对生活的一种无礼。而在植物界,一生只期许春天的,水草能算得上其中的一个个例。一袭穿在身的绿衣,直到临冬,还不想脱下换季。
比对将要冬眠的生命形态,是一洼断水;断水边,是一株已经长了冻疮的水草;水草上,爬著一只仍显生命迹象的瓢虫;盯着瓢虫的,是一只欲飞不能的蜻蜓;把蜻蜓视为猎物的,是一只小得不能再小的青蛙;青蛙身后,是它的天敌,一尾纤细的蛇。它们,还残存着捕杀的欲望和意识,但已经丧失捕杀的基本能力,只好摆出一条生存的轨迹。
泥土呵!既抚养生命,又掩埋生命,既带来原爱,又产生原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