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四《我的孟良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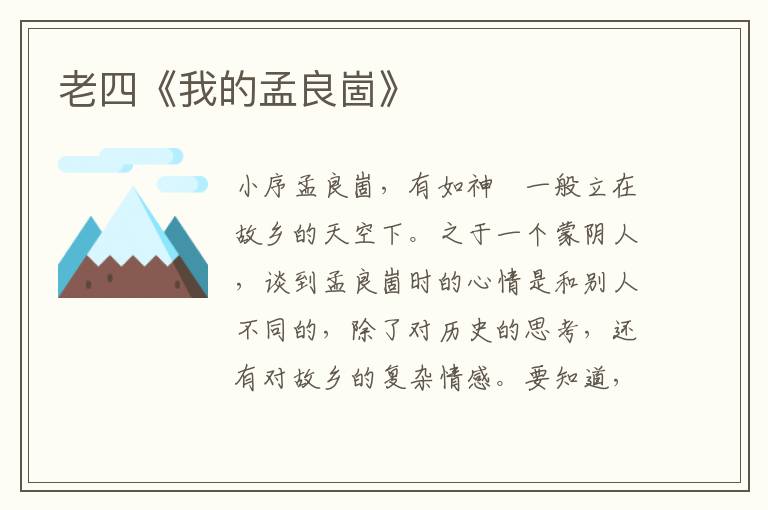
小序
孟良崮,有如神祇一般立在故乡的天空下。
之于一个蒙阴人,谈到孟良崮时的心情是和别人不同的,除了对历史的思考,还有对故乡的复杂情感。要知道,“蒙阴”两个字上一次出现在人教版高中历史课本里,还是东汉时的刘洪和他发明的珠算,跨越1700余年的历史烟尘和好几册历史书,因为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蒙阴终于再次进入高中生们的历史课堂。
老人们会以自己的视角,为那场战役增添诸多正史不载的细节,比如陈毅、粟裕坐镇指挥的老君洞,洞里的千年传说;行军途中,很多战士赤着脚,山上的石头把他们的脚磨得淌血流脓;作为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排着队,每人怀抱一个搪瓷碗,穿过村前的小道。讲到此,老人问我:“你知道搪瓷碗是干什么用的吗?”我说:“当然是吃饭用的。”老人道:“要是没有碗,就没有饭吃。”
17岁,我将第一次“出走”放在了孟良崮,从县城乘车前去爬山,梳理书上的历史与现实,观察之间的距离。20岁,读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垛庄做了一篇《孟良崮周边沂蒙老区农民收入调查》的社会实践报告。工作后,我又一次次前往孟良崮,山崮的形状没有变化,而我正在从青春中走出,在人生的天空下不断出走与还乡。
有一年,我乘火车去临沂。这是一辆从齐齐哈尔开来的漫长的绿皮车,车厢里夹杂了各种北方口音,以东北话居多。一个老头怀抱一块巨大的原木案板,向周围人讲述他当年如何逃难去东北,唾沫飞溅在周围人的脸上。有人问他老家是哪个县的,他没有说具体的县,脱口而出:“孟良崮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以孟良崮代称故乡,想必在老人的意识中,“孟良崮”三个字要比它所在的县更让人难忘。老人解释,在东北,哪儿有人知道蒙阴?但一提孟良崮,几乎无人不知。
一块东北的原木案板,将会成为故乡亲人每日的饮食必备;孟良崮幻化成了故乡,融进老人的血液。然而,之于我,孟良崮还有三层别的意思,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它被时间重塑,同样成为故乡的代名词——身体的故乡,以及心灵的故乡。
青春出走:叔侄俩与家族涅槃
孟良崮烈士陵园内,不时有肃穆的人群穿行,那是朝拜者的脚步,让坟场化作了庄严的礼堂。广场上,粟裕将军的雕塑以挺拔的姿势,守护着这片他曾战斗过的土地,一群大学生排着队前行,在将军面前伫立;广场右边,柏树丛中,一座座休憩的墓碑,那是守护将军的士兵,在喧嚣和静谧之间,历史和现实之间,没有声响,风吹过原野。
一眼望不到边的无名烈士,站成肃穆的兵马俑。他们有父母,有妻儿,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失去了名字,为了信仰,名字幻化成脚下的土地,默默无闻却又坚韧挺拔。
一对叔侄的坟墓,在树林的间隙站立——他们并非这场战役的牺牲者,却因一种特殊的荣耀,成为了这里的主人。
多年前,我11岁时,学习本县的乡土教材《可爱的蒙阴》,记住了两个名字:刘晓浦和刘一梦,从此再难忘记。烈士陵园近旁的垛庄镇,正是叔侄俩的祖居之地——燕翼堂。
“燕翼堂”三字,据说由乾隆皇帝题写,这是20世纪初垛庄乃至蒙阴最兴盛的家族,拥有5800余亩土地,上千亩山林,地跨蒙阴、沂水、沂南三个县。还有酱园、酒店、油坊、布庄、百货等店铺,雇佣工勤80余人,养看家兵15人,长短枪20余支,办小学1处,并在济南、青岛、上海等地开设有商号。
燕翼堂占地两万平方米,房屋160余间,八卦式建筑,院中套院,既严密又牢固,像一座城堡。主人刘氏,不仅财富显赫,更以开明著称,其家庭成员受共产党的影响,大部分参加革命,特别是刘晓浦、刘一梦叔侄二人。
简述刘晓浦、刘一梦的生平如下:
刘晓浦,名刘昱厚,字晓浦,1903年出生,兄弟四人排行老四,人称“四少爷”,自幼在本村读书,后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济南育英中学。1920年,考入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山东民国时最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苗海南是他的学弟。因组织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刘晓浦被开除学籍。之后,他在济南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王尽美的介绍下加入中國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加入共产党。
刘一梦,名刘增溶,字一梦,号大觉,1905年出生,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五,人称“五少爷”。刘一梦几乎沿着叔叔刘晓浦的路径发展,1923年,两人一道就读于上海大学。
刘一梦还是一位青年作家,加入了上海共产党人组织的太阳社,出版短篇小说集《失业以后》。1928年,日军占领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刘一梦联合其他作家公开发表了《中国著作家文艺家自由联合对济南惨案的三个宣言》。
上世纪30年代初,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中称:“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此时,刘一梦正在狱中。
1928年至1929年,刘一梦、刘晓浦先后回到山东开展工作。刘晓浦任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刘一梦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刘一梦以“大觉”为名,在团省委创办的《晓风》周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
1929年4月和7月,刘一梦和刘晓浦先后被捕。
10月,刘晓浦二哥刘云浦变卖家产,携巨款到济南设法营救。刘晓浦对二哥说:“不要花钱了,只有自首才能出去,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1931年4月5日,刘晓浦叔侄,以及时任省委书记刘谦初等22人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刘晓浦年仅28岁,刘一梦年仅26岁。
刘云浦再次来到济南,面对的已是亲人们冰冷的遗体。接下来,他用马车将遗骸拉回燕翼堂。从济南到蒙阴的漫漫长路,望着两位亲人的遗体,马车上的刘云浦是什么心情?他很难具体理解两位亲人所钟爱的事业,以及他们的信仰,但是,一种出于亲情的信任,以及耳濡目染的信仰的力量,让他始终坚信,两位至亲的付出,值得他将悲痛化作一种坚守。
回家后,他将二人棺材浮柩在一个叫“桑子行”的地方,上面仅覆盖了一层薄土层,堆成了两个没有墓穴的坟,他要将出殡下葬的日期放在遥远的未来。
时光如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和八路军四支队进入沂蒙山区领导抗战。刘云浦和他的燕翼堂担负起了八路军驻垛庄一带部队、工作人员等的后勤供应,肖华将军曾带领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全部驻在燕翼堂。1938年5月,八路军四支队经理部主任马馥塘、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先后代表部队和省委慰问了烈士家属。当地还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至此,刘晓浦叔侄的遗体得以安葬。
在刘云浦的带领下,整个燕翼堂竭尽全力抗战,先后有26人参加革命,有6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其中刘晓浦之女刘增蔼,为中共山东分局机要员,1941年冬牺牲于大青山战役,年仅18岁。
燕翼堂还一次捐献长短枪40余支,成立了垛庄独立营;卖地300亩,购枪一百余支,支援八路军。在刘氏家庭的带动下,燕翼堂长工和佣人,大多数参加革命,有的后来成为我党高级干部。后来,抗战最艰难的时期,燕翼堂曾多次被日军占领,我军多次攻打,付出较大代价。为了抗日,刘云浦毅然拆除了这所著名的庭院。今天,垛庄镇党委政府驻地,便是当年燕翼堂的旧址。
1994年,劉晓浦的遗骸被迁到孟良崮烈士陵园安葬,和他一起安葬的还有他在革命年代牺牲的部分亲人:女儿刘增霭、侄子刘一梦,还有刘滋泉(牺牲时年仅24岁)。
《诗经》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从孟良崮脚下走出,走向外面的世界。后来,他们回来了,一同回来的,是他们肩负的使命,以火种的形式在这片土地播撒。有时候,他们站着回来;有时候,他们躺着回来,那是他们的身体累了,回到故乡的怀抱,回到母亲的家园。但是,他们的精神没有休息,年轻的血液依旧在这片山区流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片土地有无数年轻人奋勇而起,男人拿起武器,女人支前拥军。
山河破碎,总有无穷的力量重整山河。
血色浪漫:战争中的女人
一场战役构成了孟良崮的核心价值,单纯从战略战术而言,1947年的那次歼灭战堪称经典,甚至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无出其右者。十几万人的迂回包抄,32000人被全歼,敌军主将张灵甫战死或被击毙,游刃有余,干净利索。
十几万军人,背后是数量不在其下的后勤保障队伍。
战斗打响的时候,孟良崮以北30公里,野店镇烟庄村,6个平凡的姐妹因无意识的举动而进入历史。
男人们要么当兵上了前线,要么作为支前民工上了前线,村里只剩了老弱病残,像极了今日的乡村。6位20岁左右的姑娘——张玉梅、尹廷珍、杨桂英、尹淑英、冀贞兰、公方莲,她们出身苦寒,有的是童养媳,有的是逃荒户的女儿。此时,她们成了村里的顶梁柱。
战斗打响了,六姐妹组织村民,为部队当向导、送弹药、送粮草、烙煎饼、洗军衣、做军鞋、护理伤病员。半个月的时间里,起五更睡半夜,有时候通宵不休息,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把5000多斤粮食运回村里加工成煎饼,又送回去,往返40多里路。她们还组织村民纳军鞋500多双,给部队洗了800多身衣服,为战士唱歌,鼓舞士气。
为了做军鞋,六姐妹彻夜不眠,胳膊和大腿都磨起了泡、出了血,手指也变了形。尹淑英后来回忆:“一只鞋底要纳120行,一行要过30多针,每针都要经过锥眼、穿线、走线、拉紧。当时不分白天黑夜地做军鞋,做鞋搓麻绳要用腿帮忙,时间长了把腿都磨破了,手也不行了,实在累了就躺在地上打个盹。”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六姐妹还承担起了运送草料和弹药的任务。她们翻过一道道山梁,走进一个个村庄,凑足了2500斤草料,动员妇女组织运输队,把草料送到了预定地点。至于弹药,一箱七八十公斤,两人抬,翻越10多公里山路,一直送到前沿阵地。尹淑英当时身怀有孕,行动艰难。后来,“跑到北边生了个孩子,3天就起来干活了。”
据说,“沂蒙六姐妹”这一称谓,是陈毅元帅亲自命名的。冀贞兰生前曾回忆第一次见到陈毅的情景:“骑一匹马过来,打着绑腿,不知道他是谁,很和蔼的一个人。”
一天,六姐妹接到通知去指挥部。冀贞兰再次见到上次骑马的那个人。他询问姐妹们这些日子摊了多少煎饼、做了多少鞋子、有什么困难,笑着说:“给你们起个名字吧,叫大嫂呢,你们还有没结婚的呢;叫大姐吧,还有结了婚的,干脆就叫‘沂蒙六姐妹’吧。”
多年后,在孟良崮纪念馆看到陈毅的照片,冀贞兰觉得面熟,旁边的人告诉她那就是陈毅。
1947年6月10日,鲁中军区机关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道了这个模范群体。从此,“沂蒙六姐妹”的名字传遍了整个沂蒙山区。2009年,以她们为原型的电影《沂蒙六姐妹》在全国公映。
陈毅说过一句至今听来仍让人震撼的话——“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六姐妹成为一张张名片,继续在山区飘扬,六姐妹红军小学、六姐妹纪念馆、六姐妹饭庄、六姐妹采摘园。沂蒙山区最流行的一种食物是煎饼,煎饼的品牌众多,六姐妹煎饼无疑是最有名的一个。一位记者曾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在烟庄村采访时,不仅看到这些带有名称的建筑,还偶遇了好几位‘沂蒙六姐妹’后人:尹廷珍的儿子徐美福正在村里操持饭庄生意,公方莲的儿媳妇正在果园摘苹果。‘人逝去,精神不会灭’,村人和子女们正以不同的方式在纪念、传承着‘六姐妹’留下的精神财富。”
许多年里,“沂蒙六姐妹”一次次出现在县电视台的新闻中,伴随我度过童年、少年,直到离家远行。那几位慈祥的老奶奶,受到全县人的尊敬,不光是因为“战争中的女人”这一血与火的时代命题,她们在和平年代的特殊身份,诠释了革命老区在经济社会中的存在,为这个县现实的经济发展做出旁人无法比拟的贡献。
前些天我又在电视上看到了她们——不,是她,当年的六个姐妹,逐渐去世,后来只剩尹淑英一人健在,不免心有戚戚焉,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然而,就在此文完成之后不久,2016年6月21日,尹淑英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1岁。但六位奶奶依然活着,以她们朴素的精神,诠释着这片山区的文化内涵。
战争波及女人,是时代的悲剧,然而她们又是血色与浪漫的结合,扩大了战争的外延。美国作家斯坦培克在《愤怒的葡萄》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情景:一位少妇在草棚里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流浪汉,她解开上衣,让流浪汉吮吸她的乳汁,流浪汉热泪滚滚,他感到自己进入了天堂,圣母就在自己身旁。这本书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在《愤怒的葡萄》热还没降温时,远离美国的沂蒙山区,却发生了真实版的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红嫂明德英。
明德英所在的马牧池常山庄,位于孟良崮以北20公里的沂南县。她是红嫂这一群体的最核心人物,六姐妹同样是红嫂,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期间,沂蒙山区出现的红嫂群体,从根本上解释了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人民的支持。
孟良崮上空的硝烟早已散去,那些柔弱的女人的身躯曾走过的沟沟坎坎,依然有新的身躯走过。她们的后代依然在这片山区,繁衍不息;她们的灵魂依然飘荡在我们的家园,以生活的名义,平凡而又伟大。
精神反哺:重塑乡村尊严
2016年春天,我又一次来到孟良崮山下。这一次,我的身份是记者。
省发改委派驻蒙阴的7名第一书记,有两人在垛庄,5人在旧寨。7个人平时分散在各自挂职的7个村里,遇有大事,便聚集到一起,共同解决。他们的故事,丰富了我对孟良崮的认识。
“沦陷的故乡”成为近几年的网络热词,当乡村变得越来越凋敝,生气全无,只剩老人孩子,故乡还有什么?逃离故乡的人群,放眼望回自己的宿命之地,却发现,另一群人正从喧嚣的城市来到这里,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些被冠以“第一书记”之名的人,成为乡村的一抹亮色。
“到农村去,那里有生我养我的爹娘;到农村去,那里有育我成长的南瓜米汤;到农村去,那里是魂牵梦绕的故乡。”——“第一书记”成为目前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亮点。
伴随乡村经济的发展,以新的“乡村建设运动”为契机,文化伦理、社会秩序的重建将会给乡村带来新的变革。第一书记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现代文明和传统村落之间的桥梁,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为村庄寻回失落的尊严。
孟良崮西南方向,有一个南芙蓉村,是当地鲜见的回民村。一天早晨,我跟随第一书记王海东乘车出了垛庄镇政府驻地,来到南芙蓉村,正好赶上当地的大集。河边公路旁的一片空地,卖各种杂货的小贩和赶集的人群,构成了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
王海东在此挂职已有一年多,不时有村民跟他打招呼,邀请他到自己的摊前吃饭。他摆摆手,和摊贩交谈几句,笑着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村中央,紧邻村委会,有一座始建于明初的清真寺,是村民做礼拜的场所,也是本县著名的古迹。寺内,古木参天,山东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王树理题写的碑文立于高大的皂角树荫里。抗战时期,这里曾藏过八路军伤员,大殿被赶来搜寻的日军烧毁,后重修。
看到作为记者的我,一群村民围上来,述说王海东的“贡献”。“硬化了村里的路,包括上山的生产路,打了井,有了水,王书记为我们村出了大力,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张大娘开了一家小卖部,王海东帮她的儿媳妇在水厂找了工作,月收入2000元。一位大娘称赞道:“他的脾气真好,上到八九十岁的老人,下到三岁小孩他都会停下来说话拉呱。”
出了村,我们来到村东的一片杨树林,许多杨树被伐去,一排蘑菇大棚建了起来。56岁的米天明从大棚里提出一筐刚采的蘑菇,王海东过去拿起他的蘑菇查看,叮嘱他们抽空去镇上办理银行卡,进行淘宝认证,以便将蘑菇在网上售卖。
刚开始,村民对种植香菇有抵触。去年,王海东带他们外出参观,最远去了河南西峡县。米天明夫妇也去了,很受震撼。接下来,引进蘑菇种植的阻力减小,村里建设了一批香菇大棚。米天明承包了其中的三個,每天采一次,到现在已采了8000斤蘑菇。
米天明的女儿,去年以全镇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蒙阴一中。王海东每个学期资助她500元,“这个孩子很刻苦,冬天那么冷,在家里围着炉子写作业。”
南芙蓉村只是无数案例中的一个,几天的采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农民的无奈,以及第一书记带来的变化:满山的桃子因没有路无法下山,化肥上不了山,因为浇地困难,很多桃树结果甚少。五部抽水机从遥远的水库一步一步往山上倒水的情景让人震惊,累死累活浇一次地,累倒不在乎,能浇上水就谢天谢地了。
于是,一场修路引水运动在我所考察的几个村庄以及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只用一年时间,路通向了山顶,水直达地边,荒山变果园。当地顺口溜说:“水上山,果下山;路上山,桃下山。”形象地表达了村民的心情。
第一书记带来的,不只是生产生活的便捷,也不只是越来越多的致富道路,还有老有所依和文化生活的秩序重建,比如幸福院和文化广场。农村养老问题长期被忽略,却又是亟需解决的大问题,况且农村贫困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存在于这个群体,只有让“老弱病残”脱贫,才能最终实现全面脱贫。村里建起的幸福院,为老人提供了生活和聚会的场所,受到老人的普遍欢迎。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文化广场的出现恰逢其时。平时的健身操和广场舞,节庆时的娱乐活动,每个村的广场成为显而易见的文化中心。文化广场的出现,改变了村民的生活习惯,也给文化下乡提供了舞台。一位村民告诉我:“到广场跳舞成了晚上新的习惯,种地之外,终于有了‘文化’。”
当然,第一书记并不能彻底改变农村的现状,输血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造血。外出归来的年轻人,看到村子的变化,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农村基础设施和通讯的便捷,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回乡创业浪潮能否为当下的乡村注入新的活力?如今的孟良崮,会以怎样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先人们誓死保卫的家园,终究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小结
孟良崮周围,总有那么一些人,承载不同时代的使命,在荒凉而又富有的山野上,书写历史的篇章。
20年代,叔侄俩为了信仰投身革命,将20余岁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民族解放的事业;
40年代,六个姐妹献身人民战争,用农民朴素的方式做出政权的选择;
新世纪,第一书记的出现,为失落的乡村文明注入了活力。
一座山崮,泥土和石头,大地和灵魂;一座山崮,过去和未来,青春和历史;一座山崮,我的山崮。
青春出走、血色浪漫、精神反哺,构成了“我的孟良崮”的精神内涵,构成了我的故乡的无限外延。在这里,我的青春也曾出走,我的姐妹依旧在那片山区繁衍生息,我最终的理想不过是为了反哺故乡;在这里,一百年的历史幻化于我的脑际,成为我与故乡、自我对话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