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仁宇《月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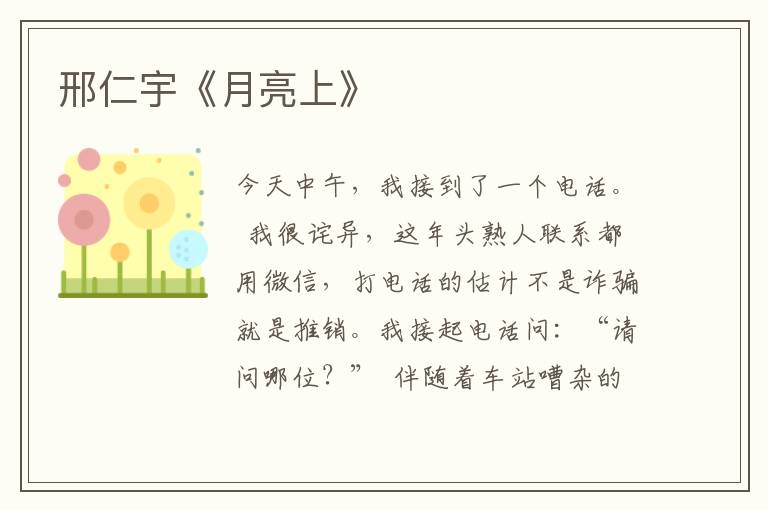
今天中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很诧异,这年头熟人联系都用微信,打电话的估计不是诈骗就是推销。我接起电话问:“请问哪位?”
伴随着车站嘈杂的噪音,电话那头响起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声音:“喂?是小邢吗,是我啊,张大瞎,张浩宇!”
张浩宇,这个名字在我脑海里溜了几圈,才终于在一个满是灰尘的角落找到了对应的人。
“哦!张浩宇!”我声音顿时高了八度,“张大瞎!久违了啊!”他明显听出了我的喜悦,笑呵呵地对我说:“我这边不方便说话,咱们晚上一起吃个饭吧!”说着告诉我一个饭店,便挂断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走到书架前拿下一本破旧发黄的笔记本,里面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碎纸片,笔记本的封皮,工工整整地写着“张浩宇”三个字。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有上百号楼的大型小区里度过的——那是地皮和楼房还没有那么昂贵的时代,这种大型的小区似乎也是一种流行和趋势。也正是因为这个巨大的小区,附近小学里半数的学生都居住在这里。那时很多家长对于学习并没有那么的重视,对孩子的管束也并不严,因此孩子们的交友基本都是靠缘分来的。我和张浩宇便是如此。
要知道,不同地区的小孩有着完全不同的童年,但有一点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欺负”的对象,有些人觉得自己小时并没有这种情况,但他们其实往往是没有自觉的加害者。
我和张浩宇就比较不幸了,我们两个都是被“欺负”的一方。张浩宇是因为他戴着眼镜,那副几乎占据了他半张脸的大眼镜在近视人数较少的小学着实看着奇怪。由于离开了那副眼镜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他便被赐了“张大瞎”的外号。我的原因比张浩宇还要憋屈,因为当时热播的电视剧里有一个叫“老邢”的角色,而他们似乎不太喜欢这个角色,拥有同样姓氏的我就这样遭重了。
张浩宇比我大两岁,我们不是同一个年级,甚至不是同一个学校,但因为常在同一个小区玩,我时常能看到他被人抢了眼镜后像黑瞎子一样摸着路去找他们要回自己的眼镜,他则是经常看到我被人追着往裤子里塞蝗虫。
一天,被人追到精疲力竭的我看到了一扇被人遗弃在墙角的半扇破门,便慌忙钻了进去,没想到那里面已经有人占位了——张浩宇正躲在里面小声抽泣,看样子眼镜并没能夺回来。就这样,孩子圈最底层的两个人成了难兄难弟。
和他交流一阵后,我了解到,他被孤立、欺负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视力不好,他似乎对于动画和玩具毫无兴趣,而且不擅长说话,每次同他闲谈,他都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然后便开始自顾自地说起自己在科教杂志上看到的文章,从恐龙谈到深海,从地核谈到宇宙,他说话过程中我完全插不上一句嘴。
“恐龙的子孙现在依然延续着,”他说道,“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思考了下,打算回答鳄鱼,但他抢先一步自答道:“是鸟!恐龙进化成了鸟类!没想到吧!”
就算是这样,日子也比被追逐时好过得多,我很快适应了他演讲式的交流,甚至渐渐也喜欢上了科教杂志。
“你知道吗?”一个夏日的夜晚,我们两个刚刚逃过追捕的人坐在墙头,叼着冰棍闲聊着,“地球的资源已经要被人类挥霍空了,人类迟早要移民到月亮上去。”
我抬头看着那轮散发着慈柔光芒的满月,那时的月亮无比明亮,在地上投下清晰的影子。在澄净的夜空下,月亮看上去是那么的遥远,比张浩宇嘴里说的事还要遥远。
他继续说:“现在只有美国和苏联登陆过月球,中国还没有踏足过那里,但我相信很快了,我长大后一定要去月球工作!”他的语气无比的自信,仿佛这件事就在明天。我笑着说,在月球上上学就不需要骑车子了吧,飞着就可以了,那我也要去。
随后他又给我讲,月球上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人类可以轻松跳出六米高。那晚我们聊到很晚很晚,直到家长出来揪人才相互道别,依依不舍地回了家。
后来,他先我一步上了初中,学业压力的上升使我们交流少了很多,再后来,我搬家了,我们只能靠电话互相联系。
高中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了他,不知已经多久没有和他联系了,但打过电话去已经变成了空号。我们相互留下的都是座机号码,这相当于彻底切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之后我到以前那个小区去找了他,却发现,他原本的住址已经住进新的住户了。
就这样,直到今天中午,我们时隔十余年才又重新有了交集。
晚上,我比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便到了说好的餐厅,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张浩宇的到来。虽然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也没能留下什么照片,但印象中他是个稍微有点瘦的小个子,当时比小他两岁的我都要矮,我对他的印象居然只剩下了这些。
大概一小时后,一个中等体型的男人走进了餐厅,环顾一圈后,面带笑容地走到了桌前。
“老邢!还记得我不?”
我尽可能地把他和记忆中的张浩宇重合在一起,似乎有点像,又似乎完全不像。
但他似乎完全记得我的长相,立刻坐在了桌子对面,开始熟练地点起了菜。
点完菜后,他开始跟我解释,在我搬家后不久,他为了方便上高中,也搬家去了别的地方,因为家里没有再安装座机,便没有跟我联系。
“你看这巧的,”他操着天津口音说,“等想起和你联系的时候,你也不用座机了,这时代发展真快。”说着打算给我倒酒,我急忙说自己酒精过敏拒绝了。
菜上来了,他边吃边和我叙旧,说起我们被人追着欺负的故事,大多情節添油加醋了不少,发现没话题了,就再把这些旧事讲一遍。
我对他说,你比以前会说话了,他笑着回答,大学加了学生会,不会说话得挨批!
酒过三巡,他似乎已经有点醉了,但仍旧对自己现在的状况闭口不谈,于是我问他,现在是不是在航天部门工作。
他迟疑了一下,笑着回答说,早就没这想法了,都小时候的事儿,小时候谁还没想当过科学家啊。说着他一口干掉了杯子里的酒。
吃到深夜,他似乎还没尽兴,拉着我找了个烧烤摊,准备吃第二顿。他去店里点菜,我坐在外面的马扎上,望着天空的月亮,不知是因为城市灯光太亮还是空气太差,月亮的光无比黯淡,仿佛即将结束生命的日光灯管。
他点好菜后吆喝道:“在外面坐着干啥?喂蚊子哪?快进来吧!”我应了声,走进菜馆给自己也开了一瓶酒。
觥筹交错间,我仿佛看到窗外变成了月球的表面,月面上坐着两个孩子,将手伸向了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