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句话可以收回》葛旭东散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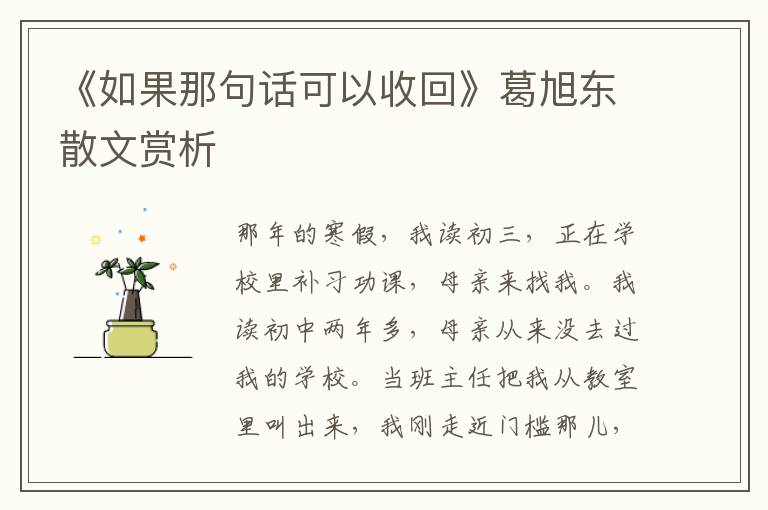
那年的寒假,我读初三,正在学校里补习功课,母亲来找我。我读初中两年多,母亲从来没去过我的学校。当班主任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我刚走近门槛那儿,还没迈腿,透过班主任细高瘦削的身材,我看到了母亲的衣襟,一件月白色的褂子。那褂子,因为洗了多年,已经变成了灰白。母亲怎么穿了这件衣服?她在冬天不都是穿着那件黑底暗红格子的外套吗?母亲怎么来了学校?母亲在娘家照看姥爷好多天了,怎么,难道?我踩在门槛上。班主任说:“你家里有事,收拾一下书,回家吧。”穿月白衣服的母亲从班主任身后闪出来,我腾云驾雾般凌空一迈,右脚踩空了一级台阶,左脚赶紧支撑,还没着地,右脚已经顺着第三级台阶的边沿滑下去,身子斜摔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
那一天,是腊月二十三,姥爷去世了。
以后,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成了大舅、小舅、大姨、小姨和我们家在姥姥那里聚会的日子,我们要去坟头烧纸。
姥爷去世后的第四年,姥爷忌日那天,天气阴冷,我们都穿了加厚的棉袄棉裤,戴了可揣下两只手的棉窝手。那时候,我们那地方的人不戴棉手套,感觉手套不暖和,都是拿家里的布头和棉花缝制一个两边开口的圆筒形的窝手,两只手揣进去,走路时戴上,抄着手,暖暖和和。那天,姥姥也把她的棉窝手拿出来,放在了炕上。我很好奇,姥姥的手从来不拾闲儿,不是做饭,就是缝衣,要不就是擦桌子抹板凳的,什么时候戴窝手?我的嘴就是那样走直线,口随心走,不由地问姥姥:“姥姥,你拿窝手出来干什么?”姥姥正在剥大白菜的老菜帮,打算剁馅,中午包白菜猪肉馅饺子,她边剥菜边说:“一会儿路上戴。”我马上来了精神,跳下炕,凑到姥姥跟前:“姥姥,难道你也要和我们一起去上坟吗?你不是从来没跟着去过吗?看来你真是想姥爷了。”那时候,我十九岁,正是情啊爱啊满脑子满心思萦绕的年龄,加上又看了那么多缠绵悱恻的言情影视剧、浪漫得要死要活的言情小说,还有那些不停地在电视台的点歌台播放的火辣的情歌,我的心思简直如火如荼了。现在,有了现实版的古老的爱情剧,岂能放过?我好像马上有了用武之地,打算调侃一下平时看起来心如止水纹风不动的姥姥。
我偏着脑袋笑眯眯地等下文。
嫩叶子厚菜帮的大白菜竟然顺着姥姥的双手一下子滚落到了地上,地面上有一层细细的炉灰,水润的大白菜立刻变成了个大花脸。姥姥赶紧从矮凳上探起身,双手抱起大白菜,嘴里嘟囔着:“唉,不中用了,连棵菜都拿不稳当了。”转身去外间屋,拿盆洗菜。
那时,恰好母亲、大姨和小姨三人从集市上买完供品回来了,我因为发现了惊天秘密,兴奋难抑,立刻向她们有板有眼地大声宣布:“告诉你们一件特大新闻吧。”大姨最爱和别人抬杠,她不屑地说:“你在屋子里钻着,能有什么特大新闻?要说新闻,还得我讲,我刚从集市上回来。”我从小爱跟大姨较真,于是拉长了声调:“你那些事,没什么轰动效应。我的新闻,是你们听都没听过、想都没想过的事情。”大姨在村戏班里是唱小旦的,声儿特尖细,听我这么一说,立马鸟语婉转地拿腔拿调:“咦——你倒是道来呀——”我顺着大姨的小旦腔:“姥姥也要去上坟——”大姨比我还人来疯,赶紧轻移莲步,飘到外间屋,大喊一声:“娘!你也要去上坟?”我像戏迷追剧情一样,追到了外间屋。姥姥已经把菜洗好,放在案板上,用干布把白菜帮上的水擦干,边擦边说:“你们几个去吧。我在家包饺子,回来你们就能吃上晌午饭了。”
我和大姨都愣在了一边,感觉到了什么。小姨赶紧走过来打圆场,呵斥我俩:“你们两个疯子,整天疯疯癫癫的,怎么着?济公转世啊?去上坟怎么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去,你们俩,炕头儿上暖和着去!”我和大姨灰溜溜地溜到了炕头儿上,谁也不再说一句话。
那天,姥姥没有去上坟。虽然我支着耳朵想听小姨在外间屋细声细语地劝说姥姥,但模模糊糊听不真。
中午的白菜猪肉馅饺子可能油放少了,也可能盐放少了,吃起来淡而无味。
一晃十几年了,姥爷的忌日成了我心头的恐慌。我一句戏言,断了姥姥和姥爷哪怕在坟头儿相会的可能。我狂热地以为我能用新潮的情啊爱啊的观念感染姥姥,以为姥姥的心思会因此如湖水般荡漾、充满活力,哪怕是思念,那也是情感的波动啊。但万万没有想到,面对一个一生都将爱尘封在心底、言语上丝毫不露半点口风的上辈人,我不自量力的莽撞致使历经四年思恋萌发的一株嫩芽猝然夭折了,那嫩芽本来可以长出两片叶子,然后伸长茎秆,枝繁叶茂。那应该是一株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每年的那一天,会花开灿烂。也许,姥姥的心头已经是一片沉积多年的沃土。十八岁嫁给姥爷,四十多年,虽然难免斗嘴斗气,但那些相濡以沫几十年走过来的夫妻生活足以使姥姥在孤寂的日子里一点点翻垦。那里面,有养料,有水源,有阳光,有田间小径,有儿女的哭闹,有一次次听着姥爷披星戴月叩门的声音,有拿到姥爷历经周折从黑市上换回来的几尺花布的窃喜,也有临终的无言。无法放手,又只能撒手。
母亲说:“你姥爷去世的时候,是握着你姥姥的手走的。”母亲还说:“你姥爷没说一句话,就闭上了眼睛,上牙紧紧地咬着下嘴唇。”那一幕,我没在跟前,但在这十多年里,它却像是长了想像的翅膀,不断地在我眼前飞翔:姥姥布满青筋的双手,从姥爷干枯的手里一寸一寸地慢慢挪出来,然后一只手轻轻抚摸姥爷残存的没剩几颗的牙齿,另一只手按在姥爷青灰色的嘴唇上,一次,两次,三次,姥姥不忍太用力,也许是姥爷咬得实在太紧了。别人是帮亡人合上眼睛,姥姥是帮姥爷合上嘴唇。姥爷闭上眼睛,安心地走了,但有一样东西,是要靠咬紧嘴唇才能防止它滑落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