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勇奇《草原断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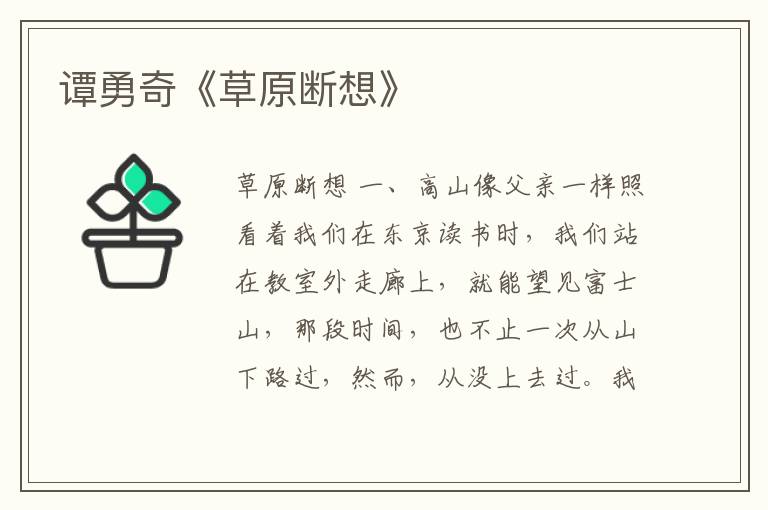
一、高山像父亲一样照看着我们
在东京读书时,我们站在教室外走廊上,就能望见富士山,那段时间,也不止一次从山下路过,然而,从没上去过。我第一次见到它,就觉得自己只想眺望它。后来,去青藏工作,在草原上望远山,雪峰如浪,连绵无穷,我为之仰望,为之低首,也没去攀登过。对于所谓征服、挑战之类字眼,我还不能理解,说到征服,对象总是敌手,心无荆棘,又何谈挑战。从山脊上蹒跚爬过,就说是征服,似略显浅薄。
自然万物充满和平气象,即使雷霆雨雪,也在滋养并成就我们,这一点,二十四节气是很好的诠释。仁者如山,高不可攀又蔼然可亲,大自然离不开这样的长者。所以,在高原上,每一座山都有一个神的名字,它们之间好像一个和睦的家族,共同经营一个清风丽日的天堂。真正的山,它的高度,人是无以可攀。
青藏高原上,山不是突兀而起,它们是大地的一个一个潮峰,缓缓起伏,融入天际。它们绝对的高度,已经不需要任何依傍和参照,以衬托它的高大和威仪。真正的高大,其实就没有高度了,大道至简,什么都不用说了。比它高的只有太阳,有时太阳也会隐入它的衣袖。所谓高大其实是它的包容,仁者如山,崇山怀玉,高度不就是它的深度吗。青藏高原最厚,所以它最高。那些高山像父亲一样照看着这片雪域草原,照看着像哈达一样飘在天空的圣湖,顺带也照看着太阳、月亮、星星、风花雪月,一切生灵,还有我们。父亲的情怀就是这样,他想照看他所爱的一切。
我们的汽车沿着草原的大毯子四处游荡,像小甲虫在作无目的漫游。山看我们正如我们看蚂蚁吧,山欣赏着我们的忙碌,百无聊赖又饶有兴趣。我们却对山不知,不知它的宽广和深厚,长久望着它的神秘,渐渐茫然。
茫然是十分美妙的感觉。有时我想,唐僧取经,吸引他一路西行的,不是那秋毫必见的觉悟,而是那无穷无尽的茫然吧。望着远山,最终我们知道,它只可向往,不可逾越。那些永不可逾越的,就成了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不喜欢听谁谁说征服了哪儿哪儿的神山,好像一种信仰受到了挑战,我为之升起近似屈辱的悲悯,因为,没有比自负地逾越信仰,更让人感到担心的了。
我见过最高的山,天际和白云都在它怀中。初看,见不到山,山在哪儿,在云端露出一点黛青,在星辉里拉起一角窗帷,在旭日后闪一片雪光。我于是知道,真山确在天上。虽然它的根连着地心,却把真面目藏在天后,留给未知。高山仰止,未知之高,确实不容攀登了。
二、站在草原上回首自己
想要把自己放进一个彻底的,又充满生机的静里,去到苍茫的高山草原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人所以要旅行,其目的不是观光,不是猎奇,不是要为外界来刺激自己日益失去弹性的心灵。而是要寻找一种在自然间的位置,在历史苍茫无极之中,给灵魂找一个位置,以便能自己看得见自己,观望到自己。
天地悠悠之际,一切曾经苦思冥想不能得到的感悟,瞬间就呈现在面前,丝毫没有怀疑之感。往日的猜测迷茫豁然开朗,如冲出了愚蠢谎言的雾霾,一下子回到了柳暗花明的童年:心也柔了,呼吸也平畅了,眼里也清亮了。终于,感觉到作为一个人的美好,——这是世间最重要的事情,对人来说,没有比感到自己活着是一件令人陶醉的事更好的了。这个时候,心里涌起无限的爱意,对着远山,对着青天,对着普照的阳光,——在喉间涌起赞美的旋律,不知不觉想唱啊——相信了生命确实是充满了爱的。
爱是生命的本意——“爱”这个字,在这里才真正变得纯粹、干净、高尚。爱和灵魂,和自然结合在一起,和生命连成一体,就如花叶和枝干一样的关系,就像森林和大地、流水与河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只有在大自然充满生机,又包含虚心的宁谧之中,才能感受到。
不能常常回归自然,但是可以努力在心里造一个草原。一个微微隆起在地平线的草原,它有一定的厚度,正好映出苍穹的弧形,昭示着人类智慧只是被局限于一个透明玻璃罩中的发现,——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切人为辉煌,也比不过草原上的一春和一秋。世间来去并不由己。于是,心中的草原渐渐丰满,淌过溪声,拂过云影,夜有星光,昼有花香。原来,那个自己曾经被自己的冷漠迷失了啊,人最大的粗心,不是忘记了自己吗?站在草原上,恢复了自在,如一棵向日葵,一枝忘忧草,一株月见花,细而密的脉弦涌流着善感的律动。尘埃落定,露水含香。胸中升起了浩荡的苍茫,眼里闪动着清澈的伤感,心底柔软充实,步履轻盈稳健。
站在草原上,回首自己,生命的美,生命的好,如草原的阳光一样明白无误。生活是值得珍惜并且可以享用的。一切都可以等它慢慢来去,且走好我的路,做个有我的自己。
三、高原上的那些名字
我第二次到拉萨的时候,站在大昭寺前的广场上看各色各样的人,欣赏他们的音容笑貌,欣赏他们的衣帽服饰。在大昭寺前,人的衣服和谈笑,肢体和眼神,让我顿悟人所以为人。我们作为人这一类生命,在最初的时候,实在是上天的杰作。
卓玛抬头看着我,或者说是望着我,草原上的人们的眼神总是这样遥远,带着动人的迷茫和迷离。我问:“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卓玛!那么你呢,你叫什么?”这使我突然感觉到有点窘迫。我们的名字在这里显得微不足道,说不出口。我的名字是什么。
问一个藏族人的名字,他们或以雄浑的声音,或以清脆的声音,伴之以谦卑的神情,坦坦率率的,以朗读的口气告诉你——扎西、卓玛、顿珠、尼玛、桑珠……一听就知道,他们深深爱着自己的名字。他们不是自己生造一个名字,名字里,是草原雪域,是太阳,是天风,是鲜花瑞雪,还有菩萨和神灵。
而相比之下,我们向来是聪明的造一个词,来做装点自己的标签。翻遍字典,动足脑筋,这些努力倒显得多余了似的。所有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努力,都近似于画蛇添足。藏人无姓,无字,也不起号。那是太琐碎和累赘了。该给自己取个啥名字,他们毫不困惑,降生时,抬头见啥,一团幸福的烛光,一片澄澈的晨曦,一株摇曳的小花,或者心里浮现出菩萨的慈祥面影,于是这些自然间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直接做了婴儿的名字。
我在八廓街的一角,看着信仰汇成的人流,肤色各异,形形色色,源源不断,虔诚又热烈地以大昭寺为轴心转动着。不管是谁,走进人流,就不由自主跟着别人的脚步,顺流而行。观光客似乎就成了朝圣者,眼光依然过于闪烁,脸上却努力收起来了轻慢浮气。这些不知何为佛的心灵,似也受到了某种触动,像在诠释“众生皆能成佛”。在人流中,多数是临时心动,那些远道步行而来的人,和飞机火车来的毕竟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脚步像钟摆一样不紧不慢,眼神里是一种充盈饱硕的空。你要是去和他们攀谈,其实很难进入一个语系。就好像我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名字不在一个语系一样。我们即使混进人流,我们在佛面前,表达的无非是我所求。但是,真正的信仰者,千里跋涉,关山烟雨,来到佛面前,想说的很多又什么都没能说完整,只是含着泪花,在心里一遍遍说:“菩萨,我来了。”菩萨记得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全一样,名字里的愿望,都明明白白在青天下、草原上。
顿珠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大昭寺做,相当于保安。对待进大昭寺的人,有时候很温顺,有时候很生硬地一定要对方出门票费。我不解,觉得他这样不好。他说,那些人是游客,又不是信佛。我说你这样凶巴巴的,不好吧。顿珠笑了,说你看金刚凶不凶。
心里有信仰的人,身上的气息简约质朴。想得太多的人难免给人累赘的疲惫感。在大昭寺里走走看看,看各种人群,看形形色色,就算人在红尘中怎么摸爬滚打,在大昭寺庄严神秘气氛中,人们一个个显示出一丝尚存的童性。在藏香极具宗教仪式感的气味中,人的身影恍惚间都变得缥缈了,似卸下了世俗的包袱,表现出作为一个人的可爱的一面。我觉得这种童性,实在也近乎神性了。
四、对酒当歌,所歌者何?
对于物欲横流的大城市来说,草原与山林的存在,是最后的救赎。我们没有远方,但草原上还有。失去了远方,失去了思念,就像心灵失去了忧伤和羞涩。没有远方,也就没有故乡。
站在牧区,极目远方,心里的纷纷念头,终于尘埃般在透明的阳光下落定。我说到高原或者草原的阳光,常常说透明的,因为只有这里的阳光可以当之无愧地说——“透明”。他赋予一切以光彩,又将一切的光彩轻轻抹去——它在这里,代表自然,主宰一切。
阳光下,我们想念远方,同时又想念故乡。对着云彩和云彩般的羊群高歌,歌唱眼前和心中的草原。人的诗性尚存,就永远在向往远方——与之同时,寻找故乡。
月光下,思念如霜花,无处不寒凉。美好的寂寞充满着思念,月光下响起马头琴温柔怜悯的悲凉。一切乐器有它自然的属性,如草木归属于四方大地。古琴韵归幽篁,二胡偏爱雨窗,洞箫意属秦楼,竹笛情寄孤舟。星光下,月影侧,劲草夕照,马头琴悲凉又热切地思念着,陶醉于纯净的寂寞中——天苍苍,野茫茫,故乡何处,总在遥远一方。
歌声之于人生,好比露水之于鲜花。人生几何,所歌者何?
每次和牧人同饮,看他们眼睛迷蒙着如寻找着梦想,脸庞羞红如少年,我知道,他们是要唱。每一滴酒都来自日月风露,每一滴酒又化为故乡之歌,借助人的咏叹,飘散风中,寄予旅人,寄予远方。
和牧人对饮,不用惧怕他们的酒量,牧民很少海量,就是海量,他们也绝不会把你劝醉。劝醉,不仅是对粮食的不珍惜,也是对客人的不尊重。对于远方的客人,他们有的只是谦卑的热情,绝不会借酒来成其他事。我常常想,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话,说的就是他们的待客之道吧。一个人对世界的态度,可以通过待客之道体现出来。最好的待客之道,当然是在敬酒之时单纯地视客人为客人。要做一个纯粹的客人,体验作客的趣味,最好还是去牧区。
在高亢起伏着的大草原上,落日把最后的云彩燃尽,悲壮地落入地平线。草原上为客人燃起了篝火。夜色愈发浓郁,如海面涨潮,流向草原。激情迸射的火星,映红了一张张未饮先熏的脸庞。四野里的寂静辽远,衬托着人们纯粹的热情。饮大地之酒,歌故乡之歌。
然而,让我窘迫的是,我作为客人,可以一饮而尽,却不能在席间以歌声来回报主人的殷殷盛情。
对酒当歌,我们歌什么?歌的土壤是故乡。然而踌躇街头,寻寻觅觅,找不到了故乡的土壤、土壤的芬芳,还有花果的飘香。引吭而不能高歌,是因为找不到了故乡之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