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恩典》许松涛散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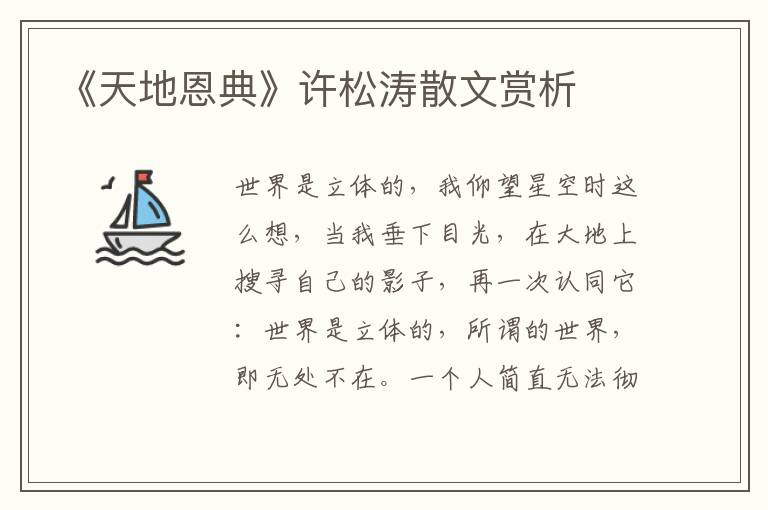
世界是立体的,我仰望星空时这么想,当我垂下目光,在大地上搜寻自己的影子,再一次认同它:世界是立体的,所谓的世界,即无处不在。一个人简直无法彻底认清这座迷宫。难道不是吗?我低头寻思,脚边一口阴暗的井,很老很老的井了,它属于某个朝代,它所在的位置,应该是从前某个大户人家的庭院,抑或是在某户恬静的四合院里,因为我几乎每去一个这样的地方寻觅古迹,井就在这些处所安静地迎来送往,用青苔,用安静的水银的波纹,我是根据一口井在这样的地方对端它的从前的,有没有道理呢,当然不由我断定。
再继续寻觅,就不是一口井那么简单了,我发现了脚下的河流,无论是宽是窄,无论是季节河或不是,无论它是否浩茫抑或潺潺,我都心生敬意,它跑了那么远,流经的地方那么多,即使偶尔断流,它总能与季节与天时相呼应,一条河的滥觞从此开始。我热爱每一条河流,像热爱每一口老井一样,我常常怀念老井时记起了每一条河,即使它们与我家乡的河流无关,我还是由此及彼地想到它们,它们依稀就流淌在我的生命里,像一个秘密的网络。我怀疑天人合一的相生相克关系被确立、被接受,从来都不是无端的,即使我宁可相信无中生有,但无端肯定不会存在。事物间秘密的联系和沟通,并非我辈有限的智力所能穷尽。我认为人体的每一条看得见的血管,错综复杂却井然有序地布置在应该安置的位子,恰到好处如本然天成。难道不是造物主的恩赐?难道不是天意的设计和神来之笔的安排?这些天衣无缝的对接,使我陷入对世界奇妙和神奇的叩问,结论虽不是我辈所能下的,却吸引了无数穷极物理的人们去探索,去开垦未知的空间。
我还是回过头来观察一口井和一条河的关系吧。恕我冒昧地打个比方,井在纵深的过程中,它是以最为简洁的路径、最短的距离,向一个更深的未知迈近,不止是一口水井,它长年累月安静地坐在院子的中心,给一个四世同堂的家族带来兴旺和安逸,带来祥和与底气,让青砖、黑瓦、檐角、青苔、衣架、立柱形成一个雅致而安谧的对应空间,将一个家族的气息和血脉在家与国的境界里持续绵延、繁盛下去,井也代表了一个家族的深度和缘起。仿佛暗示某种来历,强悍之中绵柔气象的彰显。井不说话,而所有的语言容纳其间,在厅堂、条几、八仙桌、太师椅和旗袍、马褂、山水字画和古筝的调和声中,茶、瓷器、陶壶、火炉、米酒中间,井是个安静的处子,又是个定力突出的奇人。井是一个家,一个村庄,或者一条街道的轴心?那么谁会认为轴心的位置给了井、给了水?不止是水井,井的族群也无限深广。油井,大地的深处,井并非与水构成唯一的亲缘,黑乎乎的井架为黑油油的深井向蓝天展示雄伟的高度时,谁会想到那些未来的烟囱以工业文明的名义来污染人们的肺叶呢,侵蚀人们的健康呢?我们从来不懂得大地深处的脉动,坎儿井,沙井,暗藏的力流在汹涌,仿佛那是一条河在某处的决堤,突然的强压使亿万年的流淌找到了喷发的出口,解脱羁绊,扬眉吐气,豁然开朗,甚至,这样的井喷不止发生在荒漠,还能展示在深海的沟槽,海上的钻井平台简直是一块漂浮在汪洋里的陆地。而一条河,九曲十八弯,在大地上漫流、低洄,似乎是浅吟低唱,但是有谁看到了它的强悍、暴烈与澎湃?这些河流首先挽留了迁徙的人群,他们不再逃难,命运从此安顿下来。从高空鸟瞰,那些河流像一张盘旋的唱片,围绕一根带磁性的唱针,发出四季的轰鸣,即使有沉寂的部分,它的乐音总在大地上缭绕,轻吟,盘旋,与天上的云朵和倒旋的星河遥相呼应,这是谁也不曾料想到的恣肆横溢又收敛自律的状态,与井对峙,交叉在无垠的时空之中,多像一个立体坐标系的本身,它们是早就被上苍设计好的物件,以河道和井壁的渠道,管制并有序地制动着星球的整体。疏朗。简约。固执。不可更改。
有一天,我在小城的古巷子里漫步,游走。城市是细密而繁杂的,掩映着来自远古时光里的气息,一砖一瓦,一巷一弄,青石板,凹陷在时间深处的辙痕,被磨砺得圆溜溜的黄花石,粗粝的石磙与石碾,它们的材质与井栏上的井栏材质无异,这些足以倾颓的物件,记录了时间的通道和里程,一如脚下的巷子存在,映照古今的变迁,它们是一群散落在时光缝隙里的纪念碑,是风通过的河流,是落叶坠入的井廊,我抚摸那些被粉饰后的墙,依然感知到内里肌肤的斑驳。我是自己的吗?一瞬间,我不忍质问自己,我立即否定了这个最粗浅的质问,生命的个体虽然发自自我,却孕育于自然的精气。巷子外是一条河,河水瘦瘦的,每年的汛期才能涨满,人们爱河,然后架起了桥,一座不大的古城,竟然有一条环腰的玉带,这河与一条著名的巷子依稀是天生的一对,那些巷子穿越旧时光的旧网,打捞岁月的鳞片,我在暗淡的灯光里闪烁着自己的影子,在漆黑的石板路上敲击出阵阵蛩音,物是人非,那些前朝往事都恍惚如梦了,而那些浸透前朝光阴的雨水,那些闪烁在头顶的阳光,分毫的差异也没有。那些斑驳的石墙缝里冒出的不是青藤,不是灌木的枝叶,而是来自时空的回音。浩荡,渺远,幽寂……好像这曾经的闹市,同样是更远古的山谷,空谷回音,那些没有流失的水土,又把我们带回到如今。从河沿上的八座不同材质的桥就可以历数时光的飞逝之快,河没有动,却因为桥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时间段落,每个段落都有各自的强音,如果我回到桥上,站在不同的点,都能找到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与之洽谈,即使年代有激烈和动荡的时刻,正如桥下的浪花挑选浪尖,我瞩目远眺贯穿在河沿上的风,以深邃的目光穿越面前无穷远处的飘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地经过桥上的人流,喧嚣与沉寂在一瞬间定格成一幅历史的画卷,不知今夕何夕,今年何年。
石桥,拱桥,廊桥,木桥,落水桥,人们从此岸到彼岸,桥是凝视河流的最佳过客,人们的身体离开水流威胁的第一选择是桥而不是船,这好像比船更可靠的桥任由水流激荡、穿越,这是水的追赶,更是时间的回溯,仿佛在向未知超越。我超越了吗?我无法回答。桥是静的,水是动的,这动静之间的聚会,仿佛是一种巧合,我在某个时刻来到桥头,再次验证了时间与一个人的契合关系。我喜欢梅雨季节的天气,这时的桥仿佛比时间更生动,上游的水势磅礴下泄,在这儿回旋,在那儿飞流直下,都是值得观赏的美景,我情不自禁地倾听水声,观激流,浑浊的水,野兽般成群奔突,狂野恣肆地撒野,是多么壮观和惊心动魄啊。而一座小城为什么要在一条蜿蜒的河上建这么多桥,我暗暗猜到了决策者的用心。那是对水的渴望,对时间流逝的追逐,对时空的作答和回应。我喜爱它的古朴,沉静,壮美,温文尔雅。除了每年的夏季,黄梅雨来临的前夜,这些桥就是风景,就是摆设,然而它最终形成为一道欣赏不尽的景观,来自建设者的匠心,人们把桥身建成彩虹的模样,叫它彩虹桥,人们将桥身建成回廊的模样,翘角飞檐,红墙粉柱,金瓯琉璃,南北风往来劲吹,拦截坝下的水,或汩汩,或潺潺,或款款,或嗒嗒,晚风习习的夏日黄昏,二胡的丝弦在这里呕呀周折,温馨的短笛在这儿委婉悠扬,黄梅调陪着黄梅雨,栀子花迎着老花腔,实在是文化古镇的绝配,在河岸的某条里弄里流连,简直是上天的雅意和成全。
我把井、桥、河流、巷子这些属于一座古老小城的物件排列在一起,忽然有了奇异的念头,大地万物从来就是相通的。尤其是喀斯特地貌的特征进一步被解开自然之谜后,我的这个信念更为坚定了。地下河,幽眇神秘,地下隧道,比比皆是,而在人潮拥挤的大都市,我简直为之震惊,人群如同土拔鼠一样,把地下掏空了,地下商场灯火辉煌,一时间简直不相信是在地下,形形色色的广告和灯光,在整个地下制造着白昼,制造仙境般的光怪陆离。地下的铁轨载着重负的喘息将人们不断送回地面,大地被无尽地开发,一直到某处的大地是空的!空城,不是人走光了,而是被挖空了。除了人们无尽地开挖宝藏之外,人们的生存空间已深入到地下!我从纵横交错的地铁轨道里退回来,回到我足不出户的小地方,再次走进那条寂寞的古巷子时,高高的墙垛把我与周围的市声远远隔开,我立即如同跌入陷阱,我有与世隔绝之感,尽管我还能透过头顶上的梧桐树枝看到上面蓝蓝的被弄得支离破碎的天空,我仍然心里滑过一阵寒彻,墙体厚厚的,涂抹了深重的黑,这更像被埋入地层的覆盖,我在这儿躅躅独行,仿佛走入一条地下通道,我恍然大悟,这条古老的巷子是多么幸运,它幸亏诞生在从前。倘若是现在,还能有这么安稳吗?有多少大型建筑设施能绕它而去?它的存在,得益于位置的偏僻,它将是多么幸运。这是地上的封闭与地下的开放在某个时节的交锋?
另外,我还领悟到,井、桥、河流、巷子,等等,它们是如此地有着同一的指向。它们虽然各为一方、不相往来,虽然有不同的用途、不同的特征,然而,它们共同在策划或指导着尘世,组成了一个彼此需要的格局,它们在时空面前有时竟然可以获得等号,可以发生意义上的交换,它们是时间意义上的魔术师,千变万化地圆通这个世界的来历,好像是个解释者,乃至我一次次联想到血肉之躯的身体。一个人以自己的肉身去寻访自然万象时,人的世界之谜刚刚解开一小部分,人体上的井在哪里呢,高速公路与河道在哪里呢?是肠胃?是神经元?是经络和血脉?在脏器的回环往复的迷宫里,一个谜一样的世界存在着,然而,我们因为司空见惯而消失了对它的好奇和仰望,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探究它的奥秘。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事实,常常由于我们目光的偏颇而丧失了追问的条件。在我路过街道上叫不出名字的巷子时,我想起了这是古老身体上的一根细小的神经,一个穴位,或者,一处等待我们揭开的谜团。我们其实是被谜团包围着,我们认识的日月和四季,我们所有的纪年,还有,仰观的天象,把它们画在纸上的图形,以及从地下发掘出的甬、剑、马车、陶罐等实物和模型,都是人类对自然叩问的佐证。那确实是我所要探寻的通道,然而,大自然的神秘依然深不可测。
星空还是那个星空,地球还是那颗地球,而大地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大地了,今天的大地除了自然力原始作用下的地貌山川河流湖泊之外,还留下越来越多的人类的痕迹,代表人类的意志和智慧在思考的航程中的行走,有时,为了欲望的满足,我们不惜为之疯狂和唯我独尊地处理了自然与自己的关系。我看见的那些老井渐次消失,它们在人类的抛弃中显得落寞惆怅,同时又孤傲无比。在老家的一个塘坝下,原先有个井台,我曾经在那里取过清水供烧饭和饮用,我用两只小巧的木桶担起它,晃悠悠地往家里走去,随着脚步的趔趄而颠摇出的水散落一路,恰恰给我描画出一条路线。后来我发现井干了,随后发现井被丢弃的杂物填塞了,渐渐被改造的塘坝埋没了,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可是它依旧像一只枯干的眼,在我的心里偶尔眨巴着它灰暗的眼神,我不止一次想起它曾经的鲜活存在,人们淘一口井的场面依旧在我眼前浮现。我在一处开发的老街院子里徜徉,一口天井里的井吸引我的脚步,我走过去,映照的是一方小小的天空和天空下一张飘忽不定的脸,那脸来自古人还是我呢?不甚分明,光线暗淡,井口的水面像一张模糊的底片,来自岁月的漫漶时光,我一时语噎,僵滞在那里。我转过身时,院子里的草在疯长,花在盛开,虫鸣唧唧,阳光灿烂,是个晴好的春日,我的心被这盎然春色挽住了。时间让我记住了,我真的记住了:一切接纳都是恩典!
我在大地上行走。这是一个人与蚂蚁的生命共同的趋同。没有什么惊奇,我沿着河流走,翻越高山走,趟过沙漠走,我从来都走在我想象的意境和绝境,或者我并不完全走在真实的大地上,我顺随梦境和年华地流淌自己的意趣和感觉吧,我即使偶尔离开生养我的小城池,我还是没有觉得走远,我在一座小站走下火车,我回到我的小房子,在熟悉的场子上收割玉米、大豆和麦子,我依旧还是被门前的一弯溪流所打动,我喜欢这样细小的流水,轻盈,迟缓,波澜不惊,齐岸而行的并不是河流,还有大地上的万物,那些花朵,青草,庄稼,屋舍,柳丝,炊烟,城镇,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虫子和树木,哎,我以短暂的光阴来分享这永恒往复的景致,四季流淌,时光荏苒,星河垂落,红日东升,那些歌吟不尽的雨水,那些缤纷纯洁的雪花,那些燕子和蝴蝶的踪影,都是大地上的物产,都是上苍慷慨的恩赐。我的精灵之物,总没有理由不接纳呢!
我挖向属于自己的井,一锹一锹,是我对生活的宽度和长度的丈量,那是河流和井的共同杰作!我不停地挖!挖!挖!
任由灵魂飞舞吧,我是萤火虫,我是草叶上的露珠,我是灰烬燃烧后留下的余光,我边走边唱,我仰望星月,我边走边舞,好像长不大的孩子放归自然,自然与童真是一体的。我不断地死亡,又不停地重生,我蜕下了壳,我也作茧自缚过,不过,我还是要破茧的,每每的我,忽然来到一个陌生而更为新鲜的世界,兴奋着,流连着,颠仆着,一点也没有计较和悲切,我有无数的问题需要追问,需要来自风和大地的回答,但我更愿意把一切放下。我随着河流奔跑,我在栈道口伫立,我边走边猜这时间的谜语,我走在流水的影子里,日光照彻,笑声响亮,我不记恩仇地坦然面对所经历的一切,一个人,一粒沙子,一阵风,大自然里可以过滤出太多的清纯和天真。是的,还是把自己还给单纯的大地、勇敢的河流、苍翠的群山吧,我举起右手,给这个世界一个深刻的造型,我将起航或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