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平范墩子《永不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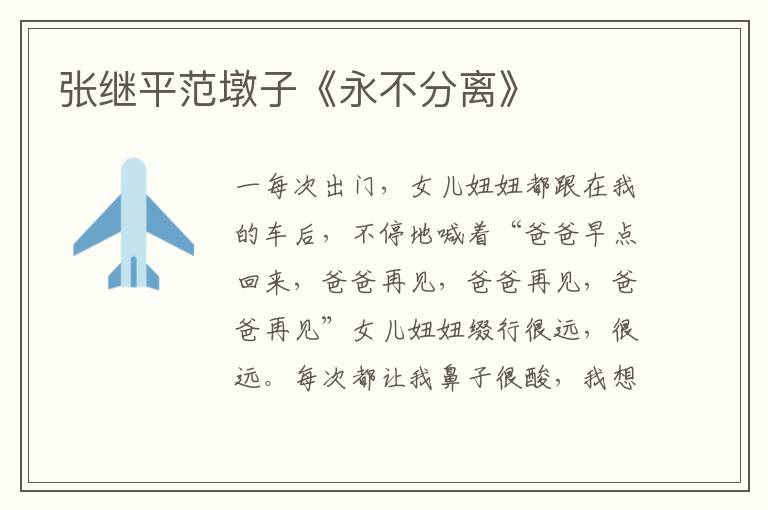
一
每次出门,女儿妞妞都跟在我的车后,不停地喊着“爸爸早点回来,爸爸再见,爸爸再见,爸爸再见”女儿妞妞缀行很远,很远。每次都让我鼻子很酸,我想这孩子,从刚开始走路,就这样粘着我,现在都快五岁了还这样,唉——这孩子。这次出门,因为生气,走得太急,连给孩子说声再见也没有,唉——这孩子。
这条高速路我很熟悉,今年中秋节高速路免费通行,这可是一个好消息,趁农民的洋芋开挖季节,我抓紧收购了10吨,赶紧上路了。
节日期间高速路上车实在太多,这不得不让我小心翼翼。但越是节日里,赶着过节的小车司机们越爱超车,他们见缝插针,而大车司机们却也是牛气冲天,一副高高在上,横冲直撞的样子,我这菜车则是介于小车与大车之间的货,哪边也不敢得罪,虽然我的心里很毛,这满车的洋芋,这大热的天,在路上也不能耽搁呀,一旦发热,一坏一大片呀。
我就在小车们穿来穿去、大车们风驰电掣中战战兢兢,躲来让去中艰难行进着。天乌蒙蒙的,似乎要下雨的样子,我说要下就赶紧下吧,不要再这样阴沉沉乌蒙蒙的了,这样的天气影响心情是小事,关键影响了我的视线,越是阴天,我的眼睛越是干涩,我努力把两只眼睛睁地大大地,努力扩大光线的接受区域,可因为干涩,上下眼睑不停地眨来眨去,它们本想给我来点润滑的,不想却越是把我的眼球擦得生疼。我狠狠地骂着自己的那几片眼皮:“奶奶的小呆皮,以为自己是雨刮吗,可老子的眼睛还没有下雨呢,让你们卷起来不要动,你们偏就眨巴个不停,奶奶的小呆皮。”
因为揉眼睛,我动作稍慢了十万分之一秒,却见一辆兰博基尼小轿车已经插在了我与前面大车的中间,我吓坏了,我要是稍稍跟进哪怕一点点,这辆小轿车就被我顶进大货车的屁股里了,不要说顶人家兰博基尼,把人家碰一点点,都有可能让我陷入万劫不复的财务深渊,我的这辆车包括这一车的洋芋疙瘩抵不上人家的一只轮胎,可跟在我屁股后面的一辆大车却一点点也不退让,这让我头顶上腾腾地冒起了汽,我感觉我的后车厢被顶了一下,那是后面的大车在警告我呢,我的车在人家大车面前,不过是一脓包而已,我赶紧又眨了一下眼,想把车向外让让,心里想,你们都牛得不行,那你们都超吧,可不曾想这一让,却把我丢进了高速路边的十几米开外的深沟里。
在10吨重的车翻下路基的那一刻,我还没来得及想任何事,因为当时我的心里一片空白,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车往路基下冲,接着是侧翻,然后滚动,我脑子虽然是一片空白,却是从来也没有过的清醒,我分明看到了我的妞妞在前面喊着爸爸,她看见了我,立刻伸出两只手向我冲了过来,我也不由地伸出手去迎接,但却听到自己的腿咔嚓的声音,我竟然没有一点点痛的感觉,在剧烈的颠簸震荡中,我无比的清醒,我极力想着防护自己的头和内脏,至于胳膊和腿我早已顾不上它们了。所以当腿被卡断的那一刻,它们都已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外,一点也没影响到我采取抱紧双膊防护重要部位,我最害怕就是方向盘压过来,压坏我的内脏,所以我的两只胳膊握紧了拳头挡在胸腹前面,可最终自己的头还是撞在了驾驶仓挡风玻璃上,挡风玻璃被我的头撞得突然裂开的那一瞬,我心里说,我完了,我彻底完了,可我却看见了车窗外苍黄的麦田,眼睛一点点也不干涩,雨水混和着血液流进眼睛的感觉非常逼真,就在这一刻我从来也没有过的强烈的愿望升了起来,我知道我在流血,而且是大量地流血,我的血已经从翻了个儿的驾驶仓外面与雨水形成了一片血池,在倒翻着的车顶上,看起来无比恐怖,那是血呀,我的血有那么多?再就是我那10吨洋芋拥堵在驾驶仓周围,还有许多的洋芋从破了的挡风玻璃处滚进了驾驶仓,几乎要把我埋了,我迫切地想看到有人过来,帮我一把,我想活,我太想活了,起码让我看到我的妻子和我那还不满五岁的女儿。
二
我想喊救命,但我喊不出声来,涌进来的洋芋太多了,它们堵住了我说话的空间。盼望着盼望着,我的神志却不由自主地渐渐模糊,我的眼帘不由自主地紧紧闭上了,我又看到了我的女儿站在大门口看到他的爸爸贩菜回家,张开双臂跌跌撞撞一路跑着一跑喊着爸爸,又看到了妻子不断地埋怨我,抱怨家里的穷困,报怨我一出门那么久,家里忙乱不堪,报怨十几年前她的不明事理嫁给了我,她的脸面不是很清晰,但却让我看到我自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猥琐的样子,我似乎天生就亏欠着她,一辈子都还不清,所以一辈子都无法抬得起头来,所以她的脸我始终记得很模糊,又看到了我的父母年轻时的样子,我像我的女儿一样等待着他们收工回家时的欣喜若狂的样子······
当所有的人事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面前逼真地上演时,我头脑里还有一个声音在呼喊着,你必须醒来,必须醒来,赶紧醒过来,否则你将滑向死亡的深渊,所有逼真的影像都是死亡前脑子不受意识控制而产生的放电效应,就像电线短路时,电器被烧坏过程中的打火现象。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拼尽全部力量睁着眼睛,但每次用力,我的双眼皮似乎是有着千万千的巨门,我现在再也不敢报怨这两对眼皮是小呆皮,我耐心地一边劝说着它们为我的眼睛开门,一边使出浑身的力量撞击着,我的力量在这沉重的巨门面前被撞得闪出一道道强烈的光茫,在我不懈的努力下,我终于顶开了我的双眼,一丝清亮的光线透进我的瞳孔,我看到了一张张奇怪的脸和眼睛。他们被我睁开的眼睛吓了一大跳,他们趴在车窗前,拿着蛇皮袋子扒拉着滚入车窗的洋芋。有人反映过来,说:“咦,司机还活着。”忽啦一声,拥在窗口的几个人散开了,我又使着最大的劲向他们呼喊:救命,帮帮我。我不知道他们听见没有,老半天没人过来,我的双眼几乎又闭上了。过了不知多久,我的耳朵分明又听到有人欣喜地喊:“死了,死了,呵呵,快装快装,司机已经死了。”
三
本来真的已经死了,可听到他们这样说我,他们的话再次强烈地刺激了我,我想,不帮就不帮,凭什么说我死了,我是不会死的,你们说我死了,我偏就不死,洋芋你们拿走就是了,放心,我都这样了,我不会向你们计较,既然你们要拿,就拿吧,我索性把眼睛闭上,你们就当我死了,只求你们把洋芋从我身边快快搬走。他们果然迅速在我身上扒拉起了洋芋,只是他们动作太粗暴了,有人竟然踩到了我的脸上,估计我的脸上的肌肉已经懒得再顾及什么脸面,所以也没什么表情给他们。
我天生是个倔强的人,谁说我不行,即使当面我不辩解,背后我都会更加努力,虽然我的努力仍然不过是原地踏步,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也不甘心放弃。说到放弃,这让我又想到了我的妻子,想到她,我觉得十分歉疚,就在这次临出门,为一句话突然与妻子爆发了一场争吵。这缘于女儿从幼儿园回来说的话:
“爸爸妈妈,我们班上的小强说他喜欢我,他会永远都对我好。”
“就像我对你妈妈这样,是不是?”
“不是,妈妈说我长大了再也不能找像爸爸这样的男人,但我爱爸爸。”
“那是你妈妈胡说呢,她呀,其实也像你一样爱爸爸。”
“打住吧,跟了你这样差劲的人,也就算认命了,我的女儿决不能再找像你这样的男人。”
“在女儿面前怎么说话呢,我差劲得很,你早干啥去了?”
“我瞎了眼了。”
······
架吵得很激烈,女儿妞妞就在一旁放声大哭,我感觉我很对不起女儿,内心歉疚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已经爆发了,再多的歉疚也像是水沷在了汽油上,不单灭不了火,连水也成了火,我几次甚至都忍不住把拳头对着妻,威胁着她了,虽然我从来没有真正动过她一手指头,但我仅仅因为向妻子攥了拳头,而更加懊悔。在怒不可扼的极点,索性摔门而去。
女儿妞妞还是冲出门去,一路跟着我的车屁股连哭带喊:“爸爸早点回来,爸爸再见,爸爸再见——”我则是气晕了,头也不回,菜车冒着一股股黑烟,疾驶而去。
现在我出了车祸,我知道满世界也没有人会帮我了,刚趴在车窗上扒洋芋的人都是附近的村民、流民,他们那是趁火打劫呢,不过出了车祸倒在路边的洋芋呀、日用杂货什么的,被附近的村民抢了那很正常,说白了就是不抢白不抢,抢了也白抢,你想想,车都翻了,甚至人都死了,车上的一些菜蔬、杂货又有谁会在意呢。现在这样的状况,我最渴望出现的一个人还是我妻子,甚至现在出这样的车祸,我都觉得这是我的大错,是我对不起她,她十几年跟着我受穷受苦,我还怎么敢出这样的差错,我真的有点差劲,唉,我很后悔出门前和她大干了一场,唉,细细想来,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十几年来反反复复陈旧得不能再陈旧的一句话,我当时又何必那样在意呢,只怪我鬼迷了心窍。
四
此刻我的身子动弹不得,我的血还在流,可我的脑子却异常的清晰,尽管我明白我的大脑因为濒死之前的异常放电刺激了大脑中许多平常没有发生过的链接,然而在不断异常放电的大脑中,我却突然迸发出一个清晰的想法——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个想法竟然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很难认同这个想法,于是在我即将失去思维的那一刻,大脑深处对我和妻子十几年的婚姻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和推理。我像突然成了两个人,我大概已经被突如其来的车祸撞得人格分裂了。一边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一边是我不相信。
妻子近年来对我越来越不耐烦,她已经认为我注定了将一事无成,曾经我对她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几乎成了我行骗的口实。我没有给她带来体面的生活,生活十几年一成不变,她注定就像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的那个守着破木盆的老太婆,那也是她极不愿意看到的自己的结局,她不停地报怨着她还年轻,却什么也不敢穿,什么也不敢买。我承认这都是我的错,当年我还年轻,总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也确实好了许多,我盖了新房子,我买了自己的农用拉菜车,我也有了自己的女儿,关键是虽然我这样好起来了,可比起大多数人,我却绝对地落后了,他们大都住上了洋楼、拥有了自己的私家小轿车,他们还拥有股票,拥有不下一处的房产,相比之下,我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更显得像个穷人了。
有时我想这样也挺好,我也算有房有车,有老婆有孩子,知足常乐,可妻子却不这样想,女人总是爱攀比,这一攀比,就有了差距,有了差距就会产生报怨,她一报怨,让我就不能懈怠,我就会加倍努力,尽管有压力。都说伟大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但我认为,或许女人的报怨也是一种激励,要是她不报怨了,男人也就少了斗志了,这日子过得或许还不如现在,这样一想,心下也就释然。虽然老婆不断地报怨着唠叨着,但生活或许就是这样,谁家的女人不报怨呀不唠叨呀,生活中若少了女人的报怨和唠叨,这还真的像吃饭没有盐巴,吃肉没有大蒜那样,缺点什么。
只是这样的报怨有时候真得令我很烦,我似乎并没有养成别的男人那样的好脾性,女人即使再怎么任性,也能做到不急不恼不争不怒,我也常常阅读别人微信发来的心灵鸡汤,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男人,可总有那么一天我会突然被妻子的某一句刺激而惹恼,关键是我恼了不要紧,我一恼,她更恼,这就会坏事,然后总是无法控制地大爆发。这一爆发,似乎把平常积累起来的所有报怨和唠叨都要进行一次清算。我才明白,其实每一句看似不经意的报怨绝对是人灵魂最深处想法的自然流露。对于女人,她只当自己经常的报怨是一种习惯,她总觉得她的心是好的;对于丈夫,他觉得女人的报怨只是她顾家的一种表现,他觉得他的女人的心是好的。然后他们都欺骗了自己,报怨绝对是一种伤害,只是这种伤害迟早会以真面目展现出来,或者来一场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争吵,每一次激烈的争吵就相当于一次严重的事故,那么结论无疑导向,若只有一次最严重的事故,那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不相信,我的妻子不会丢下我,绝对不可能——我的头脑在争论中嗡嗡作响。
对于大脑中做着这样无谓的辩解及争论,我实在烦不胜烦时,会狠狠地骂自己,都什么时候了,还胡思乱想,还自己跟自己争论不休什么,钱大有,你给我赶紧醒过来,醒过来,钱大有,钱大有,醒过来。在我的不断鼓励和激将中,我的眼皮重新打开了,我看到天上还下着毛毛雨,我的车子底朝天躺在高速路下面的一条沟里,当我血肉模糊地爬出驾驶仓,天上下着碎雨,我浑身湿透,我满车的洋芋空空如也。我似乎并不在意这个,我还笑了,因为我发现居然我还活着,只是我的两条腿,自大腿以下,从膝盖以上一札的地方,分明已经与我整个的身体不相关了,我明白肯定是车子滚下山沟时,驾驶室受到冲击变形,首先夹断了我的双腿。于是我奋力向高速公路上爬去,我想要活着,我还有妻子和儿女,我必须要见着她们,而且我的菜车以及收购了洋芋的近二十万元的货款还没有还清,我不能把债务留给她们。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决不服输的男人,我必须活着,我还有许多的设想,我的腿断了,我的其它大件都还好,而且腿或许还可以接上,现代的医学很发达的,接腿也用不了多少钱。我终于爬到了公路边上,我对自己感到了满意:钱大有,你还成,这么高的坡,你都能爬上来,看来一切都不成问题啊,你还没有被打败,你还真得不错。
虽然爬到了路边上,虽然一辆又一辆的车在我的身边旁若无人的疾驶而过,但我一直坚信,总会有一辆车停下来把我拉到医院去的。哪怕是没有一辆车拉我,我的妻子也能感觉到我出事了,她会带着女儿很快赶过来的。我渐渐感觉到头越来越疼,也感觉头似乎哪里不太对劲,我一摸,吓了一跳,发现我左边脑袋的一块骨头象瓦片那样直立着,我轻轻一拔,它竟然掉了下来,我握在手里,它竟然有茶杯底那么大一块骨头,那是我的颅骨!我再摸摸那地方,除了连着的一块头皮,我分明摸到了我的包着脑浆子的簿簿的脑膜,所幸脑浆子没有流出来,所以我没有死,所以我竟然能清晰地进行着思辨,两个人的思辨,但是我还是被手里的这片自己的颅骨吓懵了——我的脑袋竟然被撞开了一个大洞,我还能活吗?
五
当我醒来,我躺在一家医院里,我的腿自大腿以下已经被切割,我的脑袋掉了颅骨的地方蒙了一块不锈钢板。我问医生:“我是谁送来的?”医生说:“交警,他们拖了你的菜车和你,说司机已经死了,先送医院太平间,再联系家人的,再送火葬场的,可当时也没法联系你的家里人,而且医院太平间也满员了,在这秋老虎的季节里,只能先火化,就在送往火葬场路的过程中,你突然自言自语起来,于是又把你拉了回来,做了基本的处理。”我又问:“基本的处理是什么?”医生说:“截腿,给你头上蒙了个不锈钢的铁皮,输液消炎。”我又问:“为什么截了我的腿?”医生说:“你那地方骨头都成粉碎状了,接不上。”我再问:“为什么不用我自己的颅骨?”医生说:“你的脑子都露了出来,谁敢在那上面做动作,找块铁皮盖上又简单又保险。”我说:“我还能活多久?”医生说:“按你的情况,活多久得看花多少吧。”我说:“得花多少钱?”医生说:“最基本的也得花个一二十万吧。”我说:“老子连一分钱都没有啦。”医生说:“那你起码得缴纳基本的救治费。”我问:“多少?”医生说:“锯腿、包颅骨,最优惠也得五万元。”我说:“操,老子连一分钱都没有!”医生说:“你说了不算,我们已经联系了你的妻子。”我问我的妻子怎么说。医生说,她没有说话。我说:“我妻子也没钱。”医生说:“市交警大队说你的菜车还算完整,要是你不缴钱,只能用拍卖菜车的钱来顶账了。”我看了看我的腿,说:“罢罢罢。你们就把菜车拿去吧,反正我的腿也这样了,菜车对我也没用了。”医生说:“你们这些下等人怎么都这么无赖呀!”我心想下等人怎么了?医生立马对医院的保安说,这个人是个穷鬼,不缴钱在这耍赖呢。
我被医院抬出了病房,我给他们说,起码让我的妻子来接我呀,他们说,就在医院门口等吧,像你们这样的人,都是属狗的,命是又贱又硬,一时半刻还死不了。
我被扔在了医院的大门外面,这是在哪里呢?我听见街上来往的人都说着陕西话,我想我是在西安了吧。家乡离这里四千里路啊,我的妻呀,你快来吧,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了,你快来吧。我摸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妻的手机一直是忙音。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自我被医院抬出来到今天,已经整整七天了,我天天被西安秋天的大太阳暴晒着,我的伤竟然奇迹般地好了,我笑笑想,我的命真的是狗命呀,又贱又硬。
现在已是十月份的天气,只不过颅骨那里被铁皮蒙着,天气一冷,那里冷却快,头就疼,也不能在大太阳下晒,一晒头更疼。往往一疼起来,我就变成了两个人。一个冷静而理智,一个暴躁而感性。每到晚上天气冷下来,我针扎似地锐疼时,我就想到了妻子,想到了夫妻本是同林鸟的可怕的真实,每到白天气温升高时,我的头像棒敲似地钝疼时,我就想起了我的女儿,想起了她张开两只小手向我奔跑过来的情形。
我已经花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钱,再等下去,我就要乞讨了,一想到这个词,我就坚决否定了,我是有尊严的男人,我是一个大丈夫,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去乞讨,虽然有人路过我时,还以为我是个乞丐,会主动丢下一元五元的零钞,我就会绷圆了眼睛大声说道,我不是讨吃,拿回你们的臭钱。看着他们惊愕的样子,我一脸的凛然。虽然这样,我明白,一分钱也会难倒英雄汉,更何况我还不算是个英雄汉呢,所以我必须要回去了,我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
六
我回来了,准确地说我是一下火车就爬着回来了,我没有看见我的女儿张着双手飞奔而来的欢欣。门是虚掩着的。我爬到门口,只一推,我就顺势栽到门槛里了。我喊妻的名,没有应答,我喊女儿的名,也没人应答,我又爬到了屋门口,轻轻一推,屋门也是虚掩着的,吱呀一声门开了,屋里很暗,冰灰冷灶,显然已经多日未动烟火了,我喊我女儿的名,妞妞,我的妞妞。里屋传来了一个声音,非常非常虚弱,像是漂在空气中的微尘那般的微弱,只有在光线下才可以听见,也只有骨肉亲情的我才可以听见。是女儿的应答,这决不是幻觉,我摸到了炕头,我攀着两手上了炕。女儿躺在炕上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我抱起女儿,这分明是饿的,女儿看到我眼里流露出强烈的光芒,一下子就点燃了我。我已经什么都不愿意想了,我像了正常人一样,我竟然很快给妞妞拌了酸汤面糊糊,一勺一勺喂着她吃下。妞妞终于有了气力,她开始哭,抱着我哭,我也哭,我们父女俩什么也不说,就是哭,似乎只有哭才是最好的表达。哭过后,妞妞就睡了。她睡得那么苍白,却是那么甜。
七
夜深了,大西北的天凉了,我的头开始疼,脑子却无比清醒,我已经知道一切了,虽然妞妞什么都还没有说。但我知道,我必须面对我与妻的真实,妻的做法是对的,我不怪她,要是她不走,我们一家谁也过不好,她走了,对她自己对我以及对妞妞都好。只不过她走时,竟然把妞妞一个人放在家里,这女人的心啊。可我这个样子,又怎么养活妞妞呢?我头疼得越厉害了。但我一声都不吭,我害怕吵了妞妞,她睡得实在太香甜了,也只有这样的疼痛才算是对女儿的补偿吧,我竟然心里第一次感激这样的疼痛,这一感激,疼痛竟然带给我无比的幸福感。再次见到女儿,她竟然把我的被撞得分裂了的双重人格给重新融合了起来,我的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慈爱,我甚至感到了人生无限的美好,我差点都笑出声来,我都这样了,怎么可以笑?但幸福真得是那么的逼真,逼真得好像只有我成这个样子幸福才真正降临到了我的身上,我真得一点点都不怪我的妻子,虽然我还不知道妻子为什么离家,但我特别想把我此刻的幸福感告诉她,毕竟她与我十几年的夫妻了,再怎么说都是最亲的人。
我都这样了,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女儿,还能在女儿最危难的关头出现,而且从此以后,我与女儿再也难以分开了,想到这里,我竟然忘记了头疼,我兴奋得快要晕厥过去了,极度的兴奋带来的是极度的疲惫,在天快亮时,我睡着了。
我看见女儿站在我的身边,笑盈盈地看着我,女儿的脸圆嘟嘟,微微泛着光,她的身后,阳光灿烂,我家里满屋满地满灶台都盛放着大团大团的花,红的耀人的眼,女儿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我乱逢逢的胡须和头发。可是我醒不来,我一直在梦中,任她这样看着抚弄着。我感觉我的眼泪一直流着,我想要睁开眼,但努力了,还是睁不开,这与我出车祸时快死的时候有点像。此时我意识清晰,就是睁不开眼,我明白,此刻我是处于极大的幸福中不愿意醒过来。
与车祸当时我那临死前的挣扎情形不一样。但我幸福着幸福着突然感觉不安,我是不是又处于死亡边缘了,一个声音自远而近传来:你的情况,随时都可能死亡,极可能是暴死。你要有心理准备。当时我还对医生们发狠,我不会死,我决不会死,等着瞧吧。而现在,我已经见到了女儿最后一面,按说我已经完成了心愿,这已经是老天爷给我最大的恩惠,让我在人间多留几日,一旦完成心愿,冥间的小鬼们可就要来索命了。我决定再求求他们,因为我昨天自见到女儿的那一刻已经发过誓,我与女儿,我们父女俩永远也不分开。于是我再次拼尽全身的力气,内心深处积蓄着足够的力量,想要顶开那两层对我的眼睛,我的生命关着沉重大门的眼皮,努力着努力着,可当我刚要用力,眼帘竟然轻轻地就张开了。
我看到了我的女儿真的站在我的身旁,我躺在炕上,身上盖着被子,我的身子被包裹得很严实,女儿头发枯黄,脸蛋如被刀刮了一般,房子里十分昏暗,我只看到女儿的黑漆漆的眼睛,她的双手不断地摩挲着我的胡子和头发,见我醒来,她眼泪扑簌就滚下来,她扑进我的怀里,放声大哭:“爸爸,你怎么才回来,爸爸,你怎么才回来!”
一向从不落泪的我,紧紧抱着瘦得不成形的女儿放声嚎啕。我问女儿:
“你妈妈呢?”
“走了。”
“她咋不领你走?”
“我不走。”
“你为啥不走。”
“我等爸爸。”
“妞妞,你不知道,爸爸出车祸了吗?”
“知道,传来的话说你还活着,和死了一样。”
“谁传的话。”
“电话上,要妈妈去处理你的尸体。”
“妈妈怎么说。”
“她说没钱,要医院看着办。”
“家里好吗?”
“天天都有人过来和妈妈吵,要妈妈还他们的钱。”
“你应该跟妈妈走。”
“我不走,我要等爸爸,我知道你活着。”
“你看你都成什么样了,我要是不来,你要被饿死呀。”
“没有爸爸,我也不想吃饭,我知道你会回来。”
“知道我会回来,你还不吃饭!”
“我要和爸爸一块吃。”
“对,一块吃,一块吃,爸爸再也不离开你了。”
“爸爸不要哭,不要哭。”
“爸爸这是高兴。”
八
大西北的天气太冷,我的头上那块铁皮经不住冷,头疼。早晨的太阳透过窗户,我突然看到我那覆着铁的脑袋边上也透出了一线束光。
“爸爸,你的头上有光耶。”
“我也看到了,爸爸现在是铁头了,太阳一照,就有光。”
“不对不对,那束光是透着你头上的铁皮从里面出来的。”
“真的吗,呵呵,我的妞妞,爸爸的头以前是个榆木疙瘩,现在被撞,就是老佛爷所说的开了光啦,我们以后有好日子过啦。”
“我什么也不要,我不要好日子,我只要爸爸,我要永远和爸爸在一起。”
“爸爸再也不离开妞妞了。”
“爸爸,你回来,他们知道了还要来。”
“他们?”
“要账的人,他们还说要让警察来抓你。”
“妞妞,他们是吓唬我的妞妞呢,爸爸不怕他们,而且他们再也抓不到爸爸了,爸爸再也不离开妞妞了。”
“妞妞也不离开爸爸。”
“我和妞妞从今天开始要走天下了。”
“天下在哪里?”
“天下很大,大得永远都没有边。”
“那你怎么走,爸爸,你腿都没有了。”
“爸爸用手走。”
“爸爸真棒。”
趁着西北大地上第一线曙光的来临,我带着女儿乘上了驶向南方的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