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书的未来》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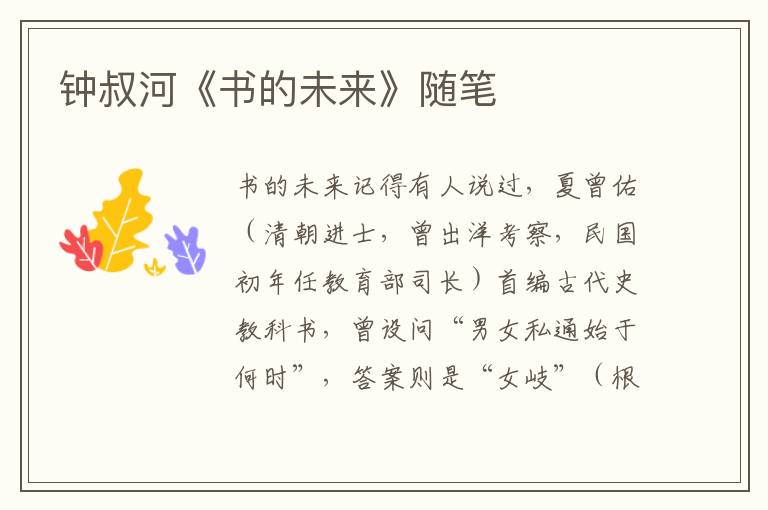
书的未来
记得有人说过,夏曾佑(清朝进士,曾出洋考察,民国初年任教育部司长)首编古代史教科书,曾设问“男女私通始于何时”,答案则是“女岐”(根据大概是《楚辞》王逸注云“女岐无夫而生九子”)。此问此答,真的妙不可言。
如果早生四五十年,有幸读夏先生的书,恐怕只能老实回答“不知道”。因为有人类便有男女,有男女便会要“通”,人类历史少说已经几十万年,明媒正娶依法登记这一套却不过实行过千百十年,在有巢氏的巢中和山顶洞人的洞里,怎么知道男女们在私通还是在公(?)通,他们的“通”又“始”于公元前几十几万几千几百几十几年呢?
这次薛君叫我谈图书的未来,西谚云“欲知其未来,先明其原始”,所以无妨学学夏先生,先来问问人们称之为图书的这种东西始于何时,如果仍援夏先生之例,也许可以答“河图洛书”吧。“河出图,洛出书,圣人(伏羲、大禹)则之”,以成八卦九畴,这是《书经》和《易经》中的话,比屈原问“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更为“经典”,但同样也如司马迁说的“缙绅先生难言之”,作不得数。
其实人类自从野蛮开始进入文明,便有了交流、学习、传承的需要,也有了想象与祈求。三千年前殷人用锐器刻在甲骨上的,四千年前两河流域人用小圆棒划在湿黏土板上的,五千年前古埃及人用炭黑写在纸草(papyrus)上的,直至二万五千年前克罗马农人彩绘在法国和西班牙洞穴石壁上的(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彩图第七页),都是先人的创作,先人留下的信息,也就是真实存在过至今还存在(当然只能存在于博物馆和图册里)的“河图洛书”。
我们的图书就是这样产生、发展、延续下来的,它们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只要文化不灭,图书也就不会灭亡和消失的。
当然,人在变,文化在变,图书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可能不变。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串联简册的皮条翻断了三次,因为那时的书是写在一片片竹简上,再用皮条串联成册的,反复不断地翻读,皮条也禁不住。这比起今天用电脑,在阅读器上读书,书之重轻和读之难易,变化确实极其巨大。但是不是用阅读器读《易》就能比孔子读得更好呢,恐怕谁都不敢拍胸脯保证。
予生也晚,从小读的就是铅字印在纸上再装订成三十二开的平装书,但小时候在老家书房中,稍大后在府后街和南阳街的书店里,入目触手者仍全是木刻线装本。避着父师自己偷看旧小说,从《施公案》《七侠五义》到《西游记》《三国演义》,有光纸上石印小字看成了近视眼的,也全是线装,随时可以卷起来塞入裤袋,装作听话的好学生。
未来的书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真不知道,是不是都会缩到阅读器里头去呢,恐亦难说。我想,即使阅读器真能全面取代纸本,也不过和平装取代线装、纸本取代竹帛、竹帛取代甲骨一样,又来一次世代交替而已。模样再变,供人阅读的功能不会变,人们读它,还是在读书。
老实说,我对此并不怎么关心。来日既已无多,架上的旧书且读不完,未来的书还读不读得了,读不读得懂,犹如太阳上的氢还能烧多久的问题一样,于我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