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跟盛唐诗人学到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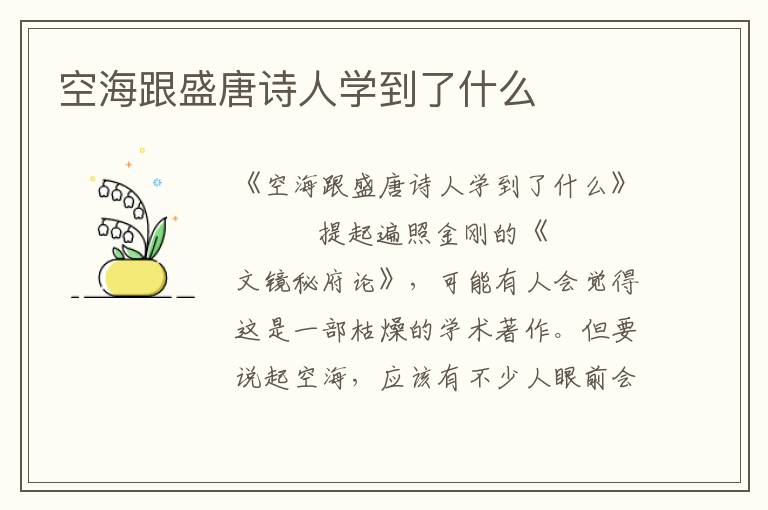
《空海跟盛唐诗人学到了什么》
提起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一部枯燥的学术著作。但要说起空海,应该有不少人眼前会马上浮现起当下流行的电影《妖猫传》中那个萌萌的日本小和尚形象。空海这个人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他就是《文镜秘府论》的作者遍照金刚。当然,历史上的空海,跟小说和电影里的空海并不是一样的。
空海于公元774 年出生于日本的一个贵族家庭,比白居易小两岁。空海从小就从舅父那里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教育。成年后,除了精研佛法,他也一直对中国诗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来中土之前就写过一些诗论。30岁时,空海随遣唐使来到中土,途中真的经历过海上的风暴。中土的游学经历只有短短一年,却使他对佛法和诗学都有了更深的了悟。回国后,他创立了日本真言宗,又根据从中土带回的诗学文献,加上自己的理解,编写了《文镜秘府论》一书。
《文镜秘府论》属于“诗格”类著作,就是后世诗话的前身,可以粗略地理解为教人怎样写诗的书。这类著作,在唐代是颇为流行的。不过,我个人并不建议初学者拿着《文镜秘府论》或者其他的“诗格”学写诗,因为这类著作离初学者的现实需要,还是有距离的。事实上,在像唐代——或者今天——这样一个想学写诗的人越来越多的时代,既然有想学“怎样写诗”的需求,那就必然有想学“怎样教人写诗”的需求。在我看来,“诗格”类的著作,与其用来教人“怎样写诗”,还不如用来教人“怎样教人写诗”更实在些。也就是说,“诗格”与其说是教材,不如说是教学参考书。当然,天资高的学生拿本教学参考书来看,对学习也会有帮助,但教学参考书的打开方式毕竟跟教材不一样。
《文镜秘府论》中引用了很多唐人的著作,很多章节有可能是直录唐人原文。那么,空海引用谁的著作比较多呢?
虽然在《妖猫传》中空海和白居易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虽然白居易在中晚唐诗坛地位显赫,被封为“广大教化主”,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汉诗界,成为日本汉诗界的偶像;虽然世间流传着署名白居易的《金针诗格》。但是,在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中,完全看不到白居易的影子。事实上,空海是否见过白居易,也没有任何实在的证据。毕竟,空海来中土的时候,白居易还只是个中进士才四年的小小校书郎,远不是什么文坛领袖。空海并不像之后的日本汉诗家那样,将白居易奉为诗学圭臬,他的诗学主要受到大历以上的唐人影响。
那么,空海追思的盛唐诗学家又是谁呢?真的是吟咏着《清平调》的李白吗?在《文镜秘府论》中,同样找不到李白的身影,看来李白也并不是空海的偶像。《文镜秘府论》引用最多的是王昌龄,其他比较显眼的,还有皎然和崔融。
崔融是武则天时代的人,比盛唐略早,出身于山东士族,山东的崔氏自汉末至北朝多有名臣,在唐代,崔氏仍是最耀眼的姓氏之一,山东崔氏的各支系贡献了不少文学家。崔融本人曾“擢八科高第”,是当时的“大手笔”。中晚唐以后,崔融似乎淡出了诗学家的视野,但在盛唐,他还是颇有影响力的。《文镜秘府论》保存了他的诗论。
王昌龄是我们熟悉的盛唐诗人,大约与李白同辈。王昌龄出身于琅琊王氏或太原王氏,在中古时代也是高门著姓。《文镜秘府论》中大量引用了王昌龄的诗论。应该说,王昌龄才是空海所仰望的盛唐。这或许与我们今天对盛唐的印象有些出入。
诗僧皎然俗姓谢,自称为谢灵运的后人,陈郡谢氏在六朝也是显赫的文学家族。皎然生活在大历时代,比盛唐稍晚。
这三位较有代表性的诗人,都生活在盛唐前后,都与南北朝的显赫家族有关,创作风格都偏于保守、温润。这可能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唐人实际的审美倾向。或许,在白居易之前,这样的人是最有资格教人写诗的人,他们自然也成为了空海学习的对象。
那么,空海跟这些人学到了什么,《文镜秘府论》又讲了些什么呢?
《文镜秘府论》分为天、地、东、西、南、北六个板块,说的都是初学者最容易遇到的问题。
《天卷》讨论格律问题。每个初学者首先都必须过格律关。格律就像天一样,是一切存在的前提,也是不能越出的。实际上,《天卷》讨论的格律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初学者的需求。初学者学格律,只要记住林黛玉说的“平的对仄的”,就够用了。《天卷》作为教师用书,提供了很多进阶的格律知识,在初学者看来,难免会头晕目眩。其实,《天卷》讲的“声病”,并不是必须规避的。如果你是对诗作声吻协合有特殊要求的进阶选手,那么还是应该了解一下《天卷》中讲的“八病”。另外,《天卷》还记载了一些特殊的格式,包括“齐梁调诗”,也是可以供进阶选手学来玩的。
《地卷》讨论诗的“体势”,可以理解为品格问题。诗有不同的风格流派,不同的审美追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体”,这些“体”的品位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品位,就好像地势的高下一样。任何体势都可以写出好诗,就像任何地势都能长出好看的花一样。但是论起地势本身,毕竟是有高有低,有一圈一圈的等高线,同样道理,诗的体势也毕竟有高下之分。在“以诗取士”的语境下,除了诗本身是好诗,诗的体势高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需要评诗的人火眼金睛,认得更高的品位,不能“见了浅近的就爱”。在这方面,《地卷》可以提供不少帮助。但是初学者要是把《地卷》当成武林秘籍,照着一招一招练过去,那是不可行的。在缺乏创作经验的时候,只是背会这里的招式名称,那更是毫无意义。所以《地卷》也是评诗者用着比学诗者顺手。当然,对学诗者来说,知道天下之大,诗有更高的境界,也是好事。
《地卷》中最实用的,当属王昌龄的《十七势》、皎然的《十四例》和崔融的《十体》。其中,王氏的写法又与谢、崔二氏略有不同。皎然和崔融写的,相当于“评分标准”,罗列诗的不同境界,其间是有差等的,我们在评诗的时候,基本可以按照他们的总结,按图索骥,评定诗的高下。王昌龄说的“势”,类似于宋人黄庭坚讲的“诗法”,这里的“法”是“活法”,不是“法律”的法,而是“办法”的法。不是规定你只能怎样写,不能怎样写,而是给你提供更多的写作思路。这些写作思路之间,不是完全没有高下,但高下是不明显的。我们写诗打不开思路的时候,可以去看《十七势》,然后就知道,写诗不是只能一板一眼地写八股,是可以有无数种章法变化的。《十七势》是招式,可以临时借鉴了用,而《十四例》《十体》基本无法当场借鉴,只能供你对照功夫练到哪一层了。
在天地之间,会有形形色色的生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东、西、南、北四卷,就是讲初学者遇到的问题的。
《东卷》讲的是对仗问题。东方是万物发生之地,东卷就讲初学者最先遇到的问题。在解决了格律问题之后,初学者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对仗。对很多人来说,要写出工整的对仗,并不是容易的事。
当下有很多人工智能软件都可以写旧体诗,如果只写散行绝句,它们的水平已经与人类初学者难分伯仲,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软件能很好地解决对仗问题。我们习以为常的“对对子”,对人工智能来说竟是难以突破的瓶颈,由此可见,对仗艺术凝聚了人类智慧的精华。在格律的壁垒被突破以后,要证明我们人类相对于电脑的优越性,对仗还是一道可以踞守的天险。
今天的初学者,经常觉得写出工稳的对仗句有困难。很多人选择了退缩,或者写个宽对敷衍了事,或者干脆只写散行绝句,只填词,有的还能填出很漂亮的词。其实,这样很不好,等于是自动放弃了人类的优势地位,把自己降格为电脑。毕竟现在电脑写出像样的词也不难了。
中古时代,在寒素阶层上升的过程中,很多寒素子弟努力学习写诗。世家子弟看他们的心情,就跟我们今天看人工智能的心情是一样的,不屑中带着担心。他们也必须拼命证明,自己比这些“后出门户”更优越。因此,在当时的诗学中,也会存在一道一道的防线。格律是第一道,品位是最后一道,而在格律之后的第二道防线,大概也是对仗。
对于自幼熟读《文选》的世家子弟来说,对仗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只想走捷径学会写诗,在文坛上暴得声名,那么对仗可能会成为他的一个弱点。评诗的大佬看见逃避对仗或者写不好对仗的人,心里应该也是有数的。所以,在乾坤定位之后,《文镜秘府论》首先要教人对对子。
但是,《文镜秘府论》的《东卷》也不适合拿来学习对仗。《东卷》讲各种对仗的方法,例如《二十九种对》,也像王昌龄的《十七势》一样,讲的是办法。是告诉你,除了规规矩矩地对仗,还有这么多出奇制胜的法子,是帮你开拓思路的。《二十九种对》不但不是必要的,也不能穷尽对仗的方法。初学者看这个,首先会晕,以为对仗有多么复杂,徒然产生畏难心理。不晕了之后,如果再把这些奉为秘籍,一一记住,一一运用,不过是浪费时间,并不会因此把诗写好。更有甚者,以为用了这些对法就是好诗,不用就不是好诗,一心钻研对仗的法门,以期拿来炫耀,未尝不是另一种急功近利。晚唐七律出现了很多精致繁复的对仗,恐怕与寒士急于靠写诗博取功名的心态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写诗不是对仗的花样越多越好的。能写对仗,能证明你是个有灵魂的人类,就足够了。要写好对仗,靠的不是背招式,而是要好好把《文选》读熟。
《西卷》讲的是“诗病”,就是诗会出的毛病。人活在世界上时间长了,没有不生病的,写诗上手了以后,也会慢慢地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西方总是和衰老、刑狱联系在一起,所以《西卷》用来讲诗病。
“诗病”就更不是供初学者学习的东西,初学者没必要把《西卷》中空海归纳的二十八种诗病都记住,一一都犯一遍。诗病是供评诗者掌握的。评诗者要知道,这样的写法是毛病,不是创意。如果学生这样写了,要纠正;如果考生这样写了,严重的要黜落。当然,作诗的时候,如果能知道诗病,有意加以规避,那也是好事。
识别“诗病”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读诗还是作诗,都要识别好歹。要知道,这么写是好的、那么写是不好的,这个字用得好、那个字用得不稳。而不能只会看中心思想,说了我好话的就是好诗,说得不入耳就是坏诗。识别“诗病”是一门很实在的学问,有几千年的积淀,能把中国诗讲成云山雾罩空中楼阁的,多半是不懂这门学问的。
考究诗病,充分说明当时存在着品评诗作高下的需求,从侧面说明了诗歌的繁荣,也说明诗作的高下关系着士人的荣辱。
《南卷》讨论的是诗的“意”与“位”。南方使人联想到光明正大,《南卷》讨论的就是诗歌中最为核心、最为光明正大的问题,是诗歌的高贵属性。
《南卷》中的《论文意》,引用王昌龄和皎然的诗论,讨论“意”的问题。为什么诗要讲“意”呢?是不是说,一首诗只要意思好,艺术上不用讲究呢?不,一个能讨论“诗病”的诗学系统,不会这样粗糙。
想靠诗歌干谒的人,如果再多下些功夫,是可以学会对仗,甚至避免诗病的。这时候,横在他们面前最后也是最严峻的考验,就是能否写出一首意脉连贯的诗。真正的诗人,写诗就是为了抒写自己的性情,如果不是心有所感,就不会写诗,那么他下笔的时候,不用怎么布置,意脉自然是连贯的。但如果写诗是为了博取声名,是功利性的,那么就会出现为写而写的情况。此时除非以很高的技巧加以经营,否则无法写出连贯的意脉。这样的诗,也许单看句子会很精致,但通篇看下来,却没有太深的思致,或者稍微思考得用心了些,意脉却断裂了,不知所云。有这样的迹象,就说明是功利性的写作,同时技巧也不够,所以绝非上品。还有一些初学者,写诗倒是有感而发,但对于如何把自己的感受完整地写下来,还缺乏经验,在写完最先想到的句子之后,就没有其他感受可以写了,于是只好开始拼凑,上句写了春天,下句却凑出来秋天。这样的诗,当然也是不好的,禁不住“意”的考量。
《论文意》主张,写诗要“苦思”“造意”,“险起杰作”,要追求新奇,其实是在要求诗人努力写诗,不可以写平熟套话,对艺术的要求是很高的。这里所说的“意”,是指新意,并非限于主题正确,而是包括了见识和技巧等不同方面的精进。强调“意”,其实是强调诗人的主体意识,以飞扬独特的个性为尊,以可复制的功利性创作为卑。这是盛唐诗人最可贵的精神,也是在诗人阶层不断扩大的时代保持诗歌高贵本性的需要。
《论文意》也是服务于评诗者的。评诗者需要知道有意之诗高于无意之诗,写诗者却无法通过阅读《论文意》而完成从无意到有意的飞跃。可以想见,如果有一天电脑可以解决对仗和诗病的问题,“文意”仍然会是它与人类高手之间的屏障。当然,人类的子孙,如果才华平平却急功近利,也是会被挡在这道屏障之外的。
同属《南卷》的《论体》,讨论诗之“位”,即不同诗体的功能。要恰当地使用不同诗体完成不同的功能,首先至少要掌握所有的诗体。只会写绝句的人,是没有“论体”的可能和必要的。因此,讨论形式与功能的关系,也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北卷》的内容较杂,有关于对仗的补充论述,也有虚词用法的介绍,或许是空海在记录不能归入其他五卷的零碎感想。
《文镜秘府论》是空海向盛唐诗人学习的成果。它以格律为始,以体势为归,靠对仗、诗病、文意、诗体的品鉴保驾护航,帮助评诗人学会识别诗作的高下,也给作诗人以必要的提醒,从而维护诗的品质。《文镜秘府论》保存了盛唐通行诗学文化的样貌,证明着盛唐诗学的繁盛与辉煌,也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与创作提供着启迪。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