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谈虎三则》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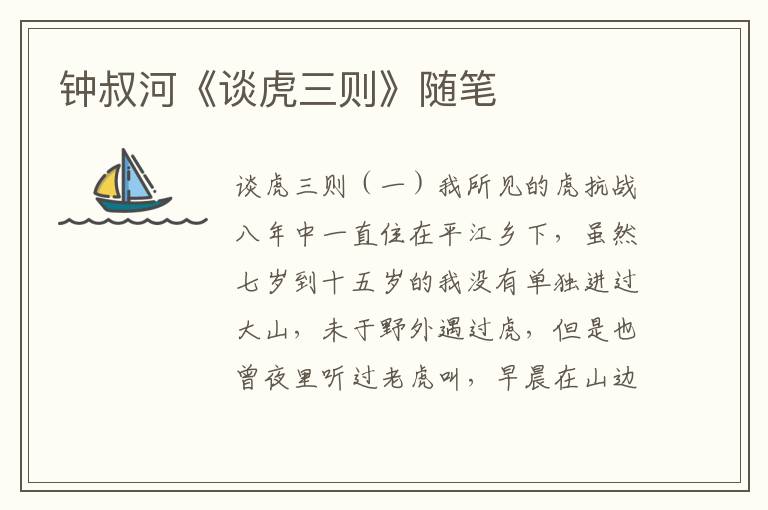
谈虎三则
(一)我所见的虎
抗战八年中一直住在平江乡下,虽然七岁到十五岁的我没有单独进过大山,未于野外遇过虎,但是也曾夜里听过老虎叫,早晨在山边湿地上看过老虎脚印。可见其时虎在湘北一带并不稀罕,更未“濒危”。
一九四一年冬,我在蟠龙山张巡庙小学读书,见几个从大山上下来的猎人,带着刚办好的虎皮虎骨往县城里去卖,在庙前歇息。有同学向他们买虎爪虎牙,一枚亦不过碗把羊肉面的价钱。猎人们还拿出虎鞭给我们看,这家伙干后只手指粗,长却在两尺以上,前端尖而带刺。此系初见,因为形状奇特,故印象很深,猎户们却并不显得特别珍重。
一九四三年在长寿街,见药店前木笼关着一虎,已受重伤,仍虎虎有生气,两眼放射着愤怒的光。据说第二天就要宰杀,虎肉论斤卖,骨架便熬虎胶,浸虎骨酒。这虎是药店的活广告,围观的人很多。我这时已进初中,正读《报任少卿书》,“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读来声调铿锵,颇有趣味,于是也挤拢去看了很久,却不见它摇尾而求食……现在想,这文章恐怕是太史公的想象之辞,常言虎死不倒威,偶然中了人的诡计,入了牢笼,怎么便会立刻变成一只狗?当然这是说野生的也就是自由的虎,若是经过长期培养教育,奴性代替了要自由的本性,则不要说摇尾求食,就是跟着群犬吠影吠声,登台表演,亦不足怪矣。
抗战胜利后,到长沙读高中,和山林疏远了。每年虽有几次在报纸上见到宰杀活虎的广告,但对动物的兴趣已经转移到读《斑麋》和《白牙》上面去,也就懒得到国药局门前去看热闹。
后来参加工作进了报社,一九五六年以前编发农村稿件,不时还有民兵打虎的报道。韶山冲农民从虎口抢救女孩的新闻,见报时还加上了花边。五七年自己成了“老虎”,被逐出机关,栖流于城市底层,从此对广阔天地发生的变化了不知情,复出后才听说虎已在湖南绝迹。动物园铁笼中关着的也都毫无生气,传种接代亦须万物之灵来采精授精,此则只能视作披着一张老虎皮的畜生,不复是我心目中的虎了。
近读湘绮楼和养知书屋日记,都有长沙南门外白昼见虎的记载,去今不过百数十年。盖人虎共存于天地之间,虎偶伤人,人或捕虎,自人之初虎之初起从来如此,并不妨害各自种群的生生不息。直到百十年前,不,直到四五十年前还是这样,此乃我亲见亲闻的事实。如是,则虎之濒危当别有其原因,只能请自然学者(也许是社会学者)阐明,非我所得而知,我所见的虎也只能当故事讲讲而已。
(二)老虎在长沙
长沙人过去对龙和虎是十分敬畏的。在河西岳麓山下湖南师范大学的生物馆里,有一只华南虎的标本,是五十年代初从山上下来,被打死后剥制的,这是长沙地方原来有老虎的物证。可见长沙人确实见过虎,知道虎的可怕,非如对龙的无知。当然真龙天子也是真实的存在,同活老虎一样,绝对不能触犯。
故长沙人过去忌说龙虎,连“龙”和“虎”的谐音都不敢出口。到茶馆里吃包子,也不叫“来一笼”,只叫“来一缴”。霉豆腐不叫“腐乳”,而叫“猫乳”。文夕大火前家住长沙红墙巷,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听大人交钱给佣人令往府正街为哥哥姐姐买文具,并不叫“府正街”而叫“猫正街”,也不知老长沙还有和我同样印象的人没有?
“腐”“府”亦须避讳,只缘与“虎”谐音,可见长沙人对老虎的敬畏了。
近阅上海报纸,说那里到医院治不育的夫妇,自从去年起,多数都要“停一停”,因为不想在虎年生个“虎子”或“虎妞”。难道十里洋场的同胞,也有老长沙的禁忌,并且一直保留到了世纪末么?
老虎本来不是什么好接近的东西。孔夫子把“虎兕出于柙”(让老虎和野牛从关它的木笼中跑出来)看作是严重的责任事故,是不得了的事情。周处所在的晋朝,人们也把虎、蛟和鱼肉乡里的恶人称之为“三害”,《除三害》这出戏至今还在演出,是架子花脸的应工。
长沙人过去还常常在幼儿的帽子和鞋头上做出个“老虎头”,差不多成了习惯,此事的动机我想不会是因为喜欢老虎想招致,而是为了厌胜,也就是借鬼打鬼,以毒攻毒,正好比在门楣上钉一个獠牙吐舌的“吞口”——木头雕刻成的狰狞鬼脸。
在藩正街旧藩台衙门的门口,有一对大石狮,国民党在衙门里办市参议会的时候,把它搬到中山东路街心花园中了。狮子在中国古时不是常见的动物,老百姓根本不熟悉,正因为如此,所以可以把它想象并制造成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大门口可以摆,正月十五还可以放肆玩它个痛快。若是换上有可能会真正碰上的老虎,便决不敢如此对待。
“三反五反”时,长沙卷烟厂出过一种“打虎牌”香烟,盒皮上印着打虎英雄武松的形象。其实《水浒传》中明明写着:“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可见即使是打虎英雄,也宁愿避开老虎,不会很想去拿那一千贯赏钱的。
当然,景阳冈上早就没有虎了。如今的虎都是动物园繁殖出来,用狗妈的奶喂大,又经过“万物之灵”的长期训练,已经变得呆头呆脑,据说见到扑翅伸嘴的鹅都会回头就跑。它们早已丧失了傲啸山林的本性,安居铁笼,并不想“出于柙”去追求自由了。但从观众总是警告小孩不要和它太接近这点看,人们对它的“畏”还是有的;至于说到“敬”字,心里恐怕早就没有,那么忌讳也就不必那么讲究了吧。
(三)十二生肖中的虎
“子鼠丑牛寅属虎”,即将到来的戊寅年是虎年,报纸刊物都来叫写文章。其实关于老虎我已经写过两回了,这次只能从十二生肖中的虎来谈一谈。
十二生肖除了龙和虎,都是人们熟悉的动物。龙活在想象中,暂且不必说它。虎虽存在于世上,但古时没有动物园,普通人难得见到。除去接了官府杖限文书的解珍解宝(还得拿上浑铁点钢叉),恐怕谁都不情愿遇上它,连武松也不例外。
洋文将虎叫作tiger,凶残的人也叫tiger.古文称虎曰山君,曰百兽之王,都有尊之为君王的意思。而老百姓对君王从来畏多于敬,爱则是根本谈不到的。古时又称凶恶而有权势的人为“虎而冠者”,此冠即使并非王冠,至少也是一顶大盖帽,无论如何总不会是二大爷头上的“老头儿乐”。故虎之列入十二生肖,并非出于人们对它的喜爱,而是出于对它的畏惧,和敬火神瘟神一样。
如今传统文化吃香,学者言必称先儒,故不妨看看孔夫子是怎样谈虎的。他有次问冉有:“虎兕出于柙……是谁之过与?”(老虎和野牛捉来只能关在笼子里,让它们跑出来伤了人,就必须追查是谁的责任。)又有次说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凭一时血性去同老虎搏斗,不测量深浅就冒险淌水过河,你说他是胆大不怕死,我却不会赞许。)这些虎恐怕都只有负面的意义。还有次过泰山侧,见妇人哭其父其夫其子都死于虎,犹不肯去其乡,说是因为此乡无苛政,孔子于是有“苛政猛于虎”的感叹。我想孔子决不会认为虎不够猛,只是说两只脚的虎比四只脚的更加可怕。
人死于虎者从来就有,但虎并未将人吃光。郭璞注《尔雅》云:“律:捕虎一,购钱三千。”这赏格到武松时涨了三百多倍。然而,据十二月五日《新民晚报》引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报告,二十一世纪初全世界尚有野生虎十万只。可见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人亦并未将虎捕杀完。须知相生相克、相反相成本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正道,达尔文研究田鼠和胡蜂,得到的结论亦是如此。古人固畏虎,仍不能不接受虎亦万物之一的事实,将虎列入十二生肖便是明证。
不幸的是,今人在力图自我发展的同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和遵循大自然的法则。苏联喜欢喊“人类征服自然”,一心要斗地战天,用中国古话说就是“以万物为刍狗”,大规模“消灭沼泽地”,还要“向荒地进军”。虎本“栖息于林间杂草丛生泥土湿润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进军”却完全破坏了它们的栖息地,于是近几十年虎的数量锐减。现代人没有冯妇的勇气,却凭着直升飞机、麻醉枪,将虎捉进“野生动物园”,用冰冻牛肉来喂,用人工采精授精来繁殖,用“狗妈妈”来哺乳……这样养出来的虎不仅怕人,还怕牛、怕鹅、怕狗、怕老鼠。人也没能捞到什么实惠(外国老板已经不买虎皮虎骨了),反要一天到晚去求拨款拉赞助来养虎,真是既害虎又害人,何苦呢!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