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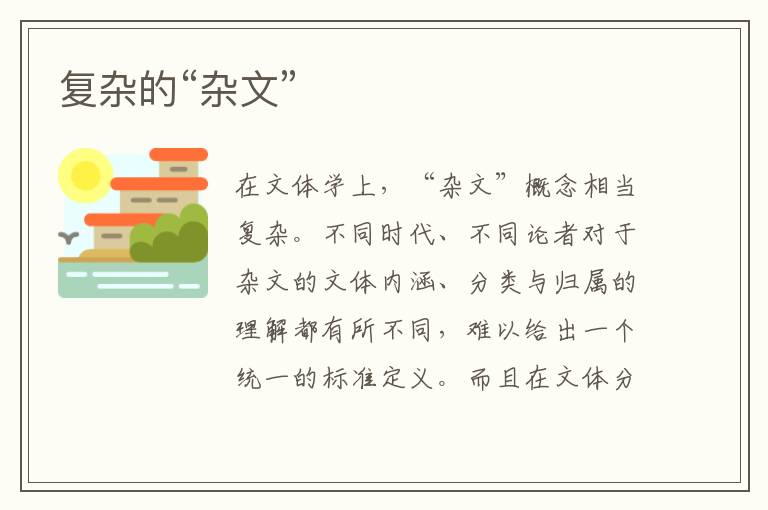
在文体学上,“杂文”概念相当复杂。不同时代、不同论者对于杂文的文体内涵、分类与归属的理解都有所不同,难以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定义。而且在文体分类学上,对主流文体与非主流文体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往往漂移不定。这些因素都促使“杂文”成为古代文体分类学中最为复杂多变的文体之一。
魏晋以至唐代,“杂文”一词曾用来泛指各种文章者,其含义与“文章”没有太大的差异。这种情况不太为人所注意。古代的“文”本身就有文采相杂的意思。《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韩康伯注:“刚柔交错,玄黄错杂。”《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另一方面,“杂”,也指各种色彩的相互配搭。《说文》云:“杂,五采相合也。”任何事情,都是由不同要素组合(杂)而成的。明谢肇淛《〈五杂俎〉序》:“五行杂而成时,五色杂而成章,五声杂而成乐,五味杂而成食。”从这个意义来看,“杂文”便可用以指代有文采之文章。“杂文”之义与文章、辞章意义相近。从魏晋南北朝的文献看,“杂文”这个概念的运用已相当普遍了。如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余所著外篇及杂文二百余卷,足以寄意于后代,不复须此。”这里仅提所著杂文而不及其他文体,此杂文或有泛指各体文章之义。《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梁武帝杂文集》九卷、《梁代杂文》三卷,未详其义,但很可能就是指各体文章。更重要而且可靠的例子是,唐初欧阳询等人所编纂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中的“杂文”分类。该书从卷五十五至五十八为杂文部,收录:经典、谈讲、读书、史传、集序、诗、赋、七、连珠、书、檄、移、纸、笔、砚等内容,可见《艺文类聚》的“杂文”主要是指含诗赋在内的各体文章,或者更简要地说,杂文即文章。这应该是继承了南朝以来的文体分类学的某些传统。当然,《艺文类聚》“杂文部”中如经典、谈讲、书、笔、砚等内容不能等于文章文体,但也与各体文章写作有密切关联。更准确地说,《艺文类聚》“杂文部”是以文章文体为中心,又包括了与之相关的言辞与书籍、书写。到了唐代,这种杂文即文章的内涵仍被官方所沿用。唐代的科举主要分为三部分:明经、进士与制科。进士科考试设有“杂文”项目,是对试策的补充,主要是考查考生的文章才华。它所包括的文体是诗、赋,或者颂、论。《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宋王谠《唐语林·补遗四》:“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条记载:“唐进士初止试策。调露中,始试帖经,经通,试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杂文又通,试策。凡三场。其后,先试杂文,次试论,试策,试帖经为四场。第一场杂文放者,始得试二、三、四场。”此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这种观念,是从魏晋南北朝一直沿袭下来的,而且得到官方的认同和使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中,“杂文”另一个意义是指在正规和主流文体之外难以明确归类的丛杂文体。这也是此后古代文体学上的常用意义。“杂”字之义指“丛杂”。这种杂文分类就像每个家庭总有一些杂碎的小物件,虽然不贵重,但各有用途,不能丢弃,所以用杂物柜把这些小物件收纳其中,以备不时之需。“杂文”作为文体名称,《后汉书》已多有记载。《后汉书·文苑传》谈到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苏顺有“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王逸也有“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等等。但是,杂文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字,《后汉书》没有明确记载。《后汉书》所谓的“杂文”,与诗、赋、论、赞、诔、吊等文体相提并论,从其语境中推测,可能是指主流文体之外难以明确归类的丛杂之体。当然,《后汉书》虽然记载东汉历史,但成于南朝宋代。我们难以确定其中“杂文”概念,是范晔根据东汉遗留文献而记载的,还是出于他本人的总结。
刘勰最早从文体学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杂文文体的渊源流变及文体特点。《文心雕龙》有“杂文篇”。范文澜注曰:“论文叙笔,谓自《明诗》至《哀吊》皆论有韵之文,《杂文》《谐》二篇,或韵或不韵,故置于中;《史传》以下,则论无韵之笔。”在“文笔”系统中,“杂文”或用韵或不用韵,但大体仍属于“有韵之文”。《杂文》篇一开始说:“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他举宋玉“对问”、枚乘“七”体以及扬雄“连珠”三体为例,既高度评价他们的才华气势以及文采,又认为“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枝派”是在主流文体之外的分支流派。“末造”是指不重要之文章制作。他认为这三种文体是文人闲暇之时的即兴之作,因事造文,因文生义,属于文章的细枝末叶。刘勰对于杂文的看法比较复杂,一方面,认为它可以表现文人的“智术”“博雅”和文学才能及文字技巧,也给文坛带来新异的风采与情趣;另一方面,又认为杂文文体处于非主流地位。刘勰的“杂文”内涵颇广,对问、七体、连珠三体之外,还包含众多文体:“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他将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等,这些难以纳入其它文体系统的小文体统统归入杂文类。所以,刘勰所谓的“杂文”,主要是指丛杂的韵文文体类别。后世一些学者沿袭刘勰的“杂文”观念,如明代何三畏《新刻何氏类镕》、清代孙梅《四六丛话》、刘师培《论文杂记》都列有“杂文”体,其分体思想大致皆采用刘勰“杂文”观念,以对问、七、连珠为杂文之主流。不过,他们所涉及的杂文文体种类越来越多,如上梁文、乐语、致语、口号、青词、步虚词、上寿词等等,这些后世兴盛的小文体,都被列入杂文之属。
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把“对问”作为“杂文”的主要文体之一,并溯源于宋玉:“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宋玉有《对楚王问》,此后,东方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崔寔《客讥》等,推而广之,在文学史上形成一个有独特风味的作品系列。刘勰以宋玉《对楚王问》为最早的对问文体之代表作,大概因为其篇名有“问”字。其实,在《楚辞》里已有类似对问形式的作品,如《卜居》中屈原与詹尹之间的对话,《渔父》中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可见此体来源之久远。吴讷说:“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将对问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真实记录彼此之间的问答之辞,一类是有意设计的、虚拟的客主答问。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总结对问文体说:“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对问,或称问对,或称设论,其文体特色首先是:辩论的中心往往围绕作者怀才不遇,志高位低,抱负不得实现等个人问题;作者通过反复问答辩难的形式,自譬自解以抒发自己的愤懑与不满,以达到自我排遣的目的。故吴讷说:“至若《答客难》、《解嘲》、《宾戏》等作,则皆设辞以自慰者焉。”徐师曾说问对之体:“反复纵横,真可以舒憤郁而通意虑,盖文之不可阙者也。”(《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其次,设辞问对的特色还在于虚拟性。徐师曾说:“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词也。”问方往往是代表世俗立场和观点的化身,作者通过驳斥对方来表达自己超越时俗的尊贵与崇高。这些问题大多是虚拟的假设之辞。例如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甚至直接将主人公命名为“非有”。对问文体的这种虚拟性,应该是受到辞赋类的影响,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皆为虚拟之人物。对问文体的风格往往铺张,也有辞赋的影子。所以,也有人把对问一类的作品列入辞赋之中。
七体也是杂文的主要文体之一。七体是沿袭西汉辞赋家枚乘《七发》而成的一种文体。《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与太子展开问答。吴客认为,“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他用七种办法启发太子,前六种是音乐之美、饮食之丰、马车之盛、宫苑之宏深、田猎之壮阔、观涛之娱目,但太子都说,“仆病未能也”。最后吴客向太子推荐方术之士,“论天下之释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霍然而愈。《七发》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连续铺张描写七件事,这种结构方式,为后世所沿习,并形成赋中的“七体”。七体,具有兼体的性质。它既是“杂文”,又具有辞赋的特点。就形式而言,七体本可归于“问对”一体。正如《文体明辨》所说:“七者,问对之别名。”但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中,它却是在问对之外独立一体的。这主要是因为《七发》之后,仿作很多,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特色鲜明的系列作品。
连珠,是一种假喻说理的骈俪文。连珠具有多重文体属性,所以也产生其文体归属的分歧。刘勰《文心雕龙》、章太炎《国故论衡》等将连珠归于“杂文”类,而吴曾祺则将连珠体归入“辞赋类”。以之为辞赋,是着眼于文体的共性;以之为杂文,是着眼于文体的特性。可谓见仁见智。连珠同样具有兼体的性质。它既是“杂文”,又具有辞赋的特征,同时,它也是论体之文。连珠是一种讲究逻辑推论,以此来阐发事理的文体。连珠体不直接陈说道理或事实,而是借用比喻和故实来表达,即“假喻以达其旨”,合乎古诗讽兴之意。在形式上,连珠篇秩短小,讲究对仗声韵之美,辞丽言约,沈约曰:“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换言之,纷沓而来的精彩比喻好似一颗颗散落的明珠,用优美的语言把这些明珠贯穿起来,互相发明,阐发事理,因之称为“连珠”。连珠是韵文,其基本句式是“臣闻(盖闻)……是以”,此句式体现出前后文辞的因果关系。如吴均《连珠》:“盖闻艳丽居身,而以娥眉入妒;贞华照物,而以绝等见猜。是以班姬辞宠,非无妖冶之色;阳子寂寞,岂乏炫曜之才。”(《艺文类聚》卷五十七)西晋傅玄《连珠序》论连珠的文体特点:“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连珠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对骈体文的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后世学子练习骈文创作的手段之一。
《文心雕龙》“杂文”反映的是以诗赋骈文为主体的文体观念。到了唐宋时期,古文之学兴盛,古文家创作了一些新的文体,“杂文”的概念也逐渐出现变化。北宋初期重要的文章总集《文苑英华》“杂文”二十九卷,又分为问答、骚、帝道、明道、杂说、辩论、赠送、箴戒、讽刺、纪述、讽谕、论事、杂制作、征伐、识行、纪事等10多类。包括了韵文和散体文,收录文章近三百篇,其中不少文体是唐以来古文家的新创。这种杂文的概念,既承六朝而来,又有相当大的扩大和变化。
从宋代开始,“杂文”又有“杂著”之名。吕祖谦《宋文鉴》卷125至127收录“杂著”。“杂著”即“杂文”,但与《文心雕龙·杂文》的含义相去甚远。《文心雕龙·杂文》主要是指对问、七、连珠等几种文体,而《宋文鉴》在“杂著”类中则不收这几种文体的作品。所收的刘敞《责和氏璧》,王回《告友》、《记客言》,王令《道旁父老言》,刘恕《自讼》等文,都是随笔性的散体短篇,或偶感,或讽谕,或戏谑,或即录见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文章从标题上,难以明确归入某类文体。这些“杂著”,大概是文学性较强的散体短篇作品。
明代吴讷《文章辨体》与徐师曾《文体明辨》继承刘勰的杂文分类法与相关理论,又有较大发展和差异。二书都收录“杂著”体作品,并对此文体进行了界说。吴讷说:“杂著者何?辑诸儒先所著之杂文也。文而谓之杂者何?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裒集,其所录弗尽者,则总归之杂著也。”徐师曾云:“杂著者,词人所著之杂文也;以其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故谓之杂著。”这是从文体分类學的角度来看杂文的,即难以归入主要文体的丛杂之文,即为杂文。后来张传斌《文辞释例》中更为明确地说:“杂文者,无类可归之文也……故凡随事命名、不落体格者,概谓之杂文。”(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下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从二人所选的“杂著”篇目来看,吴讷《文章辨体》选有唐代陈黯的《诘凤》、李翱的《拜禹言》、柳宗元的《鞭贾》等文,徐师曾《文体明辨》选有韩非子的《说难》、崔骃的《达旨》、司空图的《疑经》。根据古人确立文体名称的习惯,“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颂赞第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文章,无论从其篇名,还是从其内容和形式,确实很难归为某一个传统文体,故而在文章总集的文体分类中,只能作为杂著处理。这就是典型的“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正如吴讷说的:“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裒集;其所录弗尽者,则总归之杂著也。”从文体功用而言,这些文章皆是评古议今、讲论政教、阐发道理的论说文,文“杂”而理正,是“本乎义理,发乎性情”之作。吴讷、徐师曾二人的杂著观念相同,认为杂著的特点在功能上“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独到之见解,多为议论之辞;在形式上“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没有严格的体制要求,难以归入传统主流文体之中,而谓之“杂”。这些文体在文集之中,难以归类,即归入杂著之中。在这种杂文观念下,吴、徐二人将对问、七、连珠独立于“杂著”之外,与“杂著”相提并论。同时,徐师曾也注意到上梁文、致语、青词等文体的独特性,使此类文体取得了独立的文体资格,载之于附录内。这种观念与刘勰有明显的差异。如果说,刘勰代表了骈文时代的杂文观念,那么,吴、徐则代表了古文兴起并占主流地位之后的杂文观念。这种观念比刘勰的杂文观念对于后世乃至现代的影响要更大、更显著。此外,《元文类》《明文衡》《金文最》等文章总集,均设“杂著”类,收入“随事命名,不落体格”的作品。清代李兆洛的杂文观念与吴、徐二人相近,其《骈体文钞》在“缘情托兴之作”中列有“设辞类”(即对问体)、“七类”、“连珠类”、“笺牍类”和“杂文类”,杂文的范畴较为纯粹。但其“杂文”选录的文章却与吴、徐二人大异其趣,有王褒的《僮约》、《责髯奴文》、戴良《失父零丁》、袁淑的《鸡九锡文并劝进》、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等,多为游戏调笑之作。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杂文具有崇高的地位。它以短小形态和锋利的笔调,对于传统与现实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是“匕首和投枪”(《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杂文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总体上与传统“杂文”有本质区别。但鲁迅受传统文化熏陶既久且深,他受古代杂文传统的影响并对之有所吸收是不言而喻的。鲁迅杂文与中国古代杂文形式上短小精悍,功能上“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这种批判、讽刺与幽默的艺术传统是有血脉相承关系的。由于鲁迅创作的伟大成就,遂使“杂文”这一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上,由边缘成为主流,散兵变成主力,这可谓是文体史上的奇迹。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