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燕喜亭记》原文,注释,译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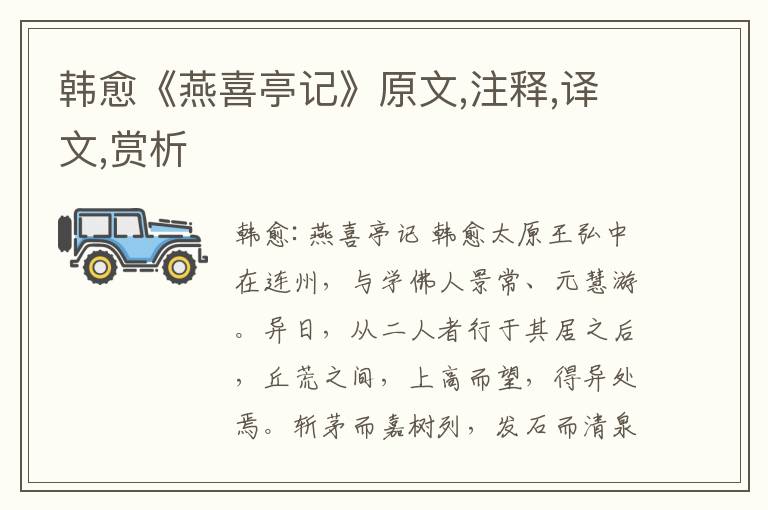
韩愈:燕喜亭记
韩愈
太原王弘中在连州,与学佛人景常、元慧游。异日,从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后,丘荒之间,上高而望,得异处焉。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燔椔翳;却立而视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为池而缺者为洞,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自是弘中与二人者晨往而夕忘归焉,乃立屋以避风雨寒暑。
既成,愈请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于古而显于今,有俟之道也。其石谷曰:“谦受之谷”,瀑曰“振鹭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日“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时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恶也。泉之源曰“天泽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诗》所谓“鲁侯燕喜”者颂也。
于是州民之老,闻而相与观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无与“燕喜”者比。经营于其侧者,相接也,而莫值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遗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贬秩而来,次其道途所经:自蓝田人商洛,涉淅湍,临汉水,升岘首,以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由郴逾岭。猿狖所家,鱼龙所宫,极幽遐瑰诡之观,宜其于山水饫闻而厌见也。今其意乃若不足。传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遂刻石以记。
这篇亭记约作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其时,韩愈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王仲舒(字弘中)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司户参军。由于两人遭遇相同,心境相似,所以在王仲舒建亭之后,韩愈为它命名,并写下这篇亭记。从内容来看,有三个特点。
第一,叙说燕喜亭自然环境的发现。王仲舒和僧人景常、元慧在“丘荒之间”,登高而望,才发现亭址“异处”。但是,作者在写法上,引而不发,故意蓄势,不直接写“异处”之所以“异”,而是写斩茅、发石,“辇粪壤,燔椔翳”,经过辛苦经营,被湮没已久的奇景显现出本来面貌;“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为池而缺者为洞”。在写法上,有三点值得重视。首先在叙述开发经营和自然美景之间,加“却立而视之”连接,实为传神之笔。经营之时,不及审视,经营之后,才“立而视之”,这不仅符合生活实际,而且别具情味,人们常常对自身的劳动成果有特殊的感情。其次,在“出者突然成丘”等三句之后,缀以“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强化了丘、谷、池、洞的神奇性。再次,行文中句式多变化,“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燔椔翳”和“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为池而缺者为洞”两组句,本来都可组成句式相同的排比句,但作者追求整齐中的变化、变化中的整齐,在两句整齐的句式之后,就改变句式,但改变后的句式,又和前边的句式相配衬。
第二,移情于物,在景物的命名上寄托自己的情思。所谓“有俟之道”就是“蔽于古而显于今”,故而为亭址所在的小丘取名为“俟德之丘”,用以说明小丘之美有待于发现,而被埋没的人材只要注重道德修养,也必定会显豁于未来的。文中对谷、瀑、洞、池的描述,冠以“谦受”、“秩秩”、“寒居”、“君子”等词,目的也在于借物言志,以显示人格价值和道德素养。它既是在赞扬王仲舒的高尚品格,也是自我心迹的显示。在封建社会网络的结构中,韩愈有其特殊的位置,他具有进步思想,敢于直谏,但始终念念不忘“天泽”和“出高而施下”的信条;他既要坚持廉洁政治,却又无力改变腐朽的政治,这就必然地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但是他身处逆境,而志节不衰,这又是难能可贵的。当王仲舒建亭之日,他为新亭命名,依然不忘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忘对王仲舒高尚品格的肯定,祝愿他象鲁僖公那样内外欢洽,多福长寿,因而根据《诗经·鲁颂·闷宮》“鲁侯燕喜”,为新亭取名为“燕喜亭”。
第三,以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所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为议论中心,先借州民之口,以层进之法,突出燕喜亭周的佳美。然后笔锋一转,写王仲舒发现亭址,乃是“天作而地藏之以遗其人”。这倒不是宣扬天意,而是借此突出王仲舒的品格,说明只有象他这样的人才能发现这样奇异之景。最后总结说王仲舒的德行、爱好正与孔子所说的仁智之乐相符合,这又进一步突出了王仲舒,将他乐山乐水的道德人格和高雅情怀,提高到圣人赞许的高度。写到这里,已经水到渠成,符合圣人之道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故而说:“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值得玩味的是,文中说王仲舒贬官“自蓝田入商洛,涉淅湍,临汉水,升岘首以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由郴逾岭。猿狖所家,鱼龙所宫,极幽遐瑰诡之观”的自然景观,既是王仲舒的经历和所见,也是韩愈由监察御史贬阳山令的经历和所见。如果说这一段在明里是借山水风景来写王仲舒,那么暗地里却是写自己的乐山乐水,并且同样是智者兼仁者,自然而然也是“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的。这种“暗渡陈仓”的手法,确乎称得上鬼斧神工,运化无痕。就全篇而言,写景记亭只是写人的陪衬,在构思上和柳宗元的《愚溪诗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