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阳休之书》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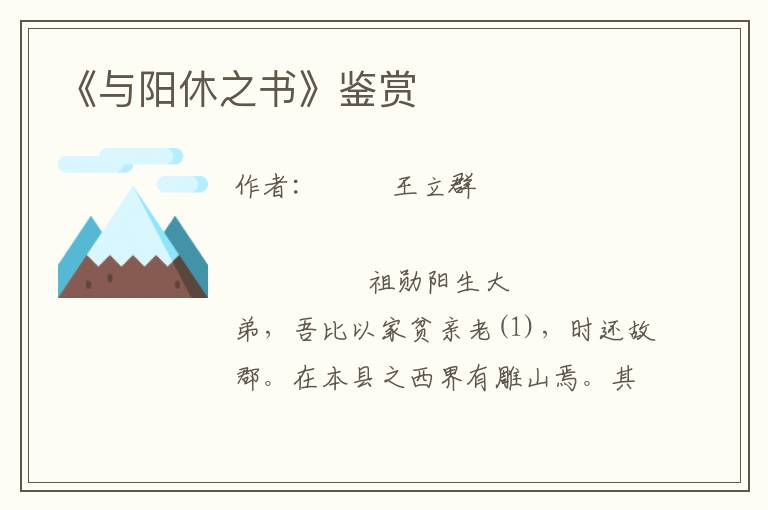
作者: 王立群
祖勋
阳生大弟,吾比以家贫亲老(1),时还故郡。在本县之西界有雕山焉。其处闲远,水石清丽,高岩四匝(2),良田数顷,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乱荒废,今复经始。即石成基,凭林起栋。萝生映宇,泉流绕阶。月松风草,缘庭绮合(3);日华云实,傍沼星罗。簷下流烟,共霄气而舒卷;园中桃李,杂椿柏而蒽蒨(4)。时一褰裳涉涧(5),负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6)。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听风声以兴思,闻鹤唳以动怀。企庄生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旷(7)。首戴萌蒲(8),身衣缊袯(9),出艺粱稻(10),归奉慈亲,缓步当车,无事为贵,斯已适矣,岂必抚尘哉(11)!
而吾生既系名声之韁锁,就良工之剞劂(12)。振佩紫台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匮之漏简(13),访玉山之遗文(14)。敝精神于丘坟(15),尽心力于河汉。摛藻期之鞶绣(16),发议必在芬香。兹自美耳。吾无取焉。
尝试论之。夫崑峰积玉,光泽者前毁;瑶山丛桂,芳茂者光折。是以东都有挂冕之臣,南国见捐情之士。斯岂恶粱锦,好蔬布哉,盖欲保其七尺,终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达,声华已远,象由齿毙,膏用明煎,既览老氏谷神之谈(17),应体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拼簪;则吾于兹山,庄可办一。得把臂入林,挂中重枝,携酒登,舒席平山,道素志,论旧款,访丹法,语玄书,斯亦乐矣,何必富贵乎?去矣阳子,途乖趣别,缅导此旨,杳若天汉。已矣哉、书不尽意。
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究竟应当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对于已经解决了生存需求并充分意识到人生选择的封建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个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求富贵之乐,则可能如“崑峰之积玉,光泽者前毁;瑶山丛桂,芳茂者光折。”保“七尺”之躯,则必须“解佩捐簪”,结庐山林。“孤坐危石”、“独咏山阿”的归隐生活,虽然在物质生活上较之仕途官场,显得清贫寂寞,但是“簷下流烟”、“园中桃李”之景,自有其足乐之处。更何况“采漏简”,“访遗文”的读书著述,还有其独到之快意。这种精神上的轻松自得,当然非仕途可比。至于友朋之间,“把臂入林”,“携酒登”,此种乐趣,宦途之中更无从领略。无怪乎作者要高呼“兹自美矣”,“斯亦乐矣”了。
南北朝之书信山水文,虽寥寥数篇,但多成于南朝作家之手,且俱为零简片牍;祖氏此书,首尾俱存,是为完璧,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与其它几篇书信山水文相较,此文表述的物我同化的山水体验也颇有深度:“时一褰裳涉涧,负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此刻作者似乎不再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涣然融汇到自然之中。同时,此刻的山水自然,也不再具有道德、情感、理性价值、无功利无实用,回归到自然的本体。无知觉无意识的自我进入无目的无价值的自然,二者不分你我。物即我,我即物,物我同化,人的本体与自然的本体合二为一。作者在这种物我同化的体验中,获得了灵魂的安宁、心理的澄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