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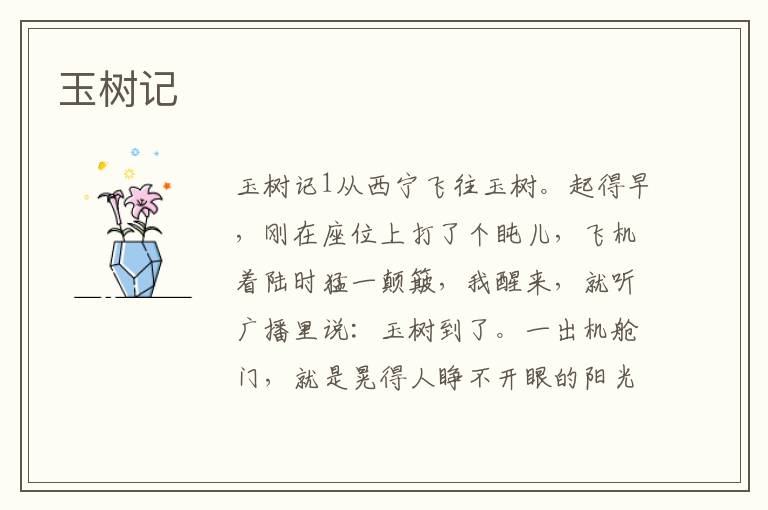
玉树记
1
从西宁飞往玉树。起得早,刚在座位上打了个盹儿,飞机着陆时猛一颠簸,我醒来,就听广播里说:玉树到了。
一出机舱门,就是晃得人睁不开眼的阳光。几朵洁白得无以复加的云团停在天边,形状奇异。云后的天空比最渊阔的海还幽深蔚蓝。几列浑圆青碧的山脉逶迤着走向辽远。这就是高旷辽远的青藏。走遍世界,都是我最感亲切与熟稔的乡野。辽阔青藏,一年之中,即便能一百次的往返我都永远会感到新鲜。无论踏上高原的任何一处,无论曾多少次涉足,还是从未到过,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如果放任自己,可能会有泪水湿润眼眶。我并不比任何人更多情,只缘这片大地于我就有这种神奇的力量。
一只鹰在天际线上盘旋。
也许并没有这只鹰,我就是会“看见”。我抬头,那只鹰真的悬浮在天边,随着气流上升或者下降,双翅阔大,姿态舒缓。
大多数时候,我在内地别一族群的人们中生活与写作。在他们中间,我是一个深肤色的人。从这种肤色,人们轻易地就能把我的出生地,我的族别指认出来。
现在,在机场出口,更多比我肤色还深的当地同胞手捧哈达迎了上来。我这个人,总是受不住过于直接而强烈的情感冲击,于是迅速闪身躲到一边。最终还是被推到迎客的酒碗面前,姑娘高亢的敬酒歌陡直而起。面前的三只小银碗中,青稞酒晶莹剔透,微微动荡,酒液下的银子,折射光线,如那歌声与情意,纯净、明亮。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同时感到,身体内部,某处,电闸合上了,情感的电流缠绕、翻卷、急速流淌,我端起酒碗的手止不住轻轻颠抖。
就这样我来到了玉树。我来到了这个在藏语的意义里叫“遗址”的地方。
玉树和玉树州府所在地结古镇,因为一场惨烈的地震让世界听闻了她的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到达。我在一篇叫作《远望玉树》的小文里写过,“记得某个夜晚,好大的月亮,可能在几十公里开外吧,我们乘夜赶路,从一个山口,在青藏,这通常就意味着公路所到的最高处,遥遥看见远处的谷地中,一个巨大的发光体,穹隆形的光往天空弥散,依我的经验,知道那是一座城,有很多的灯光。我被告知,那就是玉树州府结古镇了。但我终究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在青藏高原上,一座城镇,就意味着一张软和干净的床,热水澡,可口的热饭菜,但对于一个写作者,好多时候,这样的城镇恰恰是要时常规避的。因为这样的地方常常会有与正在进行的工作无关的应酬,要进入另外与正在进行的工作相抵牾的话语系统。对我来讲,这样的旅行,是深入到民间,领受民间的教益,接受口传文学丰富的滋养。但那时就想,终有一天,结束了手里的工作,我会到达她,进入她。”
是的,我不止一次从远处望见过这个镇子的灯光。
从附近的称多,从囊谦。
现在,在这个阳光强烈的早晨,我终于到达了。从机场到结古镇的路上,一个深肤色高鼻梁的康巴汉子坐在了我身边,我的手被有力地握住:“老师有什么事情就告诉我们,要见什么朋友也请告诉我们。”
这是个我不认识的人,但分明又十分熟悉。我们这个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仅凭身上那一点点相同的气息,就能彼此相认相亲。我说:“谢谢,但我不是老师。”我开玩笑说,“托时代进步之福,靠卖文为生,我还能养活自己,我不用兼职做家教,所以,请不要叫我老师。”其实,我想说的是,当我面对自己坚韧的族群自己的同胞,我从来都只感到自己是一个学生,雄浑广阔的青藏高原,就是给我一千年时间来学习,也并不以为能将其精神内核洞穿。
我只说了一个名字,一个民间说唱艺人的名字。那是一个给过我帮助与教益的人。我说:“我要去看望他。”
2
路上,车里,主人在介绍一些玉树的基本信息。提到结古镇在藏语中的意思是“货物集散地”。在一千多年的时光中,这个古镇处于从甘青入藏的繁忙驿道上。这条古道有一个如今成为一个流行词的名字:茶马古道。也有一条渐渐被忘记的名字:磨香之路。这也是一条文化流淌与交汇之路。所以,这个古镇,曾经集散的岂止是物质形态上的商品。经过这个镇子进入的,还有多少求法之人;经过这个镇子走出的,还有多少渴望扩张自己视野与世界的人?
在前面有着稀疏白杨树夹峙着河岸的山谷中,一团尘雾升起来,我知道,结古镇就要到了。真的,那些尘雾就是从正在重建的结古镇,从整个变成了一个大工地的结古镇升起来的。
我们就进入了那团尘烟。高原的空气那么透明,身在尘烟之中而尘烟竟消失不见。工地总是这样,浮土印满车辙,各种机械轰鸣着来来往往,节节升高中的,已显示出大致轮廓的半成的建筑上人影错动,旗帜飘扬。未来的学校,未来的医院,未来的行政区,未来的商厦,未来的住宅,我们穿行其间。没有地震废墟,只有渐渐成形的建筑在生长。这里是青海,我想起了成就于青海也终了于青海的诗人昌耀的诗句:
钢管。看到一个男子攀援而上
将一根钢管衔接在榫头。看见一个女子
沿着铜管攀援而上,将一根钢管衔接到另一根榫头。
他们坚定地将大地的触角一节一节引向高空。
高处是晴岚。是白炽的云朵。是飘摇的天。
那是诗人写于上个世纪那令人鼓舞的八十年代的诗,现在,却似乎正好描摹着眼前的情景。就是这样,被强烈地震夷为平地的古镇正在生长,飘摇的天让人微微晕眩。
那个挖掘机手,轻轻一按手里的操纵杆,巨大的挖斗就深掘地面。那个开混凝土罐车的司机,不耐路上车流的拥堵,按响了声量巨大的喇叭。喇叭声把路口那个疏导拥堵车流的年轻交警的呼喊声淹没了。
这样的情形令我感动。
工地的间隙里是板房中的小店,饭馆。四川汉族人的饭馆,青海藏族人的饭馆,撒拉人的清真饭馆,肉店,蔬菜店,电器店,旅馆。生活还在继续,热气腾腾。不像我去过的别的灾区,浩劫之后有一种哭诉的情调。驰名整个藏区的嘉那石经城在地震中倾圮了,但虔诚的信众们并不以为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六字真言,那些祈祷文,那些整部整部经卷的功德与法力会因此而稍有减损,人们依然手持念珠绕着石经城转圈、祈祷,为自己,为他人,也为整个世界。
我也因这样的情形而感动。
当然也听到好多生命毁伤,家破人亡的故事。但人们只是平静地述说,就像在述说遥远的故事,就像这些故事不是亲历,而只是听闻,是转述。活脱脱就是流行在青藏高原上那些口传故事的风格。讲这些故事的,有失去了不止一位亲人的人,有失去了自己刚建成不久的颇具规模酒店的人,有震中受重伤,身上的一些关节被替换成合金构件,回到工作岗位就服务于众人的人。还有,一位一定要在震后的玉树办起一份文学杂志的朋友。我没有看见有人流下过半滴眼泪。反而,我看到很多的平静与微笑。我喜欢这种平静中的达观。
高原上难得的温暖季节依然如期而至,草地碧绿,百花盛开。我四处走动,看到人们依然按照习惯,在靠近漫漶流水的草地上搭起帐篷,外出野餐。当我在附近的小山上把镜头对准一丛丛点地梅细密的小花时,从河谷中的野餐地,有悠远的歌声传来。歌声从谷地中升上来,达到与我平齐的高度,稍作盘桓,又继续上升,上升,升到了比身后的岩石峰顶更高的天上。我趴在馨香的草丛中,用镜头对准细碎的花朵,取景框中,焦距始终模糊不清。扶摇而上的歌,调子与词句我都非常熟悉,但那一刻,我却因为心头涌起的热流而泪光闪烁。
一位年轻的活佛,定要请我到他家里做客。他让我坐在比他高的座位上,亲手为我沏茶。然后,打开电脑听他新写的歌。他说,他要写出一种歌,采用流行的方式,但不是一般的情爱表达,而是有宗教感的,要有对于生命和对宗教本质感悟与思考。也许,他的歌与他的追求间尚有距离,但我想,催生他想法的这些因缘,同样也将是我从这块土地上领受的深厚教益。能有机会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沉潜于自己的族群和文化之中,做一个学生,并不断收获新知识新感受,是上天对我的厚爱。
3
就在那天上午,穿过喧腾的工地,穿过那些劳作的人群,穿过被阳光照得闪闪发光的尘土,一幢三层楼房出现在眼前。汶川地震后,我去过许多被瞬间的灾变损毁的地方,因此熟悉建筑物上那些狰狞的裂纹,知道是怎样的力量使这座建筑在一楼和三楼保持住基本轮廓的情况下,让之间的二层几乎消失不见。我们被告知,这将是整个结古镇唯一保留的地震遗迹。我还进一步知道,震前,这座建筑是一家以伟大的史诗主人公格萨尔命名的宾馆。格萨尔史诗是属于全体藏族人的伟大的精神遗产,更是康巴人的英雄——他出生在康巴,建功立业也多在康巴大地,在康巴人的心中,英雄受到加倍的崇仰。所以,我推测,这座以格萨尔命名的建筑作为纪念物得以保留,不仅仅只是因为这座建筑所留下的地震毁坏力的骇人印迹。
几年前,我曾在这座城镇四周的草原上搜集英雄的故事。就在那时,我就听人们不止一次提起这个镇子上的格萨尔广场。不止一次,有人向我描述那个广场中央塑造的威武的格萨尔塑像。我也在想象中不止一次来到那尊塑像面前。我甚至把这个广场与塑像写进了我的也叫《格萨尔王》的长篇小说。我寻访英雄故事的时候,没有到达结古镇。但我小说中,那个追寻英雄足迹的说唱人晋美到达过这个广场。
在这里,说唱人晋美与要跟他学习民间音乐的年轻歌手在此分手。
他们又到达另一个号称是曾经的岭国的自治州了。
他们从山坡上下来,贴地的风从背后推动着,使他们长途跋涉后依然脚步轻快。地上的风向北吹,天上的薄云却轻盈地向东飘动。这个城市的广场很宽阔,两个人坐在广场上英雄塑像基座前的喷泉边,看人来车往。年轻人说:老师,我们该分手了。他还要给他一些钱。晋美拒绝了。他的内心像广场一样空旷。身后,喷泉哗然一声升起来,又哗然一声落回去。他说:调子是为了配合故事的,为什么你只要调子,不要故事……
年轻人弹着琴歌唱。他唱的是爱情,他看见年轻人眼中有了忧郁的色彩。开始他只是试着低声吟唱,后来,琴声激越起来,是他教给他的调子,又不是他教给的调子。这使他内心比广场更加空旷。
……晋美起身了,歌手一旦开始歌唱,就无法停止。歌手用眼光目送着他,那眼光跟歌唱的爱情是一致的,无可如何,但又深情眷恋。当整个广场和人群都在晋美背后的时候,他流泪了。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也是一个说唱人,我不自视高贵。这个世界从来就是权力与物质财富至上,在当今时代,这一切更是变本加厉。但我坚持相信,无论是一个国,还是一个族,并不是权力与财富的延续与继承,而是因为文化,那些真正作为人在生活的人,由他们所创造与文化所传承的文化。我以为自己的肉身中,一定也寄居着说唱人的灵魂。我不自认高贵,但我认为可以因此从权力与财富那里夺回一点骄傲。
现在,我来到了这个广场。我早已从地震刚刚发生时那些关于玉树的密集的电视新闻中,知道了所谓喷泉是出自于我的想象。但那座英雄雕塑一如我的想象。这个形象在那些古老唐卡中我曾多次遇见。但在这里,这个形象变得如此立体,坚实的基座上,那黝黑的金属铸成的人与马,与兵器与盔甲如此浑然一体,威武庄严。那么猛烈的地震,没有对这座塑像有丝毫的动摇与损伤。我当然要为此献上一条哈达和我内心一些沉默的祝祷。我当然很高兴和当地的同胞一起在塑像前合影留念。格萨尔的英姿高高地矗立在我们身后,背后,是深远的蓝空和洁白的流云。做过一个梦,在拜读一位喇嘛诗人的诗句,惊奇他突然摆脱了那些陈腐的修辞,把流云比作精神的遗韵与情感的馨香。
我来到这里,不只是因为结古镇这个古老城镇正如何成为一个新生的样板,更因为我一直在因虔敬的固守而踟蹰难前的文化中寻找格萨尔史诗中那种舍我其谁的奋发精神与心忧黧首的情感馨香。
因为这种奋发,松赞干布的大臣去到了大唐。
因此,一个美丽女子走上了从大唐长安到吐蕃都城逻些的漫漫长途。因为这位唐朝公主的经过,结古这个今天还焕发着生机的名字从深沉的史海中得以浮现。一千多年!我们在板房中任手抓羊肉慢慢冷却,任杯中啤酒泡沫渐渐消散,嘴里感叹着:一千多年!即便这一千多年来,我们可能不断转生,但失忆的我们,只能记得此生这几十年的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一千多年是怎样地悄然流逝同时又贯通古今。聚集的财富消失了,权力的宝座倾圮了,流传至今,只是深潜的情感与悠久的文化。
又一天的太阳照亮了大地。
负责接待我们的主人把我带到了浩浩荡荡的通天河边。他们好意,不让我只去看一个又一个重建项目。他们相信,物质的重建会很快完成,但文化方面的重建会更加漫长与艰难。所以,他们还邀我们看看风景与文化遗存。我们来到通天河边的肋巴沟口,大河水深沉地鼓涌着向东南而去。河岸上,那些草地与绿树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主人带我看一面摩崖石刻,一面向河的石壁上,浅浅的线条勾勒出一尊说法的佛,佛头上有一轮月晕般的浑圆光圈。佛像的风格与镌刻方式透露出久远年代的气息。更加显出年代特征的是,说法佛侧下方那个戴着吐蕃时代高筒帽的男子,和与阎立本画中一样留着唐代女人发髻的面孔浑如满月的女子,她的手中,还持着一枝开放的莲花。
文成公主从唐蕃古道入藏时,曾在玉树的结古一带作较长的休整。传说这壁说法图就是她留下的。那么,那个顶着唐式发髻者,是她为自己所作的造像吗?佛法从印度兴起,绕过青藏高原,东渐汉地,所谓“佛法西来”。这时,佛法又从东土向西而去,并在西去途中在此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瞻礼之时,当地的朋友争相为我解说,使我深感温暖。
然后,我们溯汇入通天河的飞珠溅玉的肋巴沟溪流而上。沿途,满溢着碧绿草木的馨香。一千多年前,文成公主踏上了这条道路,而这条道路显然比一千多年更古老。一千多年后,这条路还像新开掘出来一样,前些天的雨水在泥路上留下清晰的冲刷的痕迹,裸露的石头干干净净。路边开满了野花:鲜卑花、唐松草、锡金报春……一个偏僻辽远的所在,那些草木的命名中,也强烈暗示着遥远地理间的相互关联。然后,又是一处摩崖造像,那是另一位入藏和亲的唐朝公主留下的遗迹。瞻礼如仪后,我们继续往前。
地势渐渐升高,溪谷也越来越开阔。随着海拔升高,植被也迅速变化。一丛丛的硬枝灌木出现在高山草甸上,开粉色花的高山小叶杜鹃,开黄色花的金露梅。这些开花的灌丛,从眼前一直铺展到天际线上。更宽广的草甸上,是紫色的紫菀的天下,是白色圆穗蓼的天下。我热爱青藏高原上的旅行,自然中包藏着文化,文化在自然中不经意地呈现。我问陪同的主人,有没有带上些干粮,回答是没有,我遗憾不能来一顿草地野餐。盘腿坐在草地上日光下,背后是雄浑的走向辽远的山脉,面前是叮咚有声的溪流。就这样,不过一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海拔四千多米的山口。背后的峡谷向东南而去,而面前另一道峡谷向着西北方敞开。
顺着蜿蜒的公路下到峡口,是香火旺盛的文成公主庙。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进种种庙宇。作为一个身上天生就有宗教感的人,却总对处于我们与宗教的终极关怀间,我们与神祇的昭示间的神职人员保持着某种警惕,也并不以为那些庙堂中享受香火的偶像真能代表那些缥缈深沉的神祇。但在此地,风振响着满山的经幡,还有好些人在庙后的小山顶上播撒风马。我脱鞋揭帽,进到庙里,但没有匍匐在崖龛中的佛像跟前,只在心中瞻礼如仪。然后,伸出双手,两个年轻喇嘛把取自龛后的清冽泉水倾倒在我掌上。
我小饮一口,一线清凉直贯胸臆。我以为,自己的身,越过了语,直会了意。
然后,我们去到巴塘乡的重建工地。
怀着感动与敬意,从巴塘乡重建工地出来,已是六点多钟,夕阳西下。高原的大地在这样的光线下更显得邈远深广,那些耸峙在宽广草原尽头的岩石峰峦都在闪闪发光。
忍受着强烈高原反应一起采访的朋友该回去休息了。我对主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去看看草原上的鲜花。
三四年了吧,我一直在追寻高原花草的芳踪,高原植物学成为我一门业余功课。是四年前某一天,川藏线上,站在一座雪山垭口,对着身边那些摇摆在风中的种种花朵,我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些严酷自然环境中的美丽生灵一无所知,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甚至叫不上它们的名字。我突然因此感到惭愧。说自己如何热爱这块土地,却对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事物一无所知。这个时代,爱成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轻易脱口而出的词语,同时,却对于倾吐热爱的对象茫然无知。
爱一个国,不了解其地理。
爱一个族,不了解其历史。
爱一块土地,却不了解大地集中所有精华奉献出的生命之花。
因此,一个伟大庄重的词终于泛滥成一个不包含任何承诺,也不用兑现的情感空洞。
我意识到了这种热爱因为缺乏对于对象的认知而变成了一种情感空洞。我决定不再容忍自己身上的这种荒唐的情感。
从此,当我在青藏高原这片我视为自己的精神高地上漫游时,吸引我的不再只是其历史,其文化,以及由历史与文化所塑造的今天的族群的情感与精神秘密。我也要关注这土地上生长的每一种植物。从此,不止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每一种生命都成为我领受这片土地深刻教益的学习对象。
所以,我现在要去拜会那些在这个短暂的美好季节里竞相盛放的花朵。我很高兴新结识的当地朋友乐意陪伴我。我们调转车头,向草原深处驶去。我很高兴能把一种种自己认识的草木指示给这些比我年轻的朋友。
在这个高度上,已经没有了树木生长。于是,总是用藤蔓缠绕与攀爬的铁线莲失去了上到高处的依凭,在公路两边的砾石中四处铺展,同时奋力高擎起铃铛般的黄色花。
而一层层叶片堆叠而上,奇迹般长成一座座浅黄色宝塔的名叫苞叶筋骨草,一枚枚精巧的唇形花就悄然开放在层叠而上的苞叶下面。
当我们停下车来,草原上细密的白色小花从面前铺展开去,直到视线尽头山峰浓重的阴影中间。那是白花刺参,带刺的叶片间坚立起一根带楞的长茎,顶端举着数朵一簇的象牙白的唇形花。我趴在草地上,从镜头中注视这些花朵如何反射黄昏将临时那最变幻迷离的光线。我用微距镜头表现它们的细部特征,再换上一只广角镜头,表现这些美丽生灵的广布与纵深。
直到夕阳西下,最后的一片光线紫红的阳光消失时,仿佛听见六弦琴一声响亮的拨弦后余音悠远。
晚上,在没有桌子的板房中,趴在床边在电脑上整理这些照片,竟忘记约了那位为我演唱过格萨尔王传的民间艺人来谈话。他也不来打搅我,竟在院子中等到半夜三点!
在玉树,那么多美好的印象应接不暇。最令人难忘的,还是这些真诚朴质的老朋友与新朋友们带给内心的温暖。正是如此醇厚的温暖让这回短暂的走访显得更加短暂。
怀揣着那么多的感动,真的要离开了。
玉树,在此之前,我曾经拜访过它西北部的平旷荒野,也曾经游历过它偏南方向横断山区最北端的高山与深谷。现在,我又来到了它的心脏结古镇。来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有酒,有歌。送别的时候,也是一样。可以说这是一场送别的盛宴吗?食物其实非常简单:现煮的牛肉和羊肉、油炸馓子、酸奶、青稞酒。但的确是一席盛宴。地点经过精心安排,开满了紫菀与毛茛的草滩上,一座美丽的白布帐篷,四壁挂着当地的摄影爱好者们精美的作品。还有那么美妙的歌声与敬酒。这些是受灾者也是重建者的人们用他们的豁达与乐观让我们领受一种文化的伟大力量。
这是最难分手的时候,我却再次要求几个朋友提前出发,再去看看机场路沿途那些前些天不及细看的花草。
我记得那一丛丛紫色的鼠尾草。
我的家乡距此将近两千公里,但那几位当地的朋友也和我一样,曾在童年时,把这些漂亮的管状花从花萼中拔出来,从尾部细细啜吸花朵中蕴藏的花蜜。现在,这些花一丛丛开放得那么茂盛,在强劲的高原风中不停摇晃。我拍下了它们美丽的身姿,在流云如浪花翻拂的高原的蓝空下面。我加大相机的景深,把丛丛蓝色花背后的河谷中通向深远的路,和一段高耸的曾经的陡峭河岸纳入背景。
几分钟后,我就将从这条路上去往机场。
我不想说再见。我对这些新朋友说,我还要再来。一个人来。我说出一个又一个的地名,都是玉树这片雄阔高原上,我从未到过的地方。还有一些,是去过了,但还想再去的地方。
我们正日渐廓清文化的来路,却还并不清楚文化去向未来的路径与方向。我相信,这个答案,只能从民间新生活中那些自然的萌芽中得到启发。能够找到吗?我不肯定。我唯一知道的只是,我们不能因此放弃了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