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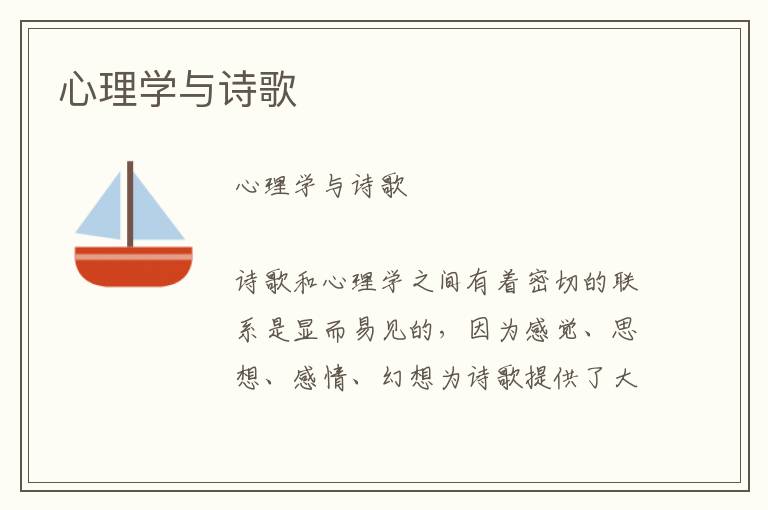
心理学与诗歌
诗歌和心理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感觉、思想、感情、幻想为诗歌提供了大部分必不可少的素材,因为精神活动作为对诗歌产生反应的机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们对这两者密切联系的程度以及心理学在诗歌批评中的应用范围,却不甚明确。这是因为很难划出诗歌或心理学的界线。如果把一切内心活动的内容和过程,都看作是精神活动的话,那么现实中可以被认识的一切就都是精神活动了,诗歌的每个方面在原则上也都可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题了。事实上,凡是尊重“精神的现实”的批评文章,从广义上讲,都可以说是心理学批评。心理学与诗歌的联系是错综复杂的。当弗洛伊德为了命名一个心理学概念“奥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时,他转向富于戏剧性的古代诗歌,从中找到了这个名称。他正是从文学和神话中推衍出了心理学概念。关于奥狄浦斯的故事以及弗洛伊德从中看到的意义模式不仅存在于这个科学概念之前,而且也带上了神话的色彩。同样复杂的是,许多从心理角度对诗歌所作的重要评论,都是在论述文学艺术的著作中偶尔述及的,而不是在研究诗歌的著作中专门论述的。因此可以认为心理学所描写的是任何形式的精神活动的性质。下面主要谈谈批评界自觉运用实验心理学对诗歌性质所作的各种研究。
每个时代的心理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人类精神活动的作用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或者为诗人所采用,或者为诗人所反对。了解诗人所处时代在心理学方面的见解,会有助于说明诗歌作品。例如,知道伊丽莎白时代关于灵魂的看法有助于解释莎士比亚的作品。又如,读过W·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1890),了解这部书对“意识流”的见解,就有助于说明现代诗歌和小说。然而,J·L·洛斯对柯尔律治的研究表明批评并非一定要借助于心理学这样一个系统化的学科,批评本身就能对诗人的心理活动提出许多见解。大部分运用心理学阐明诗歌的批评论述都是从精神分析学当中派生出来的;文学界注意这一学说是在S·弗洛伊德于1900年发表《梦的解析》以后开始的。精神分析学反映了历史的、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时刻。K·伯克曾说:“在产生伟大戏剧的时代,观众理解剧中人物为什么要采取他们所采取的行为。”H·J·马勒也曾讲过:“稳定的文化产生稳定的和标准的行为模式;行为动机也和生活方式一样带有社会性。虽然剧中人物可能在短暂的时间里会感到迷茫、困惑甚至产生逆反心理,但是他们最终会和观众一样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动机。”在文化崩溃的时期,当D·H·劳伦斯等小说家和诗人宣称应把注意力从“旧有的、稳定的自我”转向同一精神成分的“同素异形现象”时,弗洛伊德的学说在提供一种新的社会化动机上就显得异常重要。而且,精神分析学也使得文学批评家能集中研究诗歌创作和反应当中一些过去未曾受到注意的成分。
虽然弗洛伊德偶尔也写过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论述,但是精神分析学中关于文学的理论大都来自他在对宗教史、文化史、戏谑、失言、神秘事物,特别是梦境方面进行分析时所作出的一些提示。弗洛伊德通过对梦的解析分析文学及其他精神产物的途径,也部分地被L·蒂克、A·叔本华、J·保罗、F·尼采、F·菲舍、W·狄尔泰等人所采纳。他们发现在做梦与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类似的情形。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做梦使人的本能性冲动获得幻觉性的满足,而艺术则占领着“愿望难以实现的现实世界与实现愿望的幻想世界之间的地带”(弗洛伊德)。像做梦一样,艺术作品不仅有表达于外的明显内容,而具有隐藏于内的潜在内容,后者来源于充满本能的潜在意识,而且早期的精神分析式批评当中很大一部分的目的就在于提示文学作品中具有活力的潜在内容。因此,弗洛伊德和后来的E·琼斯,都把《哈姆雷特》看作是表现主角的乱伦恋母愿望和对父亲的矛盾心理,认为这部作品所取得的戏剧和诗歌效果是通过在观众心理上引起和表现恋母情结而达到的。按照这种观点,语言的意义主要是用以满足内心世界对感觉及逻辑推理的需要,因此就要减轻对被禁止的愿望的反对,容许满足这些愿望。正如N·霍兰德在《关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概述》(1966)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艺术形式的真正乐趣来之于不合逻辑和荒谬无理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又反过来表现了‘精神活动的省力原则或者是表现了从理性压制下解脱出来的轻松状态’。我们的快感来之于使我们保持正常逻辑理性的精力获得放松或减轻;我们都体验过突然精力有余的感觉,体验过节省精力突然在精神上所获得的裨益。”
近期的文学批评反映了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弗洛伊德创始的精神分析学在理论上的发展,主要的研究者有:A·弗洛伊德、H·哈特曼、E·克里斯、M·克莱因等。这些发展所关注的主要是:自我为了维持本身活动以及为了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取得某种可行的平衡的力量。精神分析式的文学批评反映了这些兴趣,它开始把文学作品不仅看作是隐蔽地表达被禁止的愿望,而且看作是反映“自我”在应付处理这些愿望与对待觉察到的道德感时所采取的不同程度的策略性方式方法。因此,文学作品表达出来的明显内容反映了潜在意识中幻想的转化;作品的形式和意义,不仅是对潜在幻想的掩饰,而且服务于这种转化过程。艺术能使人们的精神活力实现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本身就能给人以快感。而且这些转化和转变与潜在意识的非理幻想成功地进行升华的过程非常相似。正像霍兰德指出的,文学形式“对我们起着防护自卫的作用——它分裂、隔离、破坏、转移、消除(通过抑制或否定)幻想中快乐的但引起焦虑的因素”。精神分析学涉及诗歌形式的重要概念有“凝聚”(即一个形象或角色具有不同的心理倾向)和“转移”(即一种心理倾向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如弗洛伊德认为麦克白夫妇属于同一心理倾向但具体表现不同)。
有一部分精神分析式文学批评被称作“心理传记”——即运用精神分析学或心理动力学的观点和方法评述某个人的生平。在运用这种方法写作的一些文学性传记中,如B·迈耶的《约瑟夫·康拉德传》,确实令人信服地窥见了作家生活及作品中不为人知的隐蔽部分。有人曾以这种方法对几位诗人进行过分析,包括M·波拿巴对爱伦·坡、J·科迪对E·狄更生的分析;科迪就是根据精神分析学理论和精神病临床理论作出结论的。以精神分析理论作精密的联想研究可见于P·德特林对R·M·里尔克的分析;他不仅把诗人的创作动机追溯到传统的恋母情结,而且追溯到近几十年来精神分析所探讨的前恋母阶段的发展。里尔克的“自恋欲”被看作是一种复杂的诱发性模式,表现为一组复杂的、可变的、展开的诗意象征,其中包括“天使”这个象征。克利斯、霍兰德、A·埃伦茨韦格等研究者,近年来以比前辈批评家更加微妙的方式探讨文学感应的问题。精神分析学现在已经接触到一些尚待探索的领域,可能对诗歌批评有重大的意义,例如,由J·A·M·梅尔洛所提出的未发展的预感,即诗歌节奏表达出有机体幼儿时期的古老反应,表达出固有的生物信号密码。另一个领域是由H·科胡特提出的,他认为自恋欲预示着自我发展并形成这种发展的基础;自恋欲还含蓄地见之于某些创作活动的形式及其所受到的干扰。还有一个领域是埃伦茨韦格提出来的,他注意到一些有助于形成艺术形式的、超出意识控制的整理排列过程。而且,精神分析学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能够对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提出了某种心理学方面的解释,在这点上是没有其他学派可以与之匹敌的。
除了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进行批评的著名人物是荣格。和弗洛伊德不同,他的主要兴趣是文学中的超个人因素;而这一兴趣的重点是精神原型。因为精神原型大体上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形相因(本质性起因)而与动因(近存性起因)不同,后者是精神分析学文学批评的对象。所以精神原型这一概念可以有助于心理学批评家沟通诗歌结构的较低层次与较高层次。荣格认为,诗人有预卜先知的能力;他对艺术的观点使他与柏拉图、锡德尼和强调诗歌与预言关系的浪漫主义流派批评家一脉相承。他对精神活动的过程持预见论或定命论的观点,他认为潜在意识是由群体因素共同组成的,这就使他对诗人和潜意识的关系有着与精神分析学不同的解释。M·博德金认为,能够对作品的形式及其对读者的效果作出解释的主要是精神的形式创造力和它的神秘表现力。因此,艺术主要不是通过部分地解除压抑感而获得效果的;相反,艺术家经常表达的内容是在潜意识中已经充分形成而尚未被“意识”所知的内容。这些内容具有补偿的性质,不仅为诗人也为其时代提供了纠正片面性世界观所必需的材料。
艺术家可能确有精神病理学所分析出来的特点,但这个事实不能用来解释他的作品;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来看,作品是通过加强自我对威胁自我的力量的控制来为自我服务的。相反,荣格认为艺术家经常处于苦恼之中,因为他的天才和职责要求对某些心理功能进行超乎寻常的发展,从而忽视了对正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其它功能。T·舒安纳曾采用荣格关于精神的这种观点对T·S·艾略特的诗歌进行了分析(1971)。G·霍夫曾对“诗歌与精神”作过更一般化的论述。舒安纳还曾试图阐明文学批评和分析心理学对“精神原型”这一术语的使用问题(1970)。荣格派的观点对文学批评似乎比对文学性传记的分析更加适用,但K·威尔逊却运用荣格的观点对济慈的《夜莺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阐明它在济慈一生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在她看来,这首诗歌是以自我对精神原型的体验、对个性最深层的中心的体验为基础的,这种体验导致济慈在诗歌观点上的转变,导致他与他本身的灵感泉源之间关系的转变。威尔逊还运用荣格关于心理态度的类型和功能的学说阐明了济慈诗歌语言的独特性质。G·巴舍拉尔根据荣格的学说创立了局部上超越个人的“灵魂现象学”。他认为,诗歌的意象是“梦境意识”的产物;在这种意识状态下,“主观与客观的二重性一直在不停地转化,闪烁着彩虹般的光彩。”
K·科夫卡等形态心理学家的观点有时也曾被批评家采用(如穆勒),不过在文学讨论中还不常见。在继续和扩大形态心理学关于认知作用的全面性质研究中,M·佩卡姆提出了关于艺术(包括诗歌在内)的一种综合性观点。他认为,人“最向往的是一个可预见的、有序的世界……由于人对那样一个世界的向往非常强烈,因此他必然会排斥任何关于他的理想不能实现的预言,拒绝任何对于他的努力方向的误导,反对任何对于他的信念的怀疑。只有当他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即由精神绝缘的高墙把他同外界隔绝的情况下,他才可能认识到他的兴趣(即他的期待或目标)和他在现实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思想之间的差别”。佩卡姆认为,艺术的功能就在于提供这样一种体验。J·O·洛夫则根据发展认知心理学,分析了V·伍尔夫小说中的神话性特征。心理语言学也被应用于诗歌批评。由于诗歌充满着对人世状态的洞察,能激起某种情绪,并提供对待这些情绪的方式,所以诗歌也被用作精神疗法的一种手段。但是精神疗法中强调的主要是诗歌与散文同样具有的抚慰和教诲性质,而不是使诗歌具有虚拟性而非直陈性的预示性质;所以文学研究者不会从中学到什么东西。
做梦与文学创作及反应之间潜在的相似之处对文学批评有着持续的影响。例如伯克和N·弗赖伊仍然在批评中使用“梦境”这个术语。自弗洛伊德以后,对做梦的解释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行过这方面研究的有荣格、A·阿德勒、E·S·陶伯、K·霍尼、B·S·罗宾斯、E·弗罗姆、W·博宁等等,他们的观点对一些心理学批评都有很大助益。因此,荣格认为:“梦境是自我对抗的一种体验,其目的是揭示而不是掩盖。其中存在的象征性事物不是作为欺哄或虚饰,而是作为比喻性的参照。”按照荣格关于梦的观点,对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潜在内容和明显内容的差别基本上可以不予考虑;对梦的内容和结构都不能看作是随意的,而应看作为支配戏剧性材料的一种必要条件;所以梦的功能不能看作主要是为了实现愿望,而是通过对一种片面的、有意识的观点加以补偿而对精神活动进行自我调整并且使人格保持统一完整。阿德勒等学者指出,“不借助认为潜意识是进攻性及性本能冲动的储藏所这种概念也能保留梦的能动意义。……梦境奇特的思想活动可以理解为个人经历的一种奇特表达方式,而不是潜意识思想方式的突然迸发。”(厄尔曼)这些似乎可以与古代认为梦和诗歌相类似的看法联系起来,更一般地说,可以与诗歌和有关幻想这个诗歌的基本因素的来源、性质和功能等问题联系起来。这些观点中有一部分在文学研究中得到的反响很小,这可能表明在运用心理学观点进行文学批评方面的可能性尚待进一步探索。
荣格曾指出,每一个心理学观点都包含着一种主观自白的重要成分,而现在还不可能产生出为人们所公认的统一心理学。但是总的来说,在批评界中,对于心理学与诗歌之间关系的探讨已经成为一个富有成果、业已确立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