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军《伤怀最是万里月(外一篇)》散文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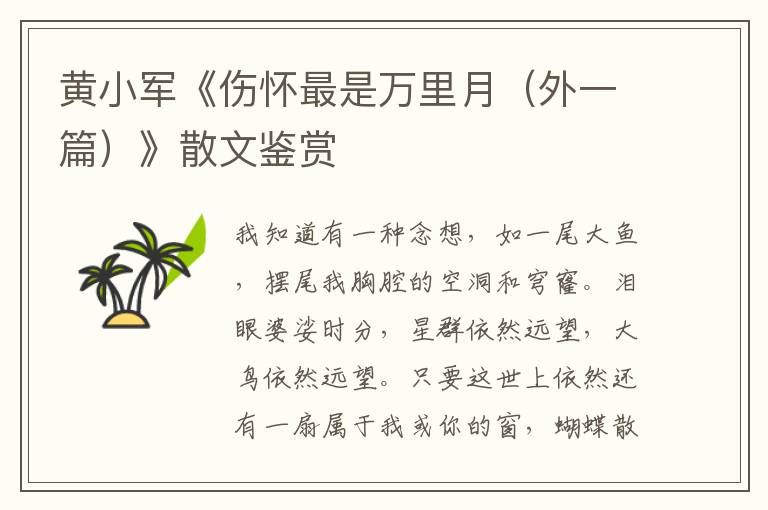
我知道有一种念想,如一尾大鱼,摆尾我胸腔的空洞和穹窿。泪眼婆娑时分,星群依然远望,大鸟依然远望。只要这世上依然还有一扇属于我或你的窗,蝴蝶散尽的时候,漂泊的岁月里,依然还有一弯或者一轮月亮。
投入怀里的月光,无论是因为多情,还是因为寡情,往往都是对的。它深知埋藏在我怀里的小径,在哪个地方拐了个弯,又拐了一个弯,而我当时还崴了脚。然后抬头,记忆便消失了,故事便消失了,岁月便消失了,融在一片柠檬色、橄榄色、苹果青的苍茫之中。
那时的田埂是弯的,炊烟是弯的,孩堤时的童谣是弯的,三姑父长烟杆是弯的,村长家小妹的辫子是弯的,老木屋上满爬的青藤是弯的,连我的过世了很多很多年的老爷爷,他的咳嗽也是弯的。
我爱那时的月亮。那时的小溪、茅草和表嫂家扔在碾台的那个水葫芦,都浸泡在湿漉漉的月色里了,包括树上或者草里一声短一声长的蝈蝈,秋声里的蝉,和池塘里的鸣蛙。这些创造了蓝色天籁的无数零碎小玩艺儿,闹腾着的这么一些声响,或是簡单的应答,或是轻佻的调情,不会也如人类一样,恋爱了吧?
遥想从前的万丈夜空,如若月色下有剪径的小贼,或十万里传报外敌铁骑来犯,这些都是比较让人头痛的。我倒是比较喜欢崔莺莺的人约黄昏后,然后等在后花园里,小姐赠金啦。这倒并不是说我这个人比较贪财,而是有了盘缠,就可以进京赶考了,就可以兼济天下了,就可以风风光光娶莺莺了。那个时代的男人,多少还是有一点西厢情结的。
但月光的确比较如水,绝美的同时,却又绝对凄迷。我敢说,古往今来,没有几个男人,娇娘远在,但秋水难渡,此情此景之下,而不凄迷着流泪,而不凄迷着柔肠寸断,而不凄迷着从此归去来兮而醉卧高榻之上。
但我不能凄迷,我刚刚才读完一本有趣的书,我还有太长的路要走,还有一份蓦然回首的艳遇正有待深入。于是我想,赶走这一地的月光吧,纵然不能一杆子都打了去,不让进门爬上我的大床,尤其不让照在我瘦削而模糊的脸上。读我脸上的泪眼阑珊,我泪眼阑珊着的青春岁月哟。我的青春还零零落落地洒在那一地凄迷的月色中吗?
但天空还是实实在在地在我的月色中,飘浮而又飘散了,又从我右肩上方不远处飘了出来。从一座老屋的檐角上,一棵老槐精灵古怪的枝丫上,再远点便是我表哥的坟头了,再远点天空打了个结,拧成了一朵白云,再远点便是远方的远方了。我想:远方是远方的茅房哟,远方是远方的娇娘哟,远方是远方的深渊哟。
或许这便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吧,世间万物,最能够牵扯起无限远方的、幽幽情怀的、默默絮叨的、忍无可忍的,便是那轮窗前月了。所谓残月如痕,蹇娥眉,万户捣衣声,真是心往哪里痛,它就往哪里戳呀。如若大天空是一张摊开的信笺,这枚戳盖的月,会是枚回家的老邮票吗?
从前,我一直在想,能够一直游走在岁月里的,除了人类堆垒起来的石头,大概只有月亮了。而石头一旦倒下,砸死的不但会是一些正在石头下膜拜的闲客或豪客,还会有不起眼的虫儿,或者草儿,有时还会是一个王朝。如此,只得姑且以为游走在岁月里的东西,只好是那轮老月亮了。
张若虚说: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不还家之痛,千古难逾,大病如大梦,大梦如月呀。
大风起兮
某天,正是有点牢骚的时候,一张抓在手里的报纸,突然飘得老远,我眼见的一只猫,半空里飘着,眼见的万里长风,抱着万里的悲怆或豪迈在跑,抱着万里赤条条的河山在跑,从我的瞳孔,我的肩头,硬生生飘过。
风从海上来,掠过的首先是波涛,或许还有裹胁在波涛上的船,和浪尖尖上的小太阳,但庞大台风的生成,按照所谓涡流理论和空气动力学原理,好像还有个迷人的蝴蝶效应,都是蝴蝶惹的祸。蝴蝶在西半球的镜头里漫舞的时候,翅膀不仅抖落季节,抖落花粉,还抖落出了东半球惊天的浪,于是眼见的人世间有风。
人世间这风真不知刮了几千年了,所有被风刮破了的岁月都在树上挂着,书里藏着。最早的风肯定是公元前就有了,楼兰古国沙地里的风堡和风雕,该有多少的风灌进去,才能把王朝和奔腾的马队挤出来。风神飘一根手指,风堡嘴边轻嘘,夕阳跳了几下,如张骞的那头病骆驼。还有摩西的出埃及,海水居然从中间让开,风竟然推起两边水墙,上苍使然,上帝使然,上苍从来就是上帝吗?还有中国智者诸葛亮杖剑借来的八百里东风,三国命运的大改写,真的仅仅只是群雄角逐的结果吗?
于是人类史有了风萧萧兮易水寒、而黄河也寒、长江也寒的悲壮,有了风小一些的时候,携三五老友,或携一条小狗,风卷黄叶而漫步的雅致,有了夜黑风高揭竿而起的江湖豪客,有了奇怪的树,奇怪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哲学,有了一眼便能看出风起于青苹之末而洞穿世事的隐士或高人。
但大风总是越飘越远的,一如远去的村落和磨盘,和小桥,农人也越飘越远,而且越飘越小了,一如那个飘去的世界。但大风从不死亡,它有根,它的根总盘踞在我们人类认知暂时无法企及的风暴眼里,所以它总能抱着万古的岁月跑,抱着万里的秋色跑,抱着万里唐诗宋词和成万上千的蝴蝶跑。眼见得撞破几朵云了,眼见得倾泻下半座长空了,倾泻下满地苍黄了,倾泻下一个元代的糟老头马致远了,伴着枯藤、老树、昏鸦。
杜甫说轻燕受风斜,刘邦说大风起兮云飞扬,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聂鲁达说河岸上的风永远都在传达新世界的声音,而我说,风太大,我出不了门,就在屋里玩这扇门吧。
所以我很害怕,所以我终于知道,高尔基为什么近乎沙哑高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尽管最后他还是被风吃了。
(作者单位:江西省德兴市第二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