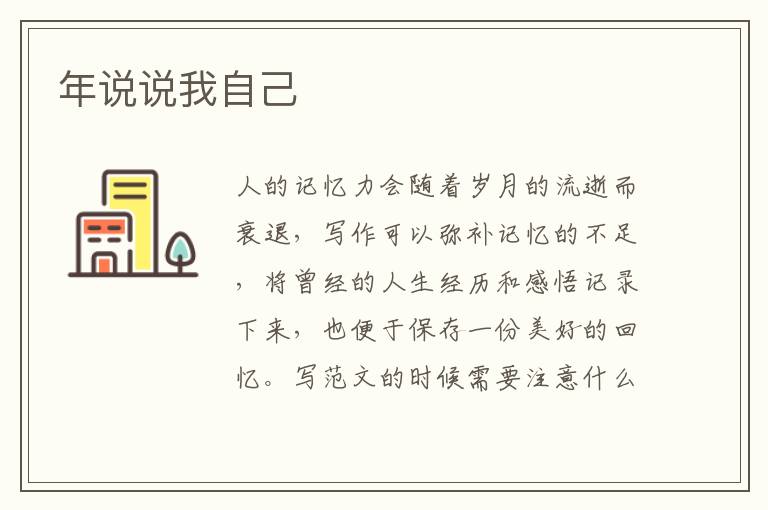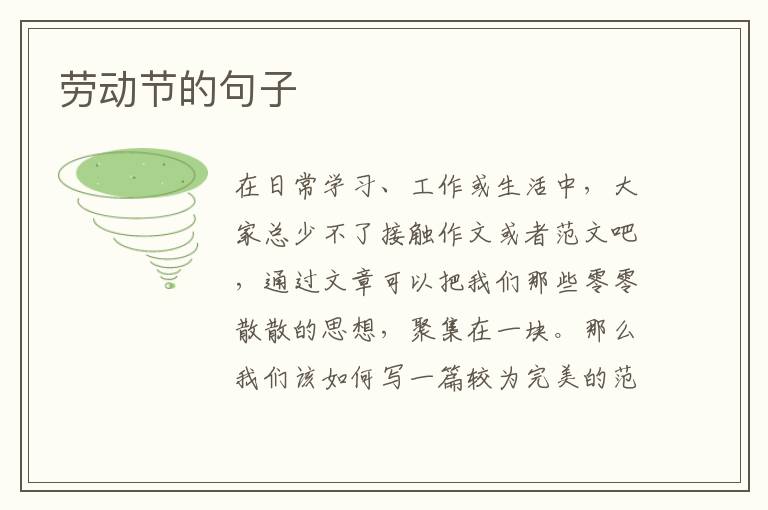小孩回农村前后对比说说汇集三篇

找寻渐行渐远的乡村岁月美文
我生在农村,在农村生活了十八年。
记忆里最早的是儿时居住的房屋,那是一个曾经在农村到处可见的大院,院分为前后院,皆为两层楼房,青砖、青瓦,前院大门口有两个石狮,进大门楼上为戏楼,小时候,我就曾经看过在楼上唱过花鼓戏。前后院用廊道连接,过道边上有柱子支撑,我们叫 伞柱,院中有个很大的天井,院里前后左右住着【第7句】:八户人家,那时候,家家没有什么隔阂,也没什么秘密,友好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小孩子更加亲密无间,打打闹闹,即使有点小的损伤,家长之间也不会互相责怪。
儿时的游戏很简单,很多小孩凑在一起,男孩子多半玩打驼骡、滚铁环,女孩子就是踢毽子、跳房子,冬天天冷,室外不能玩游戏,就一起玩捉迷藏(土话躲个力哥)、挤油渣子,以这些办法来驱寒取暖,乐在其中。
小时候,很多事都感到新鲜。那时候文化娱乐少,一些流动的手艺人、生意人的'到来都成为我们的节日。补锅的、理发的、腌猪腌鸡的都是我们喜欢围观的节目,打爆米花的来了,碰巧家中还些米或玉米、高梁之类,而且父母心情又好,那可就可以很有面子地请一回小伙伴们的客。
看戏是儿时最高兴的事。戏包括电影、皮影戏和花鼓戏,最多最有影响的是花鼓戏,花鼓戏又称土台子戏,【第6句】:七十年代一般都是过年过节或者当地有重大事件的时候,请当地一些艺人组成的班子,用木头、木板搭起台子,挂一个高音喇叭就开场,锣鼓一响,唢呐一吹,十里八乡地人都来了。看电影也一样,那时侯放电影一般到大队部或者人员较集中的生产队,一场电影,可引来周围数十里的人观看,小孩更是最开心快乐的时候,一方面是能看到电影,另一方面则是有许许多多的小孩聚到一起,可以做游戏,可以追逐嘻闹,电影情节无关紧要,享受的是一份欢乐,一份情谊。
现在,农村大变样,经济飞速发展,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尤其是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干净舒适的乡村环境,日渐完善的文化娱乐设施,让村民们体会到和城市一样的感受。但总觉得少了当年的那份自然,那种无忧无虑、悠闲自在的时光已经渐行渐远。
找寻美文随笔
可是结果
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而此刻
我独坐在电脑前反省
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但我可以想象
绝对不是我这样伤神疲惫
因为你找到了归宿
而我?我看不清方向
甚至弄不懂生活的意义
我厌倦了
终于厌倦了,没有丝毫的犹豫
从你身上我明白
想要得到必要学会舍弃
我们只活在现在
是该下决定的.时候了
我们都该向着生活靠拢
让曾经那不切实际的想法都见鬼去吧
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
相信我们都还来得及
在渐行渐远的岁月里读你美文
读你,在风雨兼程的路途中,读你,在渐行渐远的岁月里。读你,在每一个心旌黯淡飘摇的夜晚,读你,有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愉悦。
仿佛世间的花草树木就在读你的那一刻葱郁繁盛的绽放,仿佛尘寰的爱恨情仇就在读你的那一刻寂寥轻薄的淡去。
今生,在漂泊不定的人生旅途中,与你不期而遇,然后相知相别,不能说是上苍的恩赐和馈赠,应该说是命运的轮转和沉陷。
蓦然回首,曾经旖旎的梦境依旧在飘逝的时光里延绵不绝,蓦然回首,曾经缱绻的情丝依旧在流失的岁月里缠绵不断。
千回百转的,不仅仅是蛰伏在流年里的一颗阴霾重生的灵魂,不仅仅是在指尖悄然滑落的曾经丰腴的思念,还有在每一个辗转难眠的夜里恣意流淌的寂寞。
思念如海,浩淼而深邃的弥散在午夜的空怀里,寂寞如烟,清婉而缠绵的萦绕在午夜的心弦上。在与你两两相望的宿命里,在与你生生相错的轮回里,我寂寞成伤。
是谁,曾经在浩瀚的秋光里独自楫舟,一任浓浓落寞铺展于怀?是谁,曾经在萧瑟的记忆里游离寻梦,一任萋萋芳草凋零于心?是谁,将一盏心灯一一点亮,又冉冉熄灭?
极目苍穹,一片凄朦,一片清寒,远处的灯火已经幽暗混浊,只有轻柔的晚风呢喃的声音,轻柔的划过耳畔,有游离的岁月掠过的痕迹,轻缓的滑过足底。
很想就此握紧你的手,握紧岁月的手,让时光做稍许的停留,让我在你厚实的肩头歇息成蝶,在你宽阔的怀里淋漓如雨,在你深深的.爱恋里就此安寐,长眠不醒。
可是,我知道,我不能,今生我已不能。虽然,我曾经走入了你纷扰而孤寂的生命,给了你尘世间最温暖的一段记忆,但是,我却无法成为能够与你一生相依的那个人。
我知道,你亦不能,今生你亦不能。虽然,你也曾经走入过我羸弱而清浅的生命,给过我尘世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但是,你亦不能成为我永远的相知。
人生会有很多的行囊,而每一种行囊里都装有一些人性无法逾越的沟壑。所以,只有放手,放手让彼此走远。
越过千山万水,你已走远,远到我目光无法企及的地方,远到我足履无法抵达的地方。只把深深的祝福留下。
而我,却如一只折翼的蝴蝶,已经无法飞远,只有任很深的痛楚,如漫天的星辰,细密浓厚的嵌入我生命的每一程。
只有等待,等待在渐行渐远的岁月里愈合。曲高和寡,然而世有稽康,琴瑟无憾。今生能够与你相遇,与你相知,我亦无憾。
找寻心中的徽州美文
我是因为一本书才去徽州的。
书中并未过多地记述山川景色,倒是写了不少风物民俗、文人逸事。我读到胡雪岩从农家子弟变为红顶商人;堂樾的鲍氏父子争死,感化强盗。我读到户部尚书胡富一生两袖清风,无钱建桥;程大位二十年写就《算法统宗》。或许是徽商远走他乡、信义为先的背影,又或者是贞洁烈女的操守与信念,再或者只为山青水秀灰瓦白墙间的一捧清茶,我向往着人杰地灵的徽州。直到,走进她的山水之间。
初到宏村,便住进了民居中。两层的徽式小楼,小院不大,但花木繁茂,布置整洁。几套竹制桌椅随意摆放,屋檐下挂着旧式的煤油灯和纺锤。母亲在房间里洗衣服,门外偶尔有小贩的叫卖声。我推开镂空的窗户,看窗框上的雕花,看屋檐上挂着的鸟笼,看远处起起伏伏的灰色屋顶,看湛蓝的天空中游动的云,看夏日午后的阳光一点一点斑驳了树木的影子。在这一刻,时间是凝固的,我只觉得悠然自得,岁月静好。
然而倘若走到所谓的“景点”附近,就会发现宏村的另一种风格。窄窄的小巷,石板路旁流过潺潺小溪,过不了多久就有一队旅行团浩浩荡荡、匆匆忙忙地挤过身旁。导游的扩音器发出令人烦躁的声音,空气中氤氲着人的汗水和黄山烧饼还有鸭腿的味道。之前在窗边看到的那些古色古香的屋檐下面,倘若不是开了一家餐馆或旅店,就一定在卖歙砚、根雕、茶叶或者徽州毛豆腐。深夜,南湖畔灯火通明,过多的喧闹似乎打破了这里应有的宁静,天上的星星无奈地眨着眼睛。杨柳轻飏,浑浊的湖水里是周围饭店重叠的倒影。浓重的商业气息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北京的南锣鼓巷。
竖日,我们包车前往西递。路上,司机极其熟练而热情地向我们介绍附近的景点,起初令人有些不解,待到他向我们推荐西递客栈的时候,竟也释然了。
若把宏村比作小家碧玉,那么西递可谓大家闺秀了。村中的建筑比宏村的高出许多,高大的八字门楼和长了绿苔的石兽,自有一种时间的威严。坚实的白墙被雨水冲刷出深深浅浅的印痕。村口的走马楼旁,富商胡贯三似乎还在和曹振镛寒暄着;胡文光牌坊前,一群写生的学生打破了历史的寂静。一不小心,便可能闯入一位朝廷重臣的私邸,再走几步,又进了另一徽商的绣房。
有时候我不免有些错愕,这里似乎有一种穿越时间的力量。古老与现代的风格交相辉映,打破历史的宿命,形成怪异的平衡。堂上精致的琉璃灯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取而代之的电灯泡发出耀眼的白光;木雕和画像静静地躺在天井旁,任早已停止的摆钟寂寞地落上灰尘。厢房的木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一个老爷爷抓着一份报纸去寻他的老花镜,狭窄的小屋里竟铺着白色瓷砖,角落里甚至还有一台旧式冰箱。
在村中漫步,发现这里老年人居多,再有就是搞旅游业的人家。格局和形制比宏村大得多,真有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况味。印象最深的是街角的一幢房子,门槛很高,天井下摆着一张旧木桌,上面放着些明信片、小挂件之类的东西,我问坐在左边摇椅上的老爷爷,其中的一本小书多少钱,他瞥了我一眼,干巴巴地说:“那不是我的东西。”我很吃惊,四处张望着。不多时,右边厢房的`门开了,走出了另一位老爷爷,用徽腔问我:“你买什么?”我局促地向左边望去,刚才的那位已然回屋去了。这才终于明白,这座陈旧的堂院被胡氏后人一分为二,而自己却无意间触动了其中泾渭分明那条隐形的界线。忙从中撤了出来,心中怅怅然。
走在光滑的石板路上,看夕阳一点点把马头墙的影子拉长,看人家的灯火一点点地把黑夜点亮,只觉得此地与心目中的徽州风格大相径庭。走回住处“仰高堂”,在古老的客厅中吃过晚饭,左拐右拐到了房间。睡梦中仿佛看见厅堂上的明代画像在向我微笑。
盘恒几日,终于要离开了。回程中,与司机聊天,谈到政府有意将现在的“黄山市”改回原来的“徽州市”,还要进行民意调查。又说若真改了,黄山市大大小小的单位标识和公章等都要跟着作废。望着窗外掠过的风景,我不禁觉得需要改变的又岂止是名称,徽州若缺少了过去的风韵与骨格,眼前的山水也只是惘然。
将时光停驻在过去,我从书本中描摹出一个心中的徽州。我心里的徽州是“亦商亦儒”的徽州,它关乎曾经的正义与坚守。那一座座贞女孝子牌坊就是最好的见证。我心里的徽州是游子的徽州,既是李唐王朝血脉的归宿,也是远走他乡的徽商们永远的故乡。我心里的徽州是文化与商业共同繁荣的徽州,它养育出朱熹、戴震和胡适,荡漾着南湖书院、竹山书院、紫阳书院那一片朗朗的读书声。2000年,西递和宏村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自此,房屋被保护起来了,除了简单的修缮,必须保持原样。村子被围起来了,村民和建筑一同成了被参观的对象。开发商的大力宣传也终于让它们的名字被众人熟知,凡到黄山的游客,必会到此一游。然而,需要保护的仅仅是“物质”吗?
徽州,不仅仅是一群建筑,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象征,一种别致的生命。它是一片确切的土地,以及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它的风格不但应该凝固在徽派三雕的遗迹中,保留在古老的祠堂里,更应该体现在人们的举手投足间,于言传身教中传承在每个徽州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