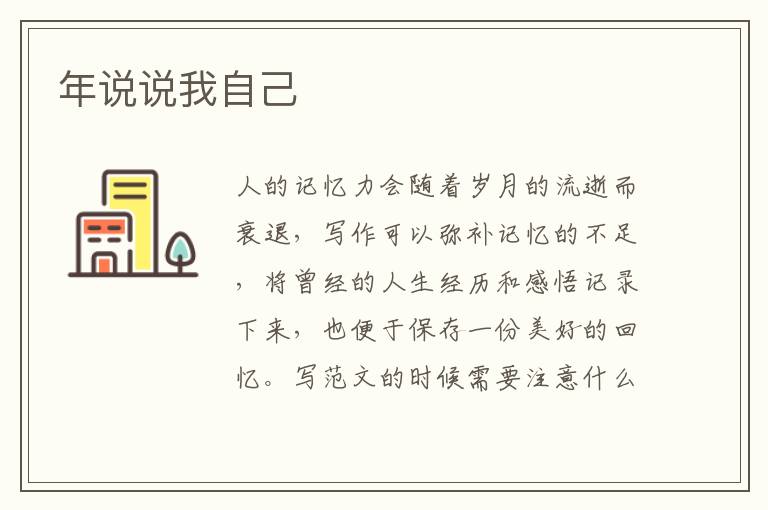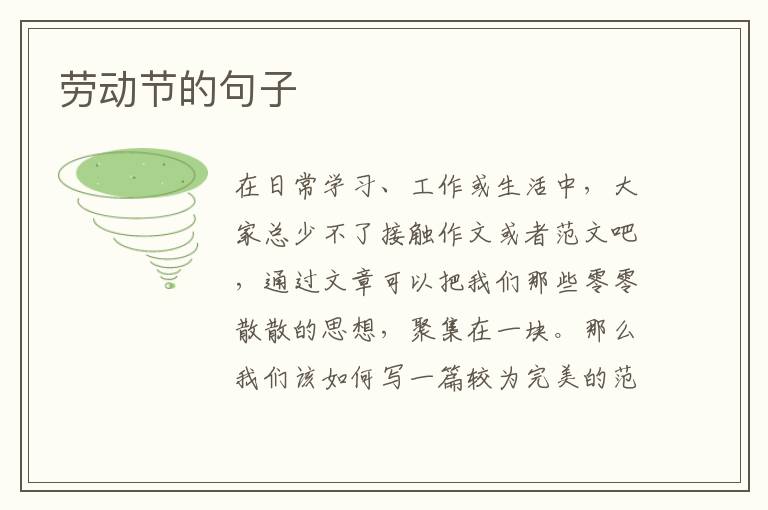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说说锦集200句

不待扬鞭自奋蹄散文
上午课间休息时,我习惯性地回“家”——天中山教师笔会——坐坐,猛然间一串滚动字幕映入眼帘:祝贺:齐云轲同志任天中山教师笔会副会长……
当时我就惊呆了:这怎么可能呢?弄错了吧?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我再次用惊大的双眼去看时,依旧。说真的,心中十分忐忑不安。因为无论是从资历上来说,还是从年龄、职衔、职称等方面来说,与“家”中许多其他成员相比,我都相差甚远。我从去年4月22日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以来,至今尚不足一年,是个新成员,一下子越级升为副会长,确实受之有愧。加入笔会的初衷,是想通过这个平台向大家学习,取长补短,相互交流、鼓励,同时还可以多认识同行中的朋友,工作中的一些疑惑和问题也可以找人请教,于“工”于私都是一件大好事。
加入笔会以后,我基本上是每天都回来坐坐,看看谁又发表了新的文章,又有谁成为新成员了。尤其是在节假日,看了一篇又一篇,往往忘了时间。记得有个周末的晚饭后,我本来说是看一会儿就回去睡觉,谁知竟看得入迷,一直到夜里十一点多,眼睛涩了,才意犹未尽的走了。读着大家的.文字,自己的手也痒痒,便也写起来了。确山县作协副主席牛红丽姐姐说“写作犹如生孩子,十月怀胎才能生,不能早产,但也别太迟”,“早产”的文章先天性不足,“太迟”的写起来又力不从心了。每天若能从繁忙的空中偷摘下一片闲云来,就着一盏灯读读书,写写东西,思考一下人生,确实很必要,也很有意义。
从2010年毕业后来到汝南打拼,至今快五年了。五年里,我在一企业办公室当了一年半的文员,在一民办学校代课了一学期,剩下的时间都在眼下的这所学校里了。五年,在一生中并不算太长,可是它早已把我与汝南紧紧连在了一起。我早把汝南当成了家,汝南的亲友们也一直拿我当自家人。走进笔会,这个小家把我心目中的汝南大家具体化了,可亲可感可爱。在笔会这个家里,亲人很多,虽然许多都没有见过面,但是如果有机会相见的话,肯定会一见如故的,因为我们以文会友,早就已经认识了、熟识了。邱老,作为这个大家庭的户主,抑或说是家长,为了使这个家变得更加温馨,更加和睦,更加生机勃勃、多姿多彩、人丁兴旺,确实没少操心费力。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要承担大家作品的编校,加上他已年近花甲,比我的父亲年龄还大(家父1966年出生,比邱老小10岁),而今还去做这样繁重的事务,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他和笔会里的其他师友一直通过各种途径给予我鼓励和帮助,使我在感动中生发出了更多的动力来继续努力。而现在,又让我担任笔会副会长,更是一种巨大而又伟大的鼓励,惭愧不安之余,也只有阔步直前,用实际行动来感恩了。一路上有你们同行,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幸福。
现在,我的“北风劲”系列长篇历史小说的第一部《廉颇大将军》即将收尾,第二部《李牧大将军》正在准备中。“北风劲”三部曲完成后,我还计划写“东风恶”三部曲,另外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蔡州》也已经酝酿多年了(新蔡、汝南历史上都曾作为蔡州的治所,小说取这个名字,有一定的深意)。我在星光学校时的老校长、书法家牛国玺先生曾经对我说:“小齐,写历史小说可不能走进历史出不来,要借古讽今,反映现实问题,给人以警醒和借鉴。”听后,我很受启发,后来在写《廉颇大将军》时,我刻意在原计划外加了一章《黄鱼岛》。写作计划很大很多,惟愿上苍赐予我足够的生命长度,让我在这条路上走的尽量远一些、从容一些。渴望自己的工作能尽早彻底固定下来,以便把精力往写作上多投入一些。
我想对笔会说:遇上你是我的缘。我想对邱老和其他师友说:真心真意谢谢您(们)!让我们共同努力,使我们共同的家——天中山教师笔会——的明天更美好,大家庭中所有亲人的明天更美好,我们挚爱的教育事业、文艺事业明天更美好!共勉之!
光阴不待人的散文
在我心里,我和他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语言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模样么?迥然不同,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事实上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我高瘦,弱不禁风;他矮而结实。小时候随他去应酬亲朋的酒席,我默不作声地跟在他身后,抑或是跑到他前面很远去,不过待到我们同坐一桌酒席的时候,总会惹人用异样的语言发问:“诶!孩子,你是管他叫爹呢?还是伯伯呢?”每当这时,我端起小碗就跑到屋外去,任由他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嘻嘻哈哈地喝得满面红光。
我时常为眼前有这么一个人在晃悠而怒不可遏,因为人们怪异讥讽的眼神让我脊背针扎一般难受。从孩童开始,我暗下决心有朝一日要远离他,摆脱他带给我噩梦般的感觉。产生离开他的想法,更多的是来自于他对我和大哥、大姐的打骂。他对我们的打骂比及那些牛鬼蛇神还要可恨。他打人时候很是狠毒,毫不留,原形败露,让我想起了“蛇蝎心肠”这样的词语。
就说我五岁那年夏天吧,因为村里的孩子相邀去村后山玩打野战,我们玩到天黑才回家。我回家的时候,满脸污垢,还不小心被荆棘划破了衣衫。我前脚刚跨入家门,他就举起拳头那么粗的竹棍抽在我的腿上,火辣辣的耳光扇得我小脸红肿,头嗡嗡作响,还罚我跪在堂屋里反省,不许吃晚饭。母亲几次抹着眼泪为我求情,他都没有理会。顺着屋里幽暗的煤油灯光,我看到里屋的他,端起酒杯自斟自饮,酒足饭饱的样子,我就恨不得冲上去,给他一锤子,然后绝尘而去。但这时候的我,毫无反抗的能力,只能跪在堂屋里,任眼里充满委屈的泪却不能哭出声来,只有咬咬嘴唇,让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滑入我饥肠辘辘的肠胃。励志中文网
当然,我也有和他和睦相处的时候。偶尔他兴趣高涨,在某一个节日里,趁着西边的晚霞通红,在晒谷坪里教我和大哥舞“板凳龙”(一种地方舞龙戏)。我和大哥举着家里的条凳跟着他飞一般的脚跟,时而变换着我们的姿势,时而看到他回头用严厉的眼神看我一眼。母亲在一般乐哈哈地端茶送水,早早地燃起家里的`炊烟。或许,唯有这时候,人们从远处观望才可以发现这里还有嬉戏的父和子。
但是,欢乐远远没有打骂那么多。偶尔的欢乐无法取缔我对他的仇视,无法逾越我和他之间那道伤痕累累的鸿沟。一直到我初中毕业,我心里都弥漫着忧郁和恨,只要想起他,我就很自然地紧锁了眉头,怒目圆瞪。我想鼓起勇气和他大干一场,战胜他一次,搓搓他的威风,但我想想自己弱不禁风的身子,我只有一忍再忍,不得不在他面前像泄了气的皮球,任由他打骂。
我初中毕业了,考取了地方中等专业学校,在计划经济末年,这意味着走向有计划的学习、工作、生活。我以为,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他,他会高兴,会给予我一丁点鼓励。可是,他不仅没有露出一丝笑容,反而和母亲为了我读书的费用而大打出手。他糟透了,一边怒骂我是没有良心的孩子,一边数落着哭泣的母亲。后来,母亲东拼西借地为我凑齐了学费,我才得以登上去学校的长途汽车。直到我离开家的那一刻,他依然没有自责的意思,没有想要和我说一句道别的话。
那一回,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坏到了极点。我几乎不再和他说话,更不要说喊他“爹”!每次放假回家,他看着我逐渐长成大人的模样,也不再对着我咆哮怒吼,但也不搭不理。我们就这样形同陌路。
当我完成学业后,因为预期的工作有变,我选择了远离家乡,极少回家和家人团圆,就是一个问候的电话,如果是母亲接听的话,我还会多聊几句,如果我听到他的声音,我会励志名言名人名言“啪”的一声毫不犹豫地挂断。这时候,我和他说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离家闯荡的日子,虽然我很少回家,但有关他的消息时不时的传到我的耳中。他学会了一些粗糙的木工技艺,经常到附近的村庄去做活,和母亲的关系也稍微融洽了一些,也时常叨念出门在外的继子女们,虽然都不是他亲生的孩子,但毕竟跟随了好些年,看着一个个长大离开,他也有割舍不下的。还有,他的父母相继过世,他只身前往,没有他的孩子去给他的父母披麻戴孝。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也先他而去,他时常在我母亲面前叨念孤独和遗憾,感觉连个说话唠嗑的地也没有。
不过,我依然是我,一个和他互不相干的我。我知道,他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可以自理,经常赚点小钱,日子一定可以过得如意一些。我常常想,孤独相对于酗酒、暴躁的人来讲又算得了什么呢?孤独相对于他那些毒辣的打骂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孤独,他叨念儿女,他也有割舍不了的情感?这些和我有关系吗?我能够算是他的儿子吗?
我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对他动了一丝恻隐之心的,大概是从我的女儿学会喊爸爸开始的吧。我自己成了一位父亲,我才可以体会到一个大男人需要什么样的情感。我隔三差五地回去探望一下他和母亲,也会买一些烟酒给他,节日里还会和大哥大姐相约去吃一回团圆饭。不管怎样,我还没有和他打破僵局。我不会和他无话不说,不会亲密无间,不会“酒逢知己千杯少”。
岁月如梭,在平平淡淡、忙忙碌碌中,他老了,我的小家也慢慢不再漂泊,还在家乡县城买了房,安顿下了。近几年,他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可以听到母亲打来电话说他这不好,那不行的,连坐公交车去亲朋家里都呕吐不止,昏头转向地跌跌撞撞。我不觉悲由心生,又觉得他罪有应得。这是我多少年前就想要得到的结果啊,这是我梦寐以求要击败他的样子啊。我觉得他应该祈求我,即使不祈求也收起他凶神恶煞的脾气,然后跑过来对我说一连串“对不起”,或者是寻求我原谅他过去所作所为的话。
那天,他从朋友家喝完喜宴,回家后突发脑溢血。母亲打电话要我赶快送他去医院急救。我匆忙坐上回老家的汽车,还在路上,母亲就把他的噩耗告诉了我,说他已经落了气。我狂奔着冲到他的床前,抱着他渐渐僵硬的身子,看着他青紫的脸,我嚎啕大哭。我冲着他喊了无数声“爹”,他再也没有应我。我猛然感觉自己失去了仇恨的对手,就如侠客“独孤求败”一样再也找不到失败的理由,感觉那样寂寞失落,感觉天崩地裂。
他毒打我的手劲到哪里去了?他那暴躁的脾气哪里去了?我一次又一次抓住他枯槁般的手,让他再锤我几下。我无法相信,他和我的恩恩怨怨还未了结就真的老去。
他就这么,连一句道别的话都没有说就老去。到死的那一刻都没有听到我原谅他的话,我再也等不到他对我说一个“”字。我明白,无情的岁月都会把人送到某一个终结点,都会让人善始善终。想到这些,我突然对他那么难以割舍,胸口绞痛,不愿他真的离我而去。毕竟在我记忆的海里,还萦绕着母亲教诲我的一句话:“不管你的继父如何待你,不管你被他毒打过多少回,你都应该觉得你很幸运,因为有了他,你才得以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长大成人。”
杏蕾俏枝自呢喃散文
还是这样的习惯,只要天气允许便每天到郊野遛弯儿。这几天受邀到朋友家小住,惯常的作息被打乱,归家后的一大早儿,便迫不及待的奔向了郊野。几天不见,路旁的柳丝嫩黄婀娜,高高的杨树穗毛吊垂;赤黄的小径绿草镶边,开放的桃花红粉灼灼;远山的青黛已经显现。那无尽的绿意,嵌在大地藏在草丛俏在树梢,一种远看有近似无的虚幻飘渺而来。
前方的杏树林跳跃着粉红的色彩,呜呜泱泱如流霞当空。每当桃花吐艳的时侯正是杏蕾初绽的当口。走近了细瞧,那密匝的杏蕾挂满了枝条,红红的小疙瘩诱人眼球,咧开的花蕾嘴沁着白芯,干枝花蕾一目了然,四边芳邻桃红柳绿,好一派盎然的春意郊野。
瞅着杏蕾,不觉间想起了南方的.腊梅,如果摆在一起的话,活脱脱的姊妹相。北方也有杏梅一说,只不过是南北品种的差异罢了。人们说“好花还得绿叶扶”,梅花反其道而行之,得到了“干枝梅”的赞誉,杏花傲美自俏春何须绿叶来帮衬也果真如此。几声喳喳的叫声传来,一对花喜鹊落在杏树上不时地撅着尾巴,一幅喜鹊登梅图天作般跃入眼帘。
真赞叹这大地的收藏,但到春醒,把自己的宝贝都抖落出来了,造就了满目春光,也精心的妆扮了自己。这小小的杏蕾,是藏在杏树心里的秘密,它不声不响地吸吮着母体大地的乳汁,挨着那冬去春来的时刻。看着桃红柳绿它的心里着急,看着小草吐绿它的心里憋屈,今年的气候偏冷,延展了它的身躯。亮相的时刻终于来了。它是自然赋予的生命,它是草木一秋的先行者,它以自己的娇小艳丽参与嬗变的升华,同样在讲着春天的故事。
杏蕾骄傲地伸出了探春的脑瓜儿,环视着挤在一起的姊妹兄弟。它们靓丽新奇,诠释出开花、结果的第一步。小小的花蕾自奴出起始,就已经担负起繁衍后代的义务。它的蕾芯里包含着雄蕊雌蕊,还有美丽的花瓣,它们相拥着,忍耐着,企盼着开放的时刻。
也许就在明天或许后天,杏蕾将渐次的开放。它的色彩会越发的艳丽,它的形态会越发的诱人,它的暗香会越发的悠远。对人们的欣赏赞赏还有惊艳,这本不是杏花的本意,它的内心在盼望着那些飞舞的精灵。果不其然,看到了它们身影,听到了它们声音,它们如约守时的来到了。“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那些黄色的黑色的,大个的小不点的蜜蜂,缠绵于旁边的桃花丛中,还有的爬落在杏蕾上悄悄地在对话,想必那初蕾的花蜜更香甜,初绽的鲜花更迷人。采蜜授粉,你帮了我,我助了你,没谁安排,自然天成,自然界里的那些知与不知就是这样的神奇。
杏蕾开花了,花开凋零了,凋零坐果了。米粒般大小的青果头顶着干枯的花蕾,稍许长大还在顶着,那么虔诚的顶在头上。这是对母体的感恩,还是对花蕾的不离不弃,想来兼而有之。不走近看不到,不思想不经意,这与“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殊途同归大同小异。
小小花蕾孕育成熟,生在天地间接受风云雨露;长在骄阳下与树叶儿为伍。几许风雨至,几多迎酷暑,绿了大了,青了黄了,经历自然的洗礼,直到羞怯的在树叶中把自己的本像露出。
杏蕾天生就知道自己所走的路,花开花落那是上苍赋予的方圆,成长道路上的坎坷就是历练,初始的生命本就是成熟的本源。
草木一秋知短暂,人生一世度春秋,短暂春秋同轮回,悟世道理共根由。
光阴经典散文
冬日,被窝的魅力总是演绎到淋漓尽致,以至于到了日晒三竿,我才极不情愿的睁开双眼。拉开窗帘,拥着炉火,看着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床边,静静感受暖暖的温度。
放一曲轻声哼唱的乡间小调,记忆随着曲调慢慢展开,那往事似一条长满青苔的小径,我独自徜徉,品尝着记忆的果实,那些酸甜苦辣都是我多年来的珍藏。
白落梅说:最美的风景,总是在远方。这像是对光阴的约定,为了这个约定,我试图走出生命中那扇小小幽窗,邂逅世间万千风物。幸好,时光宽容待我,许我静守满目风景,纵使流年辗转,于我,终究是恩泽。
等待、期盼,邂逅一场重逢。人心最初的苍老,注定受尽冷落和委屈。那场无关风月的相遇,那段有缘无分的重逢,终究只是一个未完结的故事,孰是孰非,又何必在意。
诚然,许多故事原本就不该有结局,像是纸上慢慢悠悠游走的`笔墨,一笔一划,极尽闲情逸致,可往往还没等到落下署名,或许那人就已转身不见。那一条无限延伸的思绪,那一场繁花似锦的梦境,我们不再奢求结局,亦不再苦苦寻觅,只是沉溺在了希望和幻想,从此开始了当年过往。
都说,我们都像是台上的戏子,起承转合,一出又一出,娓娓落下帷幕。记忆的斑驳中,故事仍就交替上演,唱着爱恨情仇,演着别离生死。直到历尽艰辛,我们才醒悟:所谓欲言又止,往往是咽下了最想说的话,最真挚的情,而那临别一眼像是隔着千山万水,却又无法言说。
也曾想就这般去流浪,哼着乡音,怀揣梦想,可到底舍不下这般美好的青山月色。屋檐下余光昏黄,河水拍打着岸边的青石,那曲调悠悠回荡,手中的书篇上隔着岁月悠长,恍然间却觉得黯黯生香。光是想想,就已沉醉。
思绪万千,我却从未理出头绪,呆坐了半日,抬起头,窗外飘起了小雪,这是这个冬季的第一场雪,来的这般突然,却又像久别重逢的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