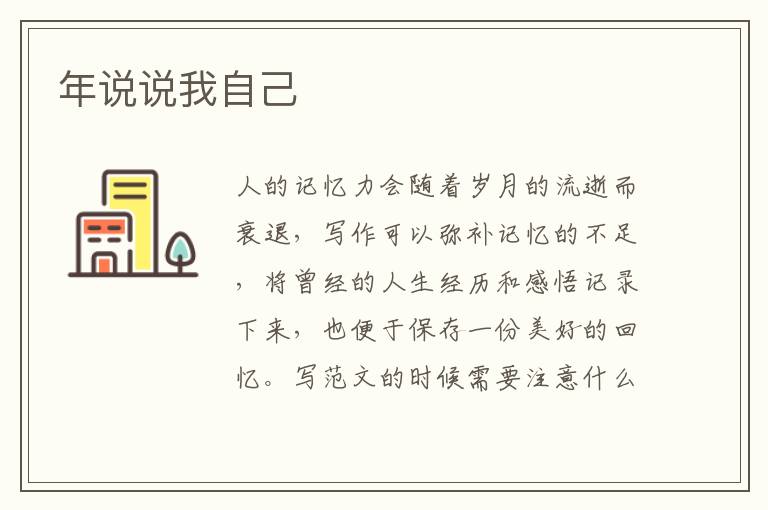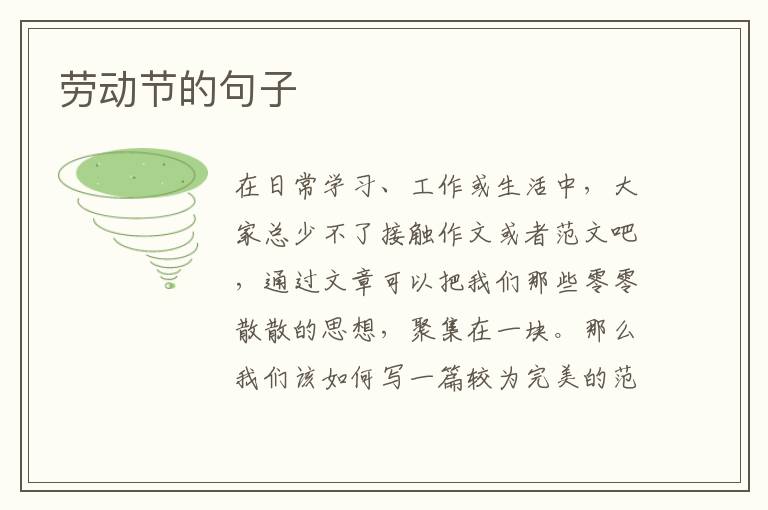关雎描写淑女的句子合集50句

《关雎》中的淑女形象
“淑女”是《诗经》中最为重要的女性形象之一,在关雎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关雎》是《诗经》的压卷之作。自先秦起,《论语.八佾篇》便有记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上博简《诗论》则从“色”、“礼”等方向偏重论析了《关雎》的诗本义。及至汉代,《诗经》初步奠定经学地位,《关雎》一篇更愈发受到学界从诗教、乐教和女教等多重维度的关注。两宋时期,苏辙、朱熹等学者加注《诗集传》、《诗序辨说》,形成了长期与尊序派对峙的废序之声,并分别从“情”、“理”等角度为《诗》添注。因而两千多年来,有关《关雎》释义的说法可谓众说纷纭。而诗中的“窈窕淑女”的形象,也因被历代学者延引为理想女性的典型而盛传于世,千年不衰。
本文就将从先秦、汉、宋的典型注本出发,结合历代审美标准,对《关雎》中“淑女”这一对象的内涵及其形象作简要分析。
【第1句】:“淑女”形象的内涵所指
古人对《关雎》“窈窕淑女”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以后妃为代表的贤德女子;二是指贤人。在封建诗教的背景下,《关雎》一诗的教化作用一直盛于其抒情作用。及至近现代,视其为纯粹表达男女恋慕的情爱诗的说法方才逐渐兴起。
(一)后妃说
先秦《毛诗序》最早记载:“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始指称《关雎》中的“窈窕淑女”为可以“风天下”的后妃。而此种说法也在后世汉唐学者间得到了最多附会,成为学界认可的主流说法。
与近现代学者从“诗本义”的角度,偏重理解《关雎》中的抒情价值不同,《诗序》主要采用陈诗义、用诗义与赋诗义等手法对《诗经》进行理解,解读的视角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自春秋时期起,孔子即赋予《关雎》一篇以极高评价,认为其在诗歌与音乐方面都建树斐然。《韩诗外传》卷五中记载,子夏曾询问夫子,《关雎》何以为《国风》之首,夫子回答,盖因《关雎》之道为“天地之基”,“王道之源”,《六经之策》悉皆“取之乎《关雎》”,可见《关雎》“正人伦而立纲常”的教化作用。而西汉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即将孔子命定的官学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奉为教化正典,《诗经》举足轻重的经学地位得以稳固建立。诗学礼教,讲求“以礼节情”,以道德为主要命题,故尔《关雎》不是单纯的爱情诗歌、而是美贵族婚姻的教化范本的'解读基调得以确立和流传。
而诗学发展至宋代,依据先前《诗大序》的猜测①,学者们又对“淑女”所指称的后妃形象进行了具体对应的阐释,认为这位德仪天下的贤妃即为周文王之妃大姒。欧阳修称谓此诗曰,“述文王大姒为好匹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而朱熹亦在《诗集传》中进一步明确,《周南.关雎》“女者……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将“淑女”形象进一步具体化。这与毛诗序《二南后妃夫人说》中认为《关雎》只是赞颂“周家世有妇德,而非专美大姒”②的论点是截然不同的。
(二)贤人说
求贤说并不是《关雎》解读中的主要说法,但却是历代注本中都有所体现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声音。《韩诗》中将“君子好逑”直接记载为“君子好仇”,而学界以闻一多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这与《周南.兔置》中:“肃肃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肃肃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中的“好仇”是同一个词。而《兔置》中的“好仇”意为“腹心”,是指公侯的知交心腹,在职能上与武夫相对,因此“好仇”所实际指代的对象是公侯身边的文臣或是贤人。而上博简《诗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时期抄本《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种皆有重要批注,称《诗经》是“(以)色俞(喻)于(礼)”,认为诗歌中思色即是思礼,“淑女”之为女色,实际是指代贤臣,这种手法与楚辞中以“香草美人”隐喻名士大夫的用法是同理的。因此《关雎》一篇并非爱情诗,实际为君王求贤诗,而“淑女”则是令君王梦寐以求的治世贤人。
《礼记.曾子问》中记载,“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肆亲也”,即婚姻嫁娶举行仪式时,现场是禁止奏乐的,这与一些学人认为《关雎》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指君王求爱于有贤德品行的淑女,先以琴瑟向其示好,再以钟鼓明媒正娶的猜想相悖。再者,“钟鼓”之乐在古时是“大乐”,并不用于婚丧嫁娶之事,而只有宴宾、祭祀等重要场合才会出现。参见《周礼.乐礼》“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而这种说法也与君王礼敬贤人的解释相吻合。
【第2句】:“淑女”之德
由于中国古代文坛多将《毛诗序》中的“后妃之德”视为“淑女”这一理想女性的重要标签,认为“窈窕”用以描述其形容风貌,而“淑”则意在赞誉其德行贞操,因而学界对于“淑”字的阐释也可谓众说纷纭。
《说文解字》记载,“淑,清湛也”,而“淑女”则可引申为如水般清澈美好、温柔娴静的女子,在德行方面需有“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的至真至纯之性。而这与先秦时期社会对于后妃的期许一致。人们认为夫妇之间应相敬如宾,有礼有节,而佳偶则必须符合温柔敦厚,谦恭贤惠的标准,对于女子而言,知书或可不必,然而答礼一定要之。
而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则对“淑”字的标准给予了更为明确的注释。他称,“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能事君主、达到举案齐眉、“夫妇和谐”的境界,是为其一;忠贞美好,能够做到上行下效,为天下男女表率,是为其二;时刻以为君王分忧、为社稷求贤为己任,克己守礼、礼贤下士,恪敬职守,将后宫操持有度,是为其三。从这孔颖达的观点看来,古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不仅其自身需要具备质朴、善良、美好的品性,对外还需有“辅助之德”。与之相同的观点还有《诗序》中,“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一说,认为贤德的淑女能够“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真正做到以德事人,而不是以色事人。这也不失为是孔子所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要义。 除此以外,笔者亦发现,古代对于达官显人的妻子的诰封亦存在“淑人”一说。学界一致认可此处的“淑”为“善良”之意,与相貌无关,而专指品行。坊间亦曾一度有“后妃求贤”之说,认为《关雎》中的“淑”字指称的是后妃为君王广募贤娴,敦厚无妒之德。后被否认,认为只是郑笺误读《诗序》中“忧在进贤”一句所引发的误会。“忧在进贤”,本义仍是指后妃心系黎民苍生之贤。
最后,南宋的朱熹在《诗集传》中综合前人的多种观点,对“淑女之德”给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称:“盖德如雎鸠,挚而有别,则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见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侧,琴瑟钟鼓,极其哀乐而皆不过其则焉”。诗教言传,讲求“发乎情而止乎礼”,朱子认为这是对于后妃之德最恰当的评价。雎鸠之德在于“挚而有别”,而淑女之德亦是如此。《关雎》虽以男子追求梦寐以求的女子的情爱诗的面目示人,但隐喻的是夫妇之间琴瑟和谐的关系。而与古时女子而言,出嫁从夫,如何事夫才是她们德行修养中最重要的课题――在父母家中,则“志在女红之事”;出配君子,则“辅佐君子求贤审官”、且“内有进贤之志,却无险陂私谒之心”③,和乐贞静、宜室宜家。诗人以“关雎”的形象作比,也正是暗示,只有德如关雎,能做到“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④的贤淑女子,才可配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君王佳偶,即淑女的原型――贵族婚姻中的后妃形象。
【第3句】:“淑女”之貌
不同于“淑”字指称女子善良品性的共识,历朝历代的注本中对于“窈窕”的注解颇为模糊。“窈窕”,形容的是女子的体态风流之美,然而具体形容如何,却在各个朝代的不同审美判准下发生了分歧。
先秦时期的《毛诗序》将其注释为“幽闲贞静”,此时解读侧重的是对淑女形态举止的描写。恰如《蒹葭》中在水一方的伊人一般,“淑女”在水边静静独坐,气质矜持闲静,这样的解读深合儒家“敏于言而慎于形”的标准,“窈窕淑女”即是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礼教中人。而其余同时代的注本释义则相对宽泛――《集疏》中将“窈窕”解释为“好貌”,与《鲁说》一致,泛指女子貌美。而《毛诗正义》记载“谓淑女所居之宫窈窕然”,认为“窈窕”的描写对象是淑女所居住的处所,“窈窕淑女”指的是居住在幽闲清静的环境中品德美好的女子。而《方言》中则综合才貌两方面,统称其曰“美心曰窈,美状曰窕”。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对于“淑女”外貌特征的考据也仅能止于“貌美”的定义。
发生分歧的焦点是后世关于“貌美”的不同理解。首先,依据先秦时期的审美风格,我们不难猜测出,体态丰满、高大健康是当时人们评价女子貌美的重要标准,如《硕人》中描述的“硕人其颀”;而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描写看来,明眸善睐,开朗灵秀,亦可视为当时女子“貌美”的依据。而作为最接近《关雎》创作年代的时期,相较后世的一些流变,先秦时期对“理想女性”的审美应当更接近“淑女”形象的本来面貌。
然而,随着审美风尚的改变,后世对于“窈窕”二字的理解也发生了迁移。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瘦”,逐渐发展为汉代飞燕合德一般金盘起舞的“轻”;从魏晋南北朝广袖飘飘、遗世独立的风神俊秀,及至唐代珠圆玉润的体貌与相对宽松的衣饰,再至两宋理学兴起后对女子样貌古拙质朴、雅致清秀的审美判准……“淑女”这一理想女性的形象一直在不断变化。而在明清的坊间小说中,甚至出现了对“淑女形象”更为大胆、也更富想象力的描画。魏子安所撰《花月痕》的第二十一回里写道:“《古今注》文王掣平头髻,昭王制双裙髻。又《妆台记》文王于头上加翠翘,傅之铅粉,其髻高,名曰凤髻……这样看来,文王自是千古第一风流的人,所以《关雎》为全诗之始”,女眷丫鬟之间大胆猜测文王所好的“窈窕淑女”是一位梳高髻、掣发钗的美人,这也是时代审美所赋予“淑女”形象的不同魅力、不同风姿。
【第4句】:结语
“窈窕淑女”这一形象是《关雎》一篇、乃至整部《诗经》中至关重要的意象。与其形貌之美相比,历代注释中更为统【第1句】:也更为突出的是其“德行之美”,即以后妃为代表的女子身上所具有的善良、温厚、贤德的道化礼教。而近现代以来,人们对于《关雎》的解读则又突破了以上所探讨的教化标准,向其内在的抒情性不断生发。因而对于“淑女”形象及其主题意蕴的讨论仍将作为《诗经》中一个永恒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被发展、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