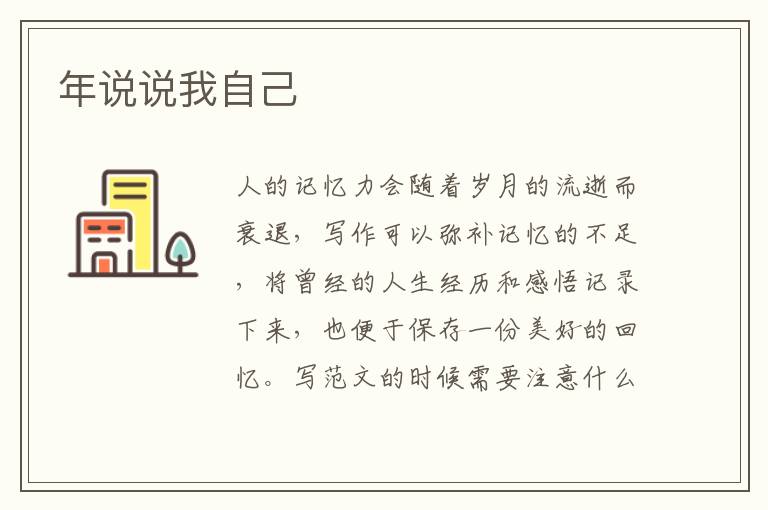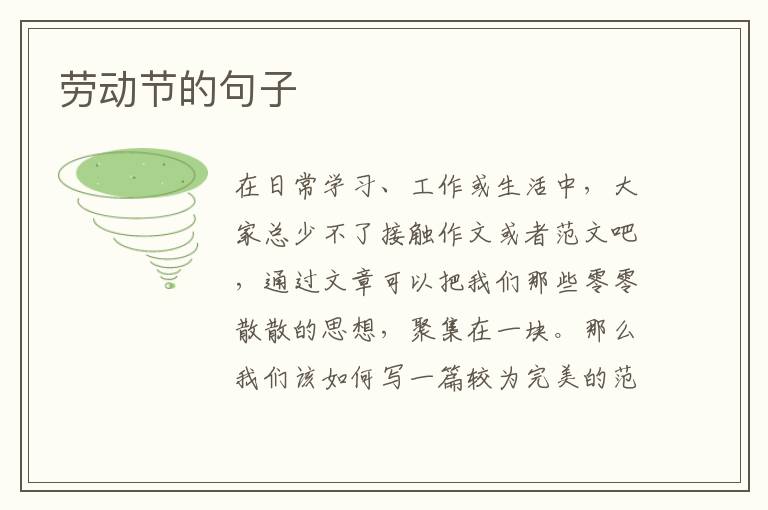晒麦子发个朋友圈的说说汇集70条

晒麦子散文
我回到老家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可父亲早已把麦粒子完全摊开,远远看去如同金灿灿的一片湖泊,木锨的痕迹使麦子像微风拂过的湖面,皱起道道波纹,走近了细看,一垄一垄的,又像刚刚收割的麦田。
麦子就晒在大门前,我家门前是村里修的水泥道,一到收获季节,就自然成了晒麦场。
父亲正在大门里边的简易钢丝床上躺着休息,听到我的声音,他翻身坐了起来,动作很麻利,父亲并不瘦,父亲的皮肤晒成了棕红颜色,父亲的头发依然是黑白相间,父亲的胡子依然那么稀,有点长,该刮胡子了——我一眼看到的,就这些内容。
我递给他一根烟,点燃:“这么早就摊开了,不是说等我家回来吗?”
“这点小活,没事,闲着也是闲着。”他吸着烟,淡淡地说:“家去吧,你娘在屋里。”
我进屋,娘正收拾着碗筷,父亲也跟着进了屋。
父亲话不多,即使在他的儿女面前,他最多的时候也只是静静地坐着,抽烟,喝茶,听我们说话。
平常我和兄妹给老家打电话,父亲也总是把电话交给我娘,娘为此不止一次地叨叨他:“你接啊,你儿子和闺女的电话怎么也不接?”
父亲不反驳,坐在电话旁边,听电话里传过来的儿女的声音,捕捉着电话里的所有内容。
“现在收麦根本不用你牵挂,你嫂能帮忙,再说几乎不用人,一个电话,人家就把麦粒子送到家门口了。”
确实,收麦和以前相比简单了许多,但再简单,四五亩的麦子眼看熟在地里,收不回家来总是心慌——收麦的那几天,天气常变,就怕刮风下雨,只有收到家里,才能够把心妥妥地安放在肚子里。
大约四五年前,我们兄弟就劝父亲不要种地了,毕竟七十多的人了,也该歇歇了,可爹娘就是不愿意:“庄稼人不种地,那还算什么庄稼人!没事,累不着,你们只管忙你们的事。”
我知道,地是父亲的命,他离开土地会觉得活着便也没了意思。我们劝说不了,只能退一步让他们减一点,少种点,也算那么个意思。可父亲一再说:“没事儿,再种一年吧,真干不动了就不种了。”就这样一拖再拖,地不仅没有减少,听娘说,爹还闲着没事沟沿子河边子的开了不少荒,一到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父亲的粮食。唉!
爹从来没说过什么,倒是娘常在一边念叨:“种就种吧,真让他闲着肯定憋出病来,人没有累死的,都是病死的,一人一个命。”
其实,有句话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知道,爹娘不想增加我们的负担。“能干一天,就干一天,你们也都不容易,里里外外,花钱的地方多的是,买房子买车的,还不知道孩子最后分到哪里去,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说过娘多次:“快八十的人了,别操那么多心了,咱村里像你们一样年纪的,还有种地的吗?儿孙有儿孙的命,花钱的地方再多,你们该花的也得花。”可说归说,答应归答应,地该种的还在种。
喝了两壶茶,我走出大门,拿起木锨,翻一遍麦子。
我学着爹的样子,用木锨顺着一边把麦子翻起,原来拱起的薄薄的麦垄,便露出了青灰色的水泥地,木锨刮过地面,麦粒刷刷地响,木锨与水泥地磨擦发出钝钝的噪音,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旁边,他提醒着我把木锨贴紧地面,麦子厚的地方要把木锨立起来,要想法把麦子摊得均匀一些,我似乎不得要领,看我笨拙的样子,他一边笑我什么也不会干,一边就要我手中的木锨。
“没事儿,你歇歇吧,我慢慢就学会了,你不让我干,我什么时候也学不会啊。”
我让他到大门里面休息,可他不动,弓着驼了的背,站在旁边看我干。
阳光像一根根刺,刺得我头皮发麻,浑身发痒,汗水滴滴答答流了下来,麦粒子被太阳晒得发烫,我光着的脚板子,一开始的时候很舒服,但时间长了就痒得难受。但我终于翻完了一遍,我撩起汗衫胡乱地擦了擦脸,然后脱下来,擦了擦胳膊和手,顺手一拧,汗衫子竟然拧出浑浊的汗水来。
娘把茶壶端到了大门里,我和父亲对坐着抽烟——二十年前,父亲查出了冠心病,后来又有严重的胆囊炎并做了手术,我们曾严肃地劝他不要抽烟,他也很听话地戒了一阵子,但后来又偷偷摸摸地抽了起来,后来我也慢慢想开了,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抽了一辈子烟了,你再强迫他戒烟,他自己会不高兴,有时会因此连饭都没心劲吃,既然这样,为什么非要让他戒烟呢?人老了,为什么非要逆着他的心,去做那些听起来对他好的事呢?爱抽就抽吧,只要他高兴,抽烟不一定会生病,但不抽烟他很可能会生病的!我不再劝他戒烟,每次回家的时候,还会给他带上一条两条的纸烟——这毕竟比他卷的老旱烟要平和一些啊。
父亲原本话就不多,我们爷俩对坐着喝茶,抽烟,父亲时而会起来给圈里的羊添添草,我呢,就起来去翻一翻麦子。父亲说这样毒的太阳,不用翻麦子也会晒得干干的,母亲倒不阻止我。“他愿意翻就翻去呗,你们爷俩坐着也是光瞎(本地土话,浪费的意思)烟卷子。”
我笑了笑,爷俩个面对面坐着抽烟就挺好,谁说一定要叨叨叨叨地说个没完呢,我很享受和父亲对面坐着抽烟的时光,我想父亲也是,不然,几乎在家呆不住的父亲,今天为什么就没有下地呢。
我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子,索性连鞋都没穿,光着大脚丫子翻着麦子,不时有过往的邻居打着招呼,开着玩笑:“哟,会干活吗?跑老家来找罪受啊?”我也和他们开着玩笑哈哈着。“大学生,这顶着太阳的滋味,比不上你们坐办公室吧?”“还大学生呢,都老成大学生的爹了……”村里年轻人我基本不认识,能开玩笑的几乎都是比我大一点的同代人。
邻居们和娘聊着闲话,他们的对话时时钻进我的耳朵里。我这时才明白娘的小心眼子:她并不在意我干多少活儿,她很享受的,是让来来往往的邻居看到他的小儿子回家干活,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当爹娘的更自豪——在外工作的儿子虽然不会干活,但他总挂着这个家,挂着家里忙碌的老爹老娘,这不,一到农忙季节又跑家来了。
我愿意满足娘这小小的虚荣心,今天这光着膀子赤着大脚丫板子的'不是什么老师,只是儿子,是眼前这老头老太太的儿子。
太阳落山的时候,父亲说晒好了,可以收仓了。
我们先是把麦子堆成堆,然后,用水桶挑到存粮食的屋里——说是水桶,其实要比普通的水桶要大得多,是那种装乳胶漆的大圆桶。母亲告诉我用三轮车推到屋门口,然后再提到屋里去。“那样够费事的,直接挑吧。”我以为运这堆粮食费不多大劲,豪气地说。
父亲没说话,于是我们装好水桶,开始运。在屋门口,父亲拿起秤,我不解:“怎么,还用过秤?”
“称一下有个数,看哪块地亩产高,心里明白。”母亲也在旁边帮腔:“忙了一季子,看看能打多少麦子,心里亮堂。”
我实在不理解他们的郑重其事,不禁暗自好笑:值得吗?不就这一堆麦子么,能值几个钱?但看着父母认真到庄重的样子,我没再说话,既然他们乐意,那就随他们的心意吧。
“大桶43斤,小桶38斤,按40斤平均吧。”父亲一边念叨,一边在算盘上记下数字。
运了几趟之后,我才觉得这活不好干,我先是两手提桶,提了几趟后换成担子挑,麦堆消了还没一半呢,胳膊和肩膀又酸又胀,父亲要替我挑,我在家里怎么能够让七十多岁的他来挑呢,我不停地擦汗,不停地喝水,借机休息一会喘几口气儿,我不停地问着多少桶了有一半了吗?我内心真盼着麦子能够少一点,早一点干完好好地休息。
“庄稼人忙了一季就盼着这一天呢,越累越高兴,老二,你不用慌,咱歇息着干,多喝点水。”
我数着从麦堆到屋门的步数,单趟16步,我记着挑了多少桶,我看着麦堆消了多少,当麦堆终于消灭的时候,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像刑满释放的囚犯一样逃离了苦刑——真的,当时我就这么想的,有个邻居大哥看我狼狈的样子,取笑我说:“不跟坐办公室喝大茶轻松吧。”我用胳膊擦拭着满脸的汗,气喘吁吁地说:“说真话,这活一小时给我两百块钱,我也坚决不干。”
“哈哈,还两百块钱呢,一分钱不给你,你这不也是大包小包又买东西又拿钱地回来了吗?”
“嘿嘿,那没法子,谁让自己当儿子呢。”
我从小就害怕地里的农活,尤其害怕割麦子刨红薯,工作以后又不大接触农活,所以,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实的。
可说归说,既然父母都还种着地,尽管内心很害怕,尽管内心特别不愿意干,我也必须回家来干一点,好像干那么一点,我的心才能安稳下来。
“一共56桶,56乘以40,2240斤,比那块地好一点,亩产能达到1100斤。”父亲把算盘打得哗哗响,母亲听得津津有味。
在父母算账的同时,我也在偷偷地算另一笔账:56桶那就是28个来回,一个来回是32步,28个来回就是896步,如果每步按照70厘米计算,那么,我一共走了627米多一点,而在这行走的过程中,我是挑着(提着)80斤的麦子,天呢,平时哪有这样的运动量,难怪胳膊疼得不敢抬肩膀不敢碰了啊!
“怎么样,不轻省吧?”父亲难得笑了笑。
“嗯,是不轻省……”我努力挤出轻松的神情。
累也不能说累啊,父亲马上就奔八十的人了,还天天干着农活,我一年回家来干个一回两回的,又怎么好意思说累呢。
“现在麦子什么价啊?”
“粮食价格一直在落,现在也就一块一毛五六吧。”
“按一块一毛六算,两块地共收不到五千斤,这一季麦子下来还不到六千元,这还不包括浇水、上肥和种子呢,至于人的力气,老百姓种地向来是不算人工的。”我嘴里嘀咕着数字,“不到我一个月的工资。”但我绝对不会说出来,我知道,父母在意收多少麦子,当然也在意卖多少钱,可这一桶一桶的麦子,又不完全是钱所能替代的,它似乎包括了庄稼人的期待荣誉和尊严,他们对麦子的感情,我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但我必须得接受并从内心里尊重他们的这种感情:从麦子下种,到出苗,到浇水,到施肥,到打药,到收割,然后再到最后的归仓,这些麦粒子里,就藏着他们有期待有焦虑有喜悦有忧伤的日子……
打扫好之后,天也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和父亲面对面坐着,四个小菜,我喝了多半瓶白酒,父亲不紧不慢地喝了三罐青岛啤酒,看得出来,听着母亲的絮叨,看着归仓的麦子,父亲喝得很高兴……
晒麦子的女人诗歌
今天,阳光正好
雨失去了消息
她摊开来自大地的荡漾
摊开麦香落地的孤独
天籁般的碰撞,如水
清澈的呼叫
此刻的爱,在如火的六月
显得十分凌乱
汗水的光芒,已忘了她
一生被映照的卑微与悲苦
泥沙俱下的生活
柔韧,平淡,甚至比时间
更为深刻,坚强
她想到了火的热烈,想到了
麦田里的灰烬
夜还是温热的'
她感到了上帝微笑
拒绝泪水里的平静
她看到那些危险的鸟了
站在风里,不知所措
她相信此刻的天空
是辽阔的
宛如她的心境
又见麦子黄散文
习惯了三点一线的生活模式,平日很少走出校园,夏日与家人出去游玩,田野到处是金灿灿的一片,这才意识到:麦子黄了!夏收就要到了!
看到这满眼的金黄,不由想起了童年夏收季节的诸多忘事,重新找回了曾经属于自己的天真与幼稚。记得那时候,临近夏收的时候,生产队的社员们,按照队长的安排,从集市上早早买回镰刀、麦叉,簸箕、筛子等夏收农具,修葺好麦场边上的土坯房,用白灰写上“龙口夺食”此类的标语,迎接这一年一度的收获,也在与老天爷争夺这全队男女老少赖以生存的口粮。
等到开镰收割的时候,我们农村的小学生,也自然放了忙假,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长长的队伍,带着红领巾,背着装上凉开水的玻璃瓶,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顶着炎炎烈日,走向一块又一块收割完毕的麦田,去捡拾遗落的麦子,做到“颗粒归仓”。有时候,为了完成任务,会趁老师不注意,在旋成一堆的麦捆中抽出几枝,或是在运送麦子的马车或者牛车的'后面偷上一把,不过这要冒很大风险,要是有“叛徒”告密的话,准得被老师批评,要么被赶车的发现,也许会像拉车的牲口一样,挨上几鞭子,但是毕竟很轻。
进入了碾打的阶段,地里遗留的麦子,也被扫荡一空,我们就没什么事情了。于是就在麦场上尽情的追逐撵打、捣乱,没少被大人们呵斥。最好玩的就是捉迷藏了,时而爬上高大的麦垛,时而在麦垛下面,像小老鼠一样掏一个洞,洞口用麦子堵住,这种藏法,除非有“内奸”,是不会被找到的,我们毕竟不是警犬啊!哈哈!有时候也有危险,又一次,一个同伴由于太累,竟然在“洞里”睡着了,差点吓死父母,最后,全队的大人通过拉网式地寻找,才把他从“洞里”拎出来。
要知道,那个年代,农村很多地方还是有狼的啊!
过了这些年,夏收的场景,离我们似乎越来越遥远。生活的舒适,让人们多多少少的丧失了追求,文化生活的繁荣,反而让很多人失去了精神寄托,以往的乐趣,正在从我们的记忆中淡出。
麦子的经典散文
自打进了城,有些年没有伺候庄稼地了。平日里吃着白馍,喝着麦面粥,反倒觉得是天经地义,该不会亏欠谁的。念及此,真真地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了一跳,继而觉得自己麻木得简直就是个饭来伸手的家伙!我不想辩白,这些年内心确有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不断作怪。进城后,这几年因了工作的关系,生活的时间、空间离农村越来越远。甚至渐渐淡忘了该去怎样种庄稼。越想越发地不安,心里一杆小秤开始七上八下起来。偏偏刚开始反省的我,还没想好怎么找着回家的路。我大抵知道,须我用心推开记忆中通往村庄的那条路……
大学毕业之初,自己单了有几年,好在无太多挂牵。逢麦秋两季子,大都请假回家帮农。上了几年的学,身子骨并没有因为丰富的大学生活凭空多生出几把子力气来。对于秋收,我无太多抵触情绪,概因时间长,劳动的份量被拆得东一天西一天的,净干些磨洋工的活儿,倒应了自己疏懒的心思。麦收不行,麦子不等人的。待到熟麦子的天气,眼看着麦穗一天一个成色。收割之前,父亲必躬身前往麦田,揪下一把麦穗,在手里搓搓,搓得麦穗离骨,父亲张开那双树皮一样粗糙的手,“孙猴子”似地朝手里的麦粒儿吹上几口气,待麦皮被吹得七七八八了,捂入嘴里反复嚼着,嘴里念叨着,嗯,火候儿差不多了,这几天就可以开镰了。
乡人眼里,麦子是与神通灵的,每逢年节,供桌上摆放的香炉里是要放些当年的新麦粒进去的,继而在上边插上三炷香,香也不敢乱放,三炷就是三炷,乡人讲究的是神三鬼四,放四炷香可是敬各路鬼魂的。且不说灵验与否,麦子的身份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开镰前,有些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提前大半个月,家家户户在家开始搓草月子,麦秸蘸了水搓起来的草月子能赶上皮鞭子,那股柔韧的结实劲儿若打在人身上,立马腾的弹跳起一道红记来。饶是这样好用,我也没敢用它去打架,因为还有比它更厉害的.东西---父亲顺手抄起的木条子。镰刀也是要打磨的。置一盆水,把磨石放到一个及膝高的长条凳上,人骑在上边,用手捧几下水均匀撒到磨石上,麦收前最神圣的工作开始了。随着父亲腰背弓一样地上下起伏,镰刀渐渐露出了底色。不消片刻,一把把锋利的镰刀就能磨成。
母亲,则操持着麦收期间应急吃的饭食。过麦,人让麦子撵得脚打后脑勺,逢急活的时候,来家吃点现成的,吃完踮脚就往麦田去。大多时候母亲要不摊上一盖垫煎饼,要不就蒸一锅窝窝头,捎带着蒸上几个馒头。把早已腌好的咸鸡蛋、咸鸭蛋一并蒸上作为应急的菜肴,吃的时候用刀一劈两半,每人一半,多了不给。烧一大锅绿豆汤,田间、回家都能喝得上。为此母亲往往操持好几天,哥哥姐姐间或去打个下手帮厨,顺嘴偷点吃的犒劳一下自己也是常有的事。
这些活于我没有太多的吸引力,我是做不来的。念书,我却能钻了书里大半天不出来。上课学到与麦子有关联的课文时,老师总能给我讲些关于麦子的过往。麦子秸秆中空却有骨节,这点倒像是竹子,是有些气节的。叶子一溜儿长披针形。老师说,麦子是有灵性的,一畦畦麦子打小长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是有感情的。它们生在长在母亲---大地的怀抱里,一路相扶走到终了。说到后来竟有股悲凉的味道。我不忍再去听。毕竟年少,有一次,受好奇心地驱使,瞅晚上出去玩耍的空当,跑到村头的麦田边上,静静坐那儿偷听。听见了!微风吹过,麦子发出沙沙的响声,看到黑暗里影影绰绰的麦子顺风向我倒来,因了心里害怕的缘故,无端地把风吹麦田的声音当成了麦子的哭声,吓得掉头就跑,再也不肯回来。
要开镰了。我随父母来到地头,看着满目苍黄的麦子,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微风吹来,麦浪滚来。头挨着头,腰挨着腰,发出齐刷刷的声音。无须再去分辨这种声音的属性或去从,因为它们很快就会倒在农人的镰刀下。随着镰刀一次次地起落,一片片麦子倒下,甚至没来得及听到一声叹息。麦子在麦地里站了一个季子,该看的看了,该经的经了。临了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了更需要它的人,毫无保留,没有一丝地犹豫。它的生命并没有结束,而是得到了延续变成了白面。被人们做成了白馍、面粥、糕点等各种美食,销往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人们在吃着这些美食的时候,到底还有几人会记得麦子的过往?
凭心而论我与麦子是有感情的。家里条件不太好的时候,父母兄弟姐妹大都吃煎饼、玉米窝头充饥。因了我在家里排行最小,又体弱少力,父母把不多的白馍留给我吃。母亲还常常偷着给我开小灶,做点面疙瘩汤给我喝。可以说那段岁月,是母亲靠着麦面把我养起来的。去外乡读初中的时候,每次临行前,母亲总是往我包袱里塞上几个大白馒。母亲是舍不得吃的。有一次我看到,在灶房里母亲用铁铲刮糊在铁锅边的馒头皮儿放到嘴里吃,吃完了一副幸福满足的样子,脸上还带着不会轻易发现的笑容。此刻我知道,母亲定然是想起了我平日里狼吞虎咽吃白馍的样子。我对母亲的感情,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麦子的。上大学以后,麦田承包到户,生活有了起色,父母就是靠卖麦子的钱供养我上完了大学。我应该对麦子是感恩的。农民讲究的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困难时候,我是靠麦子度过难关的。
与麦子的缘分,该是一生缘。那,怎么困难的时候,我对它怀揣着感情没齿不忘,越发到了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反而想不起来了呢?等写到了这篇文章的结尾,我终归还是找到了回家的路。年少时对麦子的感情是因它蘸满了深深的母子之情,养我长大,其之深,其之厚,让人念念不忘。未等我成人,母亲便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于麦子的记忆便随着母亲的离去被深深封存在了记忆的一个角落,上边加了一把时光的锁。而后的日子里我习惯性地排斥着这个角落,终日强迫自己,久而久之便变得麻木了。就像一张黑白底片,时间久了某些地方已然变色模糊。念及此,是该沿着回家的路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