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杜甫》原文与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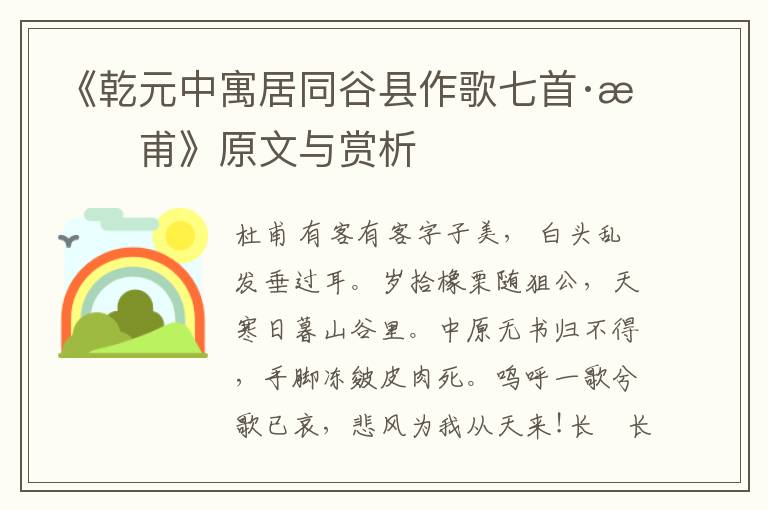
杜甫
有客有客字子美, 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前飞驾鹅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钟离, 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 白狐跳梁黄狐立。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
南有龙兮在山湫, 古木巃嵸枝相樛。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 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乾元二年(759)七月,因关中饥馑,杜甫弃去华州司功参军微官,携带家眷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去。《秦州杂诗》第一首说:“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流。”由此可见, 杜甫此去秦州完全是为生活所迫,心情极不愉快。“万方同一概,吾道竟何之?”(同上第四首)本为避乱而来到秦州,谁知秦州也跟其他地方一样,显得很乱,不是太平之境,更有什么地方可以托身呢?他靠亲友接济和卖药来维持衣食,但常常衣食不继,生活极其困难,囊中只剩下一文钱,却不忍用去,勉强留下安慰自己苦涩的灵魂:“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不炊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到了十月,听说同谷县(今甘肃成县)“充肠多薯芋,崖蜜亦易求”,于是便“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出发到同谷去。谁知到了同谷,生活更苦,只能靠拾橡栗、挖黄独来充饥肠,有时空手归来,只好全家挨饿。因此,仅在同谷勉强住了一个多月,到十二月,全家复往成都去,以寻觅一个安身之所。同谷七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惨晶泣血之作。
这是一组有严密章法的组歌。分开来看,七首各有描写重点,均可独立成章;合起来看,七首浑然一体,一意贯之,是一首完整的长歌。
第一首统摄以下各首,总写寓居同谷的艰难处境,揭示作客伤老本旨,抒写满腔悲哀之情,为组歌定下基调。首联从自叙开始,“有客有客”,运用重迭词语,强调诗人作客身份,为下文苦境的描写作好铺垫。“白头乱发垂过耳”,诗人抓住特征,自画肖像,这肖像中隐含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和社会内容。自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叛乱以来,李唐政权在风雨中飘摇,人民在战火和血腥中呻吟,已经整整四年了。虽然官军曾经收复过两京,但目前处境仍然极其不利,史思明重又于乾元二年九月攻陷洛阳,吐蕃在西部边境不断点起战火,“贼火近洮岷”,再加上关中发生特大灾荒,这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的热血诗人,怎能不被煎熬得满头白发呢?况且,生活的担子过于沉重,生活的滋味过于苦涩,一家数口的命运都寄托在他身上,“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石龛》)数十天在荒山僻径上跋涉奔波,历尽艰险,受尽苦难,哪里还有心思和空闲去修剪头发,当然是“白头乱发垂过耳”了。颔联写诗人寄迹于寒山,无衣无食,几乎被冻饿而死。“岁拾橡栗”是实录,当时的杜甫,困窘至极,“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新唐书·杜甫传》)。橡栗是栎树的果实,似栗而小,虽可食,但味极苦涩,多食会使腹胀。所以,即使是饥民,不到迫不得已时,也不吃这东西。“粮绝饥甚,拾橡栗而食之。”(《晋书·挚虞传》)狙公是养猴的人,狙公用橡栗喂猴。如今岁暮日晚,天气严寒,无其他野生植物可找,只好跟随狙公到深山中去拾橡栗。猴子倒有狙公抬了去喂,诗人却要自己去拾,简直连猴子都不如。这两句纯用白描,但怨苦之情却充满字里行间,读来令人心酸。颈联抒写有家难归之苦。人处于绝境,思乡之情必不可遏。可是,“中原无书归不得”,弟妹们信息杳然,是战事不利,还是生死难卜?诗人忧心如焚,但面对着“手脚冻皴皮肉死”的残酷现实,却又无可奈何。末联用感慨悲歌作结。歌声哀怨,歌声便是心声;岁暮多风,烈风化成悲风。主客交融,物我合一,诗人特特于末联点出“悲”“哀”二字,给整组歌词定下感情的基调。
第二首写全家生活,只靠一把挖掘土芋的长馋,结果依然空手而回,全家只好挨饿。首联运用拟人手法,连连呼唤手中挖掘土芋的工具:白木长柄锄头啊白木长柄锄头,我全家就全靠用你挖土芋来活命啦!这正如刘辰翁所说:“一歌唤子美,二歌唤长镵,岂不奇崛?”(转引自《杜诗镜铨》卷七)这种奇特的构思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表现了诗人对于相依为命的长镵的亲切感情。仇兆鳌说:“命托长镵, 一语惨绝,橡栗已空,又掘黄独,直是资生无计”;“前后章,以有客对弟妹,叙骨肉之情也,中间独将长镵配言,盖托此为命,不啻一家至亲。”(《杜少陵集详注》卷八)二是诗人流浪到同谷,身居客地,举目无亲,没有人能理解和同情诗人辛酸的遭遇,以长镵为亲人,正反衬出诗人沉重的孤独感。颔联写诗人虽然挨冻熬冷,但由于雪盛盖山,却挖不到黄独。“山雪盛”三字,不仅是“黄独无苗”致使诗人难以寻找无法挖到的原因,也是数挽短衣无法掩胫这一典型动作产生的原因。有经验的土人绝不会在这种情况去挖掘黄独。而缺乏生活经验的书呆子却偏于此时去挖,其性格之憨厚、生活之窘迫也就可想而知了。颈联写空手归来,全家呻吟;继而四壁空空,一片死寂。“男呻女吟四壁静”一句采用反衬手法,极其精彩传神,正如张溍所说:“既曰呻吟,又曰静,言除呻吟外, 别无所有,别无所闻也。”(转引自《杜诗镜铨》卷七)末联写邻居终于被感动,产生了怜悯之心。前首以悲风结,是天助之哀;此首以邻里结,是人为之悯。合两首来看,天人一同悲悯,杜甫的怨苦,显得多么深广啊!
第三首悲叹兄弟离散,难以团聚。杜甫兄弟共五人,杜甫最年长, 四个弟弟名叫颖、观、丰、占。写此诗时,只有幼弟杜占在身边,其余三个弟弟,散处在山东、河南等地。他另有《月夜忆舍弟》诗云:“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由此可见诗人兄弟情谊之深。首联写三位弟弟散居在远方,无由见面,想象他们在兵荒马乱中一定都很瘦弱,言下充满关切之情。“三人各瘦何人强”句,除了表面意思外,还暗用了两个典故:《后汉书》:“赵孝弟礼为贼所得,将食之,孝自缚诣贼曰:‘礼饿羸瘦,不若孝肥饱。’贼感其意,俱赦之。”梁武帝《与武陵王书》:“兄肥弟瘦,无复相见之期。”这两个典故都是有关兄弟深厚情谊的,首联暗用了这两个典,更显得情意浓郁。颔联叙述使其兄弟离散的原因。上句叙诗人从东都而到长安,席不暇暖,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接着又弃官由秦陇入同谷,匆匆奔走,兄弟不能团聚。 下句以胡尘暗天道路漫长说明兄弟生别的原因,极其形象确切。安史叛乱已整整四年,战火遍地,疮痍满目,拆散了多少家庭,屠杀了多少生灵,想起这些,诗人的心都为之发颤。如今兄弟参差,生离犹如死别,怎能不使诗人痛心疾首呢?颈联写诗人幻想假翼飞鸟,飞到三位弟弟身旁,以享天伦之乐。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残酷的现实是他流落同谷,即将被冻饿而死,生聚已经无望,死别将成为事实。于是就逼出了尾联,发出三位弟弟不知到何处来收埋兄骨的哀叹。呜咽悱恻,如闻哀弦,惨晶泣血,令人掩卷长叹:天之丧斯文,何至于此耶?
第四首怀念寡居的妹妹。首联叙述他的妹妹远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丈夫早已死去,几个孩子都很幼稚而不懂事。似乎是纯客观的叙事,实际上搏动着一位兄长最关切的赤诚之心:在战乱和天灾交相煎迫的艰难环境中,象他这样的男子汉都无能为力,一位寡居的孱弱的妇女,带领一群嗷嗷待哺的幼儿,将如何生活呢?颔联感叹已与其妹十年不见,虽然迫切希望她来到自己的身边,但是,“长淮浪高蛟龙怒”,妹如真的前来, 要跨过多少山山水水,途路中的险恶又令人不得不担忧。这是一种十分矛盾与惶恐不安的心情,都凝缩在这短短的两句之中了。颈联进一步写自己欲往不能的苦恼。“箭满眼”、“多旌旗”是对于战争的形象描绘。当时永王李璘欲与肃宗争帝位,江南也发生了兄弟阋墙的战争,所以即使诗人拟“扁舟欲往”也不可能。又是战乱,阻挡了亲人的会面。末联以猿啼清昼作结,更增加了凄惨的气氛。猿多夜啼,现在连白天都啼了,更显得悲哀。仇兆鳌说:“猿啼清昼,不特天人感动,即物情亦若分忧矣。”(《杜少陵详注》卷八)
第五首写诗人流浪在荒凉古城,万感交集。前四句写景,将一座谷里孤城刻划得那么荒凉、冷落、凄惨、恐怖。这既是对于同谷县这座山城景色的客观描绘,也是诗人凄苦哀怨的主体感情的物化。仇兆鳌说:“此歌忽然变调,写得山昏水恶,雨骤风狂,荒城昼冥,野狐群啸,顿觉空谷孤危, 而万感交迫。”(同上)所以前四句写景是为五、六句抒情服务的。末联结句翻用楚辞《招魂》中的“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意思,表达了诗人思恋故乡心情的迫切。“魂招不来归故乡”是说诗人流落在这么一个荒凉的孤城, 令人丧魂失魄, 因为诗人的魂魄早已飞向故乡,招也招不回来了。如此使用典故, 不仅化腐为新,而且曲折地传达了此时诗人的心境,使人感到寓意更加深沉。
第六首以同谷景物为喻,抒发对于现实的深沉感慨。前四句描写了同谷县万丈潭的景色,在古木参天,枝桠交缠,木叶黄落的隆冬季节,在一片萧条冷落、阴森森的背景下, 出现了龙蛰山湫、蝮蛇东游的反常现象。前人指出, 龙蛰山湫比喻“君当厄运”,蝮蛇东游比喻“史孽寇逼”,我们认为是切合杜甫原意的。据史书记载,这时史思明正与李光弼在洛阳一带恶战。乾元二年三月, 九节度使六十万兵溃于邺城; 九月, 史思明复陷洛阳。直到十月,李光弼才把史思明打败。杜甫写同谷七歌,约当十一月间,古代交通不便,消息传递较慢,诗人于写诗时得到的主要是官军打败仗的消息,因此诗中深深为朝廷担忧。五、六两句进一步写诗人愿为朝廷出力,拔剑斩此妖孽。但是力不从心,“欲斩且复休”。一方面固然由于诗人体弱多病,无能为力;更重要的是,朝廷排挤玄宗时的老臣,杜甫属于房琯一派, 也在被排挤之列,不在其位,难以谋其政,只好“欲斩且复休”了。尾联盼望严冬赶快结束,春天很快到来,是对战乱极其厌恶的表现,希望天下太平, 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当时人民共同的心声。
第七首自叹功名未就而落泊荒城,呼应第一首而总结全歌。首联慨叹身已衰老,但功名不就,壮志蹉跎,只落得个“三年饥走荒山道”的凄惨下场。古今中外有多少优秀诗人,生前不被人理解,颠簸困顿,受尽折磨,衣食无继,连最低生活水平都无法维持。是“诗穷而后工”呢?还是诗能使人穷?其间的微妙关系,恐怕谁也说不清。读了杜甫这两句诗,禁不住要洒下一掬同情之泪。颔联用长安新贵们的得意与自己落泊的情景相对照。杜甫愤慨地说,朝廷中的卿相都是少年新贵, 可见要想取得功名富贵必须及早去钻营。这表现了诗人对宦官李国辅独揽大权、排斥旧臣、滥用新进、误国误民行为的极端不满,并不是对新贵的羡慕。而朱熹完全误解了杜甫,只在艺术上肯定了这组歌,而从内容上批判了这一联。他说:“杜陵此歌,豪宕奇崛, 至其末章,叹老嗟卑, 则志亦陋矣,人可不闻道哉!”(转引自施鸿保《读杜诗说》)朱熹这种批评,完全是无的放矢,是理学家的故作高论,正如施鸿保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朱子特未遭此境耳!”指出这是不能体会诗人身处穷愁潦倒困境时心情的风凉话!颈联写诗人与山中儒生回忆往事,越发增加了凄凉之感。因为当时的儒生们忧国忧民的怀抱是相同的,而处境又都是如此凄凉,他们之间共同的语言很多,当然都要共同发一番感慨了。末联感叹时光飞驰, 而老冉冉将至,有汲汲顾影、 自伤迟暮之意。当时杜甫已经四十八岁,多愁的人容易衰老,他自己感到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这是诗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综观这组歌,“七首皆身世乱离之感。遍阅旧注,疑后三首复杂不伦。杜氏连章诗,最严章法,此歌何独不讲?及反复观之,始叹其丝丝入扣也。盖穷老作客,乃七诗之宗旨,故以首尾两章作关照,余皆发源首章。条疏于左:一歌,诸歌之总萃也,首句点清‘客’字; ‘白头’、 ‘肉死’,所谓通局宗旨, 留在末章应之;其‘拾橡栗’则二歌之家计也; ‘天寒’‘山谷’则五歌之流寓也;‘中原无书’则三歌四歌之弟妹也;‘归不得’则六歌之值乱也;结独逗一‘哀’字、‘悲’字,则以后诸歌,不复言悲哀,而声声悲哀矣。故曰,诸歌之总萃也。各章结句,亦首首贻定,语不浪下。”(浦起龙《读杜心解》)浦氏这段话,简明扼要地分析了这组歌各首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我们深入理解杜甫组诗的严密章法,是很有帮助的。
这组歌采取定格连章体,反复吟咏,一唱三叹,这种抒情方式显然受到了张衡《四愁诗》、蔡琰《胡笳十八拍》和鲍照《拟进路难》等组诗的影响,但又能够加以变化、创新,传其神而不袭其貌。自从杜甫创建了这种连章体的组诗形式后,历代都有诗人继承这一传统,创作出许多优秀篇章,其中尤以文天祥的《六歌》最为突出,现录一首如下: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识桃李春。天寒日短重愁人,北风随我铁马尘。初怜骨肉锺奇祸,而今骨肉相怜我。汝在北兮婴我怀,我死谁当收我骸?人生百年何丑好,黄粱得丧俱草草!呜呼六歌兮勿复道,出门一笑天地老! (《指南后录》卷之二)豪宕奇崛,慷慨悲凉,深得少陵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