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琇荣《一粒水红色革命种子的燃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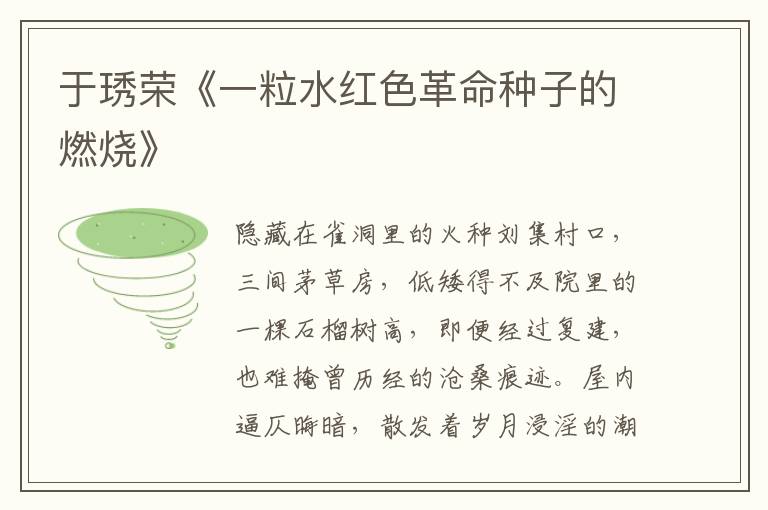
隐藏在雀洞里的火种
刘集村口,三间茅草房,低矮得不及院里的一棵石榴树高,即便经过复建,也难掩曾历经的沧桑痕迹。屋内逼仄晦暗,散发着岁月浸淫的潮凉。屋门右边,四块青砖呈“井”字形嵌在山墙里。那是雀洞。我很是诧异,刘世厚——一个仁慈到为鸟雀筑巢的农民,是如何在血腥屠杀中举起了反击的拳头,并历经动荡混乱风雨飘摇的43年,将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译本保存至今。而那山墙雀洞,正是主要藏匿之处。
我在广饶博物馆见过那本书,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比现在的32开本略小一点。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上端从右至左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上署“马格斯、安格斯合著”和“陈望道译”。全文用5号铅字竖排,计56页。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初版”“定价大洋一角”字样,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
山东倚山临海、民心淳朴、经济富庶,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14年欧战爆发,欧洲各国几乎全部卷入了战争,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并借机攫夺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租借地,使山东再次陷入了战火硝烟之中。1919年,“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合理主张,引起了人民极大愤慨。在进步思想影响下觉醒了的青年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最终促使政府放弃在和谈上签字。自此,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和人员基础。而饱受战火蹂躏的山东,也注定成为了革命洪流中的漩涡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1920年初,陈望道受上海《星期评论》编辑李汉俊等人委托,返回乌镇老家,不分昼夜地依据日文、英文翻译《共产党宣言》,把一直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带到了中国,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由此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924年,刘子久受党的一大代表、山东党委王尽美同志委派,借探亲之际,回到家乡刘集,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刘集党支部。1925年,刘雨辉将《共产党宣言》带到刘集,交给当时党支部书记刘良才,1930年刘良才调任潍县任县委书记,将书交给刘考文。1932年,博兴暴动失败,刘考文预感可能被捕,又把这本书交给了共产党员刘世厚保管。
刘世厚很清楚,接受保管这本书将意味着什么。当时,国民党在统治区实行文化“围剿”,颁布法令,把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非法”的“禁书”,《共产党宣言》是禁书之首,如果被发现藏有此书,可能被判处监禁甚至会被处死。但他还是接受了,因为这书里藏着他梦想中的好日子。他精心地用油纸把书严实包好,装进竹筒,埋在了炕铺下面。
1941年1月18日,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刘世厚知道,此次敌人来者不善,一定会大肆清剿搜查。他忙把埋在炕铺下面的《共產党宣言》取出,塞进山墙的雀洞里,用碎泥土块封住洞口,领着乡亲们逃往村外。
一月的鲁北平原,北风凄厉、广袤苍凉,阴郁低垂的天空下,一拃长的干枯麦苗,像被抽了筋骨似的倒伏在大地上,远远望去,泛着一层虚浮的绿意。几棵老榆树散落其间,伸着干枯扭曲的枝桠绝望地在风中舞动,妄图在空气中抓到点儿什么,但除了几声老鸹不祥的聒噪,终究没有什么也没抓到。苇子沟迎着风口,肆虐的北风,呼呼地往沟里灌。村民静静地趴在苇子沟里,河沟里的水不深,结了一层薄冰,寒冷的冻土,隔着棉衣凉进了骨头缝里。 寂静,可怕的寂静,大家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一切静谧得像场梦。只有额头抹不尽的汗和咚咚急促的心跳,在昭示着一场灾难正在发生。
透过芦苇叶的缝隙,刀锋一样锐利的眼神盯视着正惨遭涂炭的村庄。忽然,一股浓烟在村落上空升起。火?火!有人发出惊呼。浓烟里,通红的火苗跳跃着,舔舐着天空,一会儿工夫,整个刘集村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看着火势越来越猛,刘世厚心急如焚,藏在雀洞里的《共产党宣言》揪得他坐立不安。他心一横,不顾他人劝阻,沿着地埂往村里跑去。燃烧的热浪混着黏腻的血腥味在村巷弥漫,树下、断墙边、院落里横陈着他熟悉不能再熟悉的乡邻的尸体。刘世厚顾不得难过,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正四处搜寻的鬼子,悄悄地溜回家。家里此时已是破碎不堪一片狼藉,火苗正从屋顶、门洞、窗眼里向外疯狂乱蹿。他急忙拨开雀洞滚烫的泥土封口,直到摸到完好的竹筒,他紧绷的心才一下子舒缓下来。
他把竹筒揣进怀里,忍着大火的炙烤,蹲在墙角躲藏了起来。
远远地,他听到一个人从墙外巷子里慌乱地跑过去,紧跟着,一阵嚎叫混着杂乱的脚步声追了过来,随后一阵枪响。又一个老乡被枪杀了,刘世厚想。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杂乱的脚步声远了,零星的枪声也停止了,整个村庄陷入了一片死寂。周遭静得骇人,世界在这一刻仿佛被扼住了喉咙。惊恐,在毕毕剥剥的燃烧声以及房屋轰然倒塌的声音里渐渐消失,只剩下愤怒和仇恨,在狠狠地撞击着胸腔。
这次围剿,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刘集惨案”,80多名村民遇害,500多间房屋被烧,而那本《共产党宣言》,竟奇迹地保存了下来。
在此后的34年里,刘世厚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藏进过屋檐瓦里、封进泥灶头、粮食囤底下、山墙雀洞,他的生命好像只为这本书而存在,刘考文把书交给他时的谆谆嘱托:“记着,人在书在”,刘良才被敌人用铁钉活活钉死在城墙上的惨状,让刘世厚备感肩负的责任重大。
1975年秋,广饶县文物所所长颜华得知失踪多年的《共产党宣言》在刘世厚手里,便到他家里做动员工作,已84岁高龄的刘世厚老人一袋接一袋地吸着旱烟,就是不说话。颜华说,这是马列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主义的纲领,这么多年,承载着多少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痕迹,珍贵着呢。老人沉默良久,才把这本珍贵的书从藏匿地取出来,将散乱的页码订好,在首页的左上角郑重地盖上了一枚“刘世厚印”,将它献给了国家。
走出茅草屋,阳光和煦,刘世厚的半身铜像迎门而立。老人仁厚安详地微笑着,注视着来访者行走在蓬勃的“中共刘集支部旧址”,与鸟雀和睦相处。
革命,在血腥的土壤里萌芽
1941年12月20日凌晨,黑漆漆的夜,分外寂静,一轮镰刀似的残月斜挂在山顶。此时,正是睡意酣甜的时候,一片安逸的鼾声在村庄里虚渺地飘浮着。村长林凡义躺在炕上辗转反侧,不幸的预感搅得他心绪不宁。前几天,驻扎在小梁家的伪军来要钱粮,被他坚决拒绝了。敌人不会善不甘休的,林凡义心里知道。忽然,他听到几声狗吠,接着,整个村落里的狗疯狂地叫了起来,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鬼子来了。林凡义想着,心里反倒镇定了下来。
村长林凡义对乡亲们说:“鬼子把咱们包围了,冲是冲不出去了!咱渊子崖人是有血性的,宁死不当孬种。”村民异口同声:“宁可站着死,绝不躺着活!”
这是场惨烈的不忍用笔去叙述的战斗。 1500余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趁着夜色扑向了渊子崖。
淵子崖,位于沭河东岸,据《林氏续立石谱碑》记载:“大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自新泰来复业,复迁兰邑东乡渊子崖村。”因村坐落在一深渊近处故名渊子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躲避匪盗祸乱,渊子崖沿村筑起了5米多高、1米多厚的围子墙,墙上修了大小不等的炮楼、炮眼,很是坚固。
敌人开始进攻了,先是用炮轰炸围墙和村庄,雨点一样的炮弹砸向城墙。顿时,村子里硝烟弥漫、浓烟滚滚,不时有被炮弹击中的房屋轰然倒塌成一堆瓦砾。有人从围墙上的脚手架掉下来牺牲了,乡亲们拉来草苫,含泪为他盖上。炮弹炸伤了肚子,肠子流出来,再填回去,用破布在腰上一扎,继续战斗。围墙炸开口子,用门板、石块把缺口垒上。老人、妇女、孩子把烧饭的铁锅砸碎,把铁耙钉砸下来,当作土炮的砂子,青壮年手持几支简陋的枪支、铡刀片与鬼子战斗。村民林九兰隐藏在围墙豁子口旁,鬼子上来一个,他就用铡刀砍死一个,上来一个,就砍死一个,砍倒第八个鬼子,终因体力不支,被鬼子的刺刀扎进了胸膛,牺牲了。
鬼子进村了,村民们边打边撤,用笊钩、铁锨、菜刀、锄头同敌人展开了更加惨烈的巷战、肉搏战。林九乾死了,他妻子怒吼着冲上去,用镢头将鬼子的脑袋砸开了花,她搂住丈夫的尸体悲痛地号啕大哭,公公林秉标冲了过来,用一捆稻草轻轻盖在儿子脸上,一把拉起儿媳说:“孩子,这不是哭的时候,站起来和鬼子拼呀!” 有的父子在巷口阻击敌人,有的母女合力同鬼子厮打在一起。儿子死了,父亲上;丈夫死了,妻子上;哥哥用身躯挡住了扎向弟弟的刺刀;姐妹与鬼子撕扯成一团,用牙咬烂鬼子的喉咙;围墙上,不断有人搂着鬼子一起跳下摔死。村子里到处都是惨叫声、怒骂声、砍杀声……
鲜血染红了村巷、断墙,染红了天,街道上、院落里横七竖八躺着牺牲了的乡亲。终于,附近的八路军闻讯赶来增援,敌人这才退败而逃。
夕阳西下,冬日的余晖抽走了人间最后一丝温暖,像不忍直视这惨烈的人间地狱,用暗夜,一点一点遮蔽起飘荡在这座英雄村庄上空的悲泣和哀伤。
此次战役,村民牺牲145人,伤400人。毙伤日伪军154人。这是一场真正的与敌人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战斗啊。
这样的事在沂蒙老区俯拾皆是,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支前模范,每个村庄都有抗日故事。这是一群有着怎样脊梁的人啊?
当跟随省作协采风团走进莒县革命纪念馆,我找到了答案: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分别于1924年和1926年介绍刘子久和宋寿田入党。刘子久借回家探亲之际,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刘集党支部。宋寿田则受省委指示,回到家乡莒县开展农民运动,因此,莒县群众得以较早地接受到了进步的革命思想教育。
莒县,人口不足百万,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就达13341人。众所周知,解放前,中华大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革命前途晦暗未卜,是他(她)们,在黑暗中点亮了曙光,并笃定地坚信光明终将到来,用心中崇高的信仰,坚信!
纪念馆玻璃展板内,一张张因时间久远而泛黄薄脆的入党申请书上写满“蹩脚”的汉字,甚至有错字、别字,但正是这些字,却看得我肌肤战栗,热血沸腾,禁不住为自己填写入党申请书时的狭隘与浅薄而羞愧。
刘太花、入党动机:为了抗日打鬼子,保家乡。
董玉胜、入党动机:为人民服务,不在(再)受压迫,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到底。
李经岗、入党动机:为了反(翻)身解放过好日子,有地位领导人民组织互助组。
“老头子嫌乎俺成天往外跑哦,说不退党就离婚,俺就说,宁可离婚,也不退党。”薛贞翠老人说。
“是党的人,就要听党的话,跟党走。”86岁还担任村支书的卢翠秀说。
“入党为了打鬼子,不打鬼子,没有家,没有好日子过。”竺守海老人说。
大银幕上,耄耋之年的老人提及过往谈笑风生,曾经的生死一线在他(她)们眼里早已化作云淡风轻。那一张张沟壑纵横却乐观豁达的笑脸,一句句朴实却振聋发聩的话语,濡湿了我的眼眶。
蓬勃发展的根据地武装
烈士陵园,曾是庆云小城里最好的一栋建筑。红墙碧瓦,廊柱高耸,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愈加显得庄重巍峨,尤其是那几根爬满山墙的紫藤,根系粗壮蓬勃,风吹枝叶,会发出一阵又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像海浪,穿过硝烟,浅吟低唱地诉说着被时间尘封的过往。
每到清明,武洪章会随单位人员一起去烈士陵园祭扫。而在这个日子里,武洪章还会带着祭品或者去铁营洼,或者去东安务,那里一个是他二爷爷武大风的牺牲地,一个是武大风的衣冠冢。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创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11月,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王尽美和邓恩铭被选举为领导人。王尽美负责鲁南地区的党组织活动,邓恩铭则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津南、鲁北平原,让正在庆云中学求学的武大风得以接触到进步革命思想。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以及更多的进步书籍,武大风的思想受到深刻教育,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劳苦大众”。不久,他在刘格平的介绍下,加入了党组织。
在《庆云县志》人物传记中,革命烈士武大风占了一个重要篇幅。传记说:“武大风是庆云县东安务村人,性行温雅端庄,忠厚俭朴,素怀大志,坚贞有骨气。”
“侵略者是弱糠,是经不起大风吹的。”他说。为此,他把名字由武同心改为武大风。
武大风被党组织派往无棣县工作,他挨家逐户地宣传抗日思想,不到3个月,就发展了40多人入党,组建了160余人的地方武装,除掉了60多个汉奸,策反80多名伪军投诚,成功组织了“马颊河暴动”。
蓬勃发展的抗日武装活动引起了鬼子的注意。1941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凌晨,日寇集中上万兵力,趁黎明前的黑暗,把方圆10多里的铁营洼围了个水泄不通,采用骑兵与装甲部队在前,步兵紧随其后的“铁壁合围”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把武大风和战士、乡亲堵在了包围圈内。
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武大风与大队冲散了,和几十名战士、群众被挤压在一条深沟里,借助地势与鬼子继续战斗。十多分钟,阵地上、深沟里,已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和战士的多具尸体。这时,通讯员报告,说东北方向已经把鬼子的包围圈撕开了一道口子,可以从那儿冲出去。武大风看着不断从路上仓皇逃难过来的群众,又看了看在不断组织进攻的鬼子阵地,说,你带乡亲们走,我们阻击敌人。话刚说完,他发现文书负伤倒在了沟沿上,他猛地冲上去,一把把他拽了下来。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肩,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染红了靛蓝色棉袄。
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用完了。武大风高喊,宁可战死,不当俘虏!率领仅存的16名战士与鬼子展开肉搏战。战士们跃出沟壕,与鬼子撕扯在一起,锋利的刀刺狠狠扎向敌人。 激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猛地跌倒在地上,再没有站起来。那一年,他刚满28岁。
武洪章说,当家里人听说“铁营洼突围”已经是在一天之后的事了。他爷爷推着独轮车走了几十里,去给武大风收尸。等走到铁营洼,眼前的情形把他惊呆了,蛮荒的盐碱洼地已成一片坟场,到处散落着残肢和尸体,北风呼号,干枯的蒿草上挂着蓝灰色或者土黄色碎衣条,在凄惶地摇摆,河沟里,厚厚的冰层上凝着一层瘆人的红,那是血。
武大风牺牲后,肖华司令员写诗称颂:“生即正直举止非凡系人中一大;死亦壮烈英勇不屈是无产作风上。”
敌人的残忍没有把革命者吓倒,反而点燃了仇恨。各县武装大队联合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给予鬼子以沉重的打击。
1938年5月,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指出,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每个士兵和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民兵、武工队等地方武装的蓬勃发展,不仅为主力部队提供了后勤保障,还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以及最终取得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炮火硝烟里的一抹红
“我们该如何活下去?”
这是电影《柏林女人》中女主人公最后的一句话,她茫然空洞的目光投向虚无的远方——一片硝烟弥漫满目疮痍的战场废墟。
也许战争的属性是雄性的,但纵观世界战争,女人,并没有从战争中走开,甚至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戰争的中心,承受着战争带来的屈辱和累累伤痕。是啊,当家国零落,又能有谁可以侥幸逃脱,成为一名旁观者呢!
如果日本鬼子没有在1938年侵略临沂,蒙阴县李保德村的李凤兰会有一个热闹喜气的婚礼,至少,会有新郎。但她没有,她和一只披红挂绿的公鸡拜了堂。她心里有点儿失落,但不悲伤,她知道,新郎是喜欢她的,只是作为一名战士,为了她和乡亲们能过上安稳日子正拼杀在战场。婚后,她参加识字班,学着唱《小战士》:
小战士,不很大,
心里装天下。
小战士,不很高,
扛着枪,挺着腰。
离开了爹,离开了娘,
到处打豺狼。
不怕苦,不怕冻,
为了翻身闹革命。
吃树皮,穿草鞋,为了胜利早到来。
她跟着婆婆、嫂子备军粮、做军鞋、看护伤病战士。她摊的煎饼,均匀薄脆,圆的像太阳。也许他会吃到呢!她想。她纳的鞋底和鞋垫,针脚密实,花朵艳丽。也许他会穿到呢!她想。她照顾伤病员,不怕脏累精心细致。也许他受伤了,别人也正这么照顾他呢,她还是这样想。她把满心满腹的情愫暗暗地融入了她的工作当中。
战斗越来越激烈,死伤的人也越来越多,她的心也越来越沉重,等待中的每个崭新一天,都让她既渴望又恐惧。终于,她悬着的心落了地,等待有了结果:丈夫在战场牺牲了。
“接到阵亡的消息,心里很难过吧?”几十年后,有人采访她问道。
“当时孟良崮正打仗,俺成天忙着粮食供给,哪还顾得难过。俺是党员,有这个觉悟,想要取得胜利总要有人牺牲的。”老人微笑着,甚至带有几分羞涩地说。
老人后来领养了两个孩子,于2008年去世,终身未再嫁。
在沂蒙山区,几乎村村有红嫂,家家有战士。为合围孟良崮,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李明芳毅然决然带领32名妇女,每四人一组,用8扇门板架起了火线桥,运送了整整一个团的兵力。冰冷的河水麻木了双腿,甚至导致有的妇女终身不孕。蒙阴母亲王换于,抚育了80多名革命后代,自己的三个亲孙子却因营养不良夭折。沂蒙红嫂明德英,为救生命垂危的八路军伤员,正在哺乳的她将乳头放进伤员的嘴里,用洁白的乳汁挽救了伤员的性命。据说,曾有人因为明德英是聋哑人而质疑整个事件的真实性。其实,卑微与高尚从来没有标准界定,心理残疾比身体缺陷更让人厌恶。还有身负重伤的女战士辛锐,年仅23岁,面对鬼子的包围,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据《战争和女人》一书中统计,仅抗日战争时期,就有15.5万沂蒙妇女以不同方式掩护了9.4万多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4.2万名沂蒙妇女救护了1.9万名伤病员。据资料记载,山东战场女性参战的多,争取政权的少,尤其是以沂蒙山区为最。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曾深情地慨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民……
胜利的堡垒 大后方
老家有两间土坯房,已闲置多年,除了一台体积庞大的织布机,就是些零碎的旧物。爷爷过世的早,奶奶靠为人织布维持家用,在那动荡的年月,所历经的苦难可想而知,但她很少提及,只一次,她抚摸着织布机动情地说,这可是活命的物件。单想想,禁不住让人心疼起来。奶奶去世后,爸爸隔几年,就会请人修缮一下。在记忆里,那房子,好像只是为了存放织布机而存在。
再次见到织布机,是在沂蒙的一个革命纪念馆。一根绳索隔开一块区域,里面一台破旧的织布机、一架纺车和一辆似乎可以随时架起出发的独轮推车。织布机的挡板和纺车的摇柄已被磨得圆润光滑,像浸了油 。旁边一行竖排正楷黑字:男人支前上战场,女人在家拼命干,做军鞋,纺棉线,种地打粮全支前。
缓步从展馆走过一圈,再站到这里,眼前的物件便生生活了起来:不分昼夜,纺车嗡嗡地转动,人歇机不歇。织布机的梭子,鸟一样,在细如发丝的棉线里上下翻飞,挡板咔嚓咔嚓地在后面紧紧追赶。憨实的沂蒙汉子,推起独轮车,用一双硬实的脚板,满载着军鞋军粮和弹药穿潍河、趟沂水、过吴家庄、瓦子口、太山营,推着小车跟着大部队历经睢宁、薛城、徐州等三十几个县市,往返数千余里,直把革命用小车推到滚滚长江的彼岸,推出了个孟良崮战役,推出了个淮海战役,推出了个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崭新中国。
据蒙阴县野店镇板崮崖村“支前模范”包彦廷回忆:1941年沭河干旱,1942年又闹严重蝗灾,庄稼几近无收,在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吃地瓜秧、树皮,是八路军从敌占区搞来粮食分给百姓,这才活了命。八路军在前方打仗,咱咋能袖手旁观,都争着扛上枪,推着军需物资去支前。他们避开大道,哪里山路难走走哪里,寒冬腊月,山上到处是积雪,他们就扛着物资攀着石头爬,手冻僵、划伤是经常的事。在护送的路上,无论怎么饥饿,也没人抽一张肩膀上扛着的煎饼充饥。运送伤员回后方救治,遇到轰炸,会立刻趴到伤员身上保护伤员,有人还因此牺牲了。他朴实的话,道出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当时,沂蒙老区喊出了“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口号。
在淮海战役中,群众为了支援解放军做工事所需要的木头,把自己家的箱子、门板,甚至是为老人准备的棺材都抬了来,解放军就用它们支撑起了密密麻麻的掩体、交通沟。当打完淮海战役,解放军部队转移时,吃惊地发现,周围百十里内的村庄,家家户户都没有了门板……被俘国民党将领杨伯濤也看到了一幕:以前经过村庄,门户紧闭,村镇静寂,现在却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抬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一辆辆大车满载猪肉,而他前不久经过这里,连一头猪都没看到。他感叹地说:民心向背至此,战败已成定局!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至解放战争1948年战略反攻,沂蒙老区共有留下名字的6万多名烈士,加上无名烈士共约近10万烈士。 沂蒙人参加战争的时间从1937年至1953年,足足有16年。
孟良崮战役,一举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从沂蒙山发起的淮海战役,更是敲响了国民党统治的丧钟。它的胜利,扭转了解放战争的整体局面,打破了蒋介石以长江“划江而治”的战略妄想,此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接连打响,最终夺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据统计,自1945年至1949年,山东先后动员1106万多民兵民工,使用了146.8万大小车辆,76.5万大牲畜,出动了43.5万副担架,支援了华东、中原、东北、西北四大野战军作战。将11亿余斤粮食和大批弹药、军需物资运往前线,把20.3万余名伤员转移到后方,同时,还担任看押俘虏,打扫战场等战勤任务。
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以及《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的讲话》上多次提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
穿过孟良崮革命烈士陵园纪念馆的大门往里走,迎面就是革命烈士纪念碑,碑两侧是茂密的松树林,一棵棵松树苍劲挺拔,像整装待发的士兵。这里,埋葬着2865名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忠骨。 墓地不高,在地面微微隆起,每个黑色大理石卧碑上都有一颗醒目的五星。五星下方,是烈士的名字,但大多卧碑上镌刻着的是“无名烈士之墓”几个字。无名烈士——埋葬着远方母亲永远眺望不到的儿子,和一生割舍不下的牵肠挂肚。“无名”比“有名”更扣人心弦,更揪得人心疼。
走在“沂蒙情雕塑园”长廊,我在雕塑群“火线桥”前伫立。旁边有两个当地民工在低语,一个问:如果是你,你会去支前打仗吗?另一个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会。
我抬头,发现孟良崮,海拔不高,山势亦不陡峭,却让人感觉无比的巍峨——它的高大巍峨,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