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沙漠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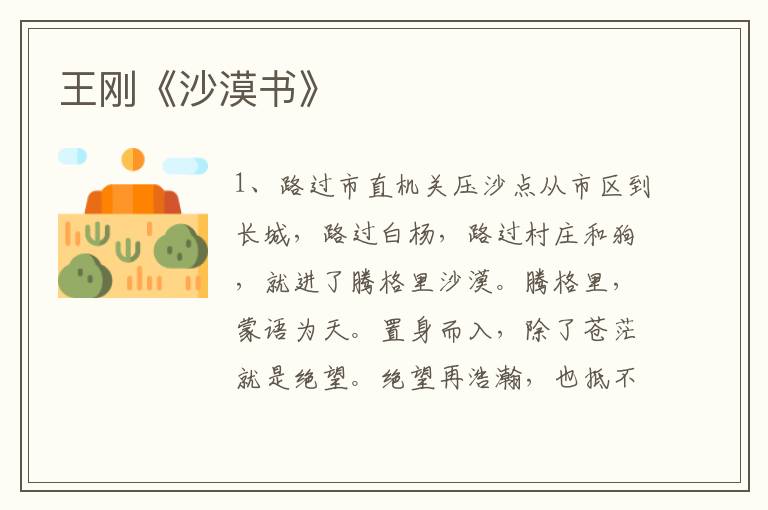
1、路过市直机关压沙点
从市区到长城,路过白杨,路过村庄和狗,就进了腾格里沙漠。
腾格里,蒙语为天。置身而入,除了苍茫就是绝望。绝望再浩瀚,也抵不过大漠的浩瀚。茫茫流沙如渺无边际的天空,人走着,也不过一粒沙子,倏忽就被湮没在苍茫的洪流之中。
这蔽目黄沙,可是成吉思汗征伐西域的滚滚马蹄裹携而来?我伫立在市直机关压沙点界碑前,长久静默着。风狂虐而起,没有理由,也无可阻挡,凉州城四面楚歌。
一株株梭梭,正昂扬唱歌。我说,为什么叫梭梭呢?芳凝说,你听,风一吹,索索地响呢。
西风浓烈起来,果然满耳都是“索索”的声音。大家循声四望,环环相扣的草方格,绑住了大大小小的沙丘,那些梭梭、毛条和花棒忽然就在草格子里恣意舞蹈了。
干旱和烈风造就了沙漠。而意志和信念又改变了沙漠。
这个初夏的早晨,一颗泪甩出眼角,腾格里知道,我被这苍凉的生命撞疼了眼睛。
2、九墩滩移民新区听风
九墩滩有多远?
路知道,车知道,我来了才知道。
路是新的,楼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正是午后,阳光曛暖。风追赶着发丝和衣角,长发微乱着,衣裳翩跹着,清风过耳的长街上,适合吼几声凉州贤孝呢。
从祁连、旦玛搬迁下来的人,在这里安营扎寨。告别了大山,以及雨雪寒霜,他们在这里开始打理新的生活。青白的小院,盛开的红槐,几把青蔬和豆角,搅拌在平常的日子里,祥和而静谧。
堂哥也在其中,他把牛羊变卖干净,义不容辞地来了。山里苦了一辈子,被山风吹打了一辈子,他受够了,沙漠里的城再荒凉,也是平坦的,水电都在按钮里,再也不用看老天的脸色侍弄牲口和庄稼了。
问堂哥,搬到荒滩后悔不?堂哥纠正,什么话,这是新城,沙漠里的江南。你看看,这树绿的,这楼挺的,这马路敞的,还可以听风呢。
风呼呼地吹着,时而清冽,时而温婉,总是停不下来。街上一尘不染,我们踏街前行,在九墩滩移民新区侧耳听风。
衣袂乱了,身形不乱;头发乱了,心里不乱。九墩滩的风里是有故事的,每一个移民的故事都在风里轻诉,只要用心,就能听到。这风是号角,一吹,他们就大步流星地走出门去;这风也是战歌,一吹,他们就热火朝天的干起事来。
风中,望着堂哥坚定的眼神,我的心就滚烫起来。他们是生态勇士,决然离开草原和故土,把根扎入沙漠深处,镇守住这方新开辟的疆场,牢牢抵抗住沙漠侵袭的脚步。
3、头墩营林场的雨
蓄谋了一天,饭罢,雨终于落了下来,打湿了头墩营林场。
风沙老谋深算,常常突袭;雨没有心机,还未下先皱巴个脸,提醒我们带伞。其时微雨沥沥,我们一直被满目的碧翠和新奇牵引,以致忘记撑伞的了。
自小在林场长大,对林场始终有着别样的挂怀。沙漠里的林场,更让我意兴盎然。
厂长说,“登高望远一片沙、大风一起不见家”,曾经是头墩营林场的真实写照。当年一干人冷水干馍,风餐露宿,豪气干云的誓言拿下沙漠,孰料头年秋季栽植的数百亩沙生苗木,第二年开春几场大风,就被集体连根拔掉。眼泪和干嚎能有啥用,治沙造林不能蛮干,理论知识远远不够,必须掌握沙区的气候特点,因地制宜,科学治沙才行。
春秋植树、夏季补水、冬季压沙,头墩营人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着八十里大沙林草植被。年复一年的心血培灌,风沙稳住了,沙丘变绿了,植被茂密了,沿沙绿树成片了。
今日雨中,枸杞、皇冠梨、酿造葡萄,青海云杉、祁连圆柏、樟子松争先比翠,经济苗木和常绿树种并肩吐绿,而它们脚下及周围,却是滚滚黄沙;而这黄沙的下面,一定就埋葬着头墩营人的血汗和铁骨。
雨中细问,才知头墩营林场始建于1976年,辖区面积28.9万亩,承担着21.9万亩国家级生态公益林和806亩苗圃的经营管护任务。四十年,几代人,固守在腾格里沙漠西南、红水河沿岸的万亩风沙线上,追逐并实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之梦。
雨渐渐浓烈起来,迫使我们乘上大巴,透过车窗,与每一株树木和绿草对视,探究它们在头墩营林场的前世今生,看着被沙漠包围的这一方葱茏屏障,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静静地走完了全程。
雨打湿了一切,心却不能平静,作别了头墩营林场,那团绿意自心底熊熊燃起,任凭这激烈冷雨也不能浇灭。
4、治沙歌与沙漠枪
长城乡名不虚传,残留的长城断续延绵,从远古而来,又隐没在今日的戈壁荒滩。这些当年耀武扬威的御敌壁垒,如今在风沙面前俯首称臣,臣服的结局不是倾塌,就是被黄沙掩埋。而今,沙漠以席卷之势,淹没了历史的金戈铁马,惟留下的一地叹息和无尽幽怨。
在长城乡红水村,见到了闻名已久的王天昌老人。
魁梧的身子,花白的胡子,洪亮的嗓子,散发着个性而又亲切的凉州味道。忽然想起祖父,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老人走进了沙漠。老人脚下生风,如履平地,我们暗自努力,勉强跟上,一路被满目的绿色惊奇,不觉就到了老人一家进军沙漠的地窝铺旧址。
让我们更惊奇的,是王天昌老人治沙的地窝铺。
这地下三尺,凿土挖洞,蓬上茅草树枝,搭成简易窝铺。我们猫身而入,里面逼仄阴暗,一盏油灯点燃,光阴流溯当年,土炕泥灶,灌风漏雨,据说有一次坍塌下来,差点就掩埋了全家。
这不是避难所,而是治沙的根据地。为了节省治沙时间,不在家和沙漠之间来回奔波,全家人开挖了地窝,以窝为家,日吃咸菜,夜燃油灯,日复一日,压沙治沙。
如此艰辛,治沙图啥?我们的疑惑尚未出口,老人就侃侃道来。
当年大风起兮,沙尘昏天蔽日,一碗饭吃罢,碗底落下半寸厚的沙粒;更残酷的是,风沙肆虐过后,庄稼被连根拔起,辛苦一年颗粒无收。有人携家带口,洒泪离开村庄;有人茫然四顾,无奈连声叹息。于是,那個清寒薄冰的早春,王天昌率领老伴,带上儿子王银吉带上咸菜干馍,水桶骆驼,毅然走进沙漠。
治沙根据地有了,还得有治沙武器。面对狰狞的沙漠,在一次次失败的经验里,一杆长枪打磨出世。
这枪,两米长的枪杆,圆锥形的枪头,大约一尺半长,枪杆的另一头,安着锄头。这是王天昌老人的智慧发明。他说,这叫沙漠枪。多么豪气的名字,老人胡须迎风飘扬,双目精光闪耀,沙漠枪在手里舞动生风,利落地示范起来,先用锄头刨去地表干沙,再调换方向,枪头插入沙中,用脚使劲踩踏,当枪头完全没入沙中时,拔出来,将树苗从枪头刺出的圆孔中植入。一棵树就这样在流沙中生根发芽,成为阻截沙漠侵袭的绿色长城。花棒、梭梭、毛条在沙漠枪下艰难播种,在草方格里繁衍生长,一家人用心血培绿了万亩沙丘。
说到治沙,老人一直神情激昂,可说到家庭,老人忽然黯然神伤。
幼孙十四岁那年,突然病倒,王天昌率领全家正在前线奋力植树压沙,就想一个壮如牛犊的娃蛋,偶然生病没啥要紧。这一耽搁,竟是永别。孙子最后的心愿,是让爷爷背着他来到沙漠深处,嘱托爷爷把沙漠治得绿绿的后,才闭上了一双清澈的眼睛。
一个人把一生丟进了沙漠,沙漠是他自豪的战场,拼杀过风沙的汉子,多少年岿然不动,可幼孙的罹世,永远是他心中最柔软的疼。一碰,就身躯颤抖,老泪纵横。
多少心事被黄沙掩埋,多少悲伤被岁月风干,安葬了孩子,擦干眼泪,挺直身子,吼一曲治沙歌,扛一杆沙漠枪,王天昌父子悲壮掉头,义无反顾地又走进沙漠。这一进去,就是十八年。
草长了,树绿了,可沙漠深处还焦黄着,老人停不下来,一辈子停不下来。他脱下布鞋,拎起来说:“瞧,我死了,就把这鞋留给儿子,叫他穿上,带着孙子,继续治沙。”
回到住所,见到了那张贴在墙上的治沙歌:“家住长城乡,紧靠黄沙边,带领家人进沙滩,住进了沙窝漩;手拿‘沙漠枪’,老伴紧跟上,治住了沙坡头,后代们有盼头……”
王天昌老人坐在条凳上,头颅高高扬起,眼望着茫茫无边的大漠,转轴拨弦,纵情吟唱。他弹的是凉州贤孝,这苍凉的声音,粗砺而豪迈,卷夹着十八年的雨雪风霜,自红水河上空响起,飘过腾格里沙漠,飘向凉州城的每一个角落。
一个人,一杆枪,抗击沙漠。一首歌,一辈子,歌唱沙漠。
归程,腾格里渐不可望,凉州城大雨如泼。这雨水,一如老人念孙时,那汹涌决堤的泪水,怎不叫人感慨肃穆呢?
作者简介:秦不渝,原名王刚,甘肃省作协会员,武威市作协副秘书长,“凉州听雨楼”微信平台创始人。作品刊发《飞天》《长江文艺》《今古传奇》《甘肃日报》《華夏散文》《西凉文学》等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