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生《穿越苍凉的城镇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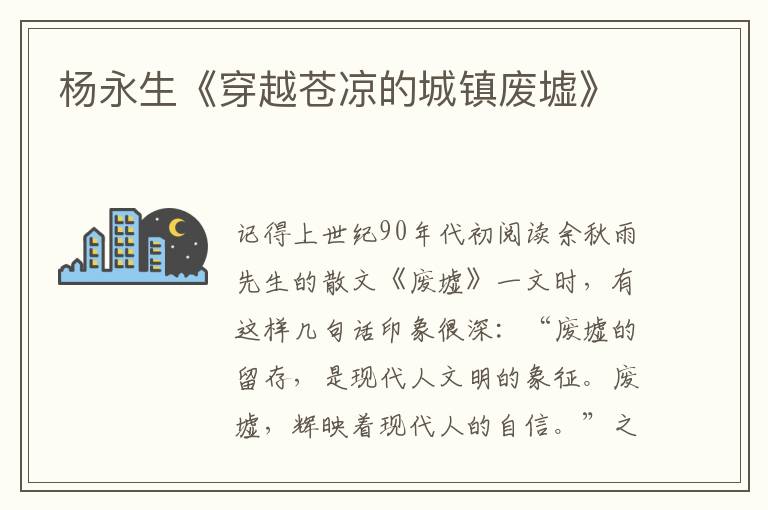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阅读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废墟》一文时,有这样几句话印象很深:“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之所以重温余先生有关废墟的话语,是因为我在走向草原冰川的途中,一次次穿越了或大或小的城镇废墟,让我的思绪缠绕在废墟的上空,久久盘旋,一种寂寥、落寞和惋惜的情绪,无以名状,欲说还休。
当我们的车队又一次穿过位于阿克塞县博罗转井镇的老县城废墟时,我的心还是微微颤动了一下。坐落于阿尔金山东段北坡中腰,海拔2600米的阿克塞老县城,在她作为现代文明的城市生长繁育时,我曾多次光顾于她,熟悉她的街衢、脉络和气味,熟悉她民族的滚烫豪情和坚韧的精气神韵。我曾在阿克塞老县城钢筋水泥铸就的楼前院落里,见到了悠闲自在踱着方步的羊群;在山坡的草地上听到了冬不拉弹唱的哈萨克民歌,看到了羊群在音乐声中陶醉吃草的优雅景致;还是在这座小县城中我吃着鲜美的羊肉,在哈萨克朋友优美的歌声中喝完了一杯又一杯美酒,穿着她们民族的服饰,摇摇晃晃地翩翩起舞。这些人类和牲畜和谐生活的场景,随着1998年因海拔过高而将这座城市遗弃,瞬间的废墟便接踵而来,铺天盖地,势不可挡。有时候就连我们人类自己都吃惊,我们建设一座城市时是那样的艰辛和漫长,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子子孙孙,薪火相传呀。可是,破坏一个世界,废弃一座城市却是如此之快,轻而易举。我亲眼目睹了阿克塞的老县城演变为废墟的快速过程,以至于站在她的废墟上时,神情恍惚,匪夷所思。我低头怎么也看不见城市原有的轮廓,原有的生命,原有的生活气息。我惊叹于这座城市与昨天的断然诀别,与人类的无情告别,与大地休戚与共的血脉相连,怎么瞬间就沉睡于大地的怀抱之中了?
可见,文明大厦的构筑需要历经千难万险,而人类文明巨著的倾覆却是易如反掌的事。这可能是人类文明最终的宿命和定律。
从哈尔滕草原返回途中,我远远就看到了一簇建筑群落,走近一瞧,原来是一个废弃的乡政府驻地废墟,那破败的残垣断壁,孤零零的枯树干,残损斑驳的门楣及标语,向过往的人诉说着她曾经的存在和与人的丝丝情感瓜葛。如果不是她的周围有几峰骆驼在孤寂地吃草游离,真还感觉不到生命游动的影子。这个乡政府驻地,不管她过去的功用如何,但现在作为一个废墟存在于草原,远看就像是草原的一个霉斑,近看就是草原上一个撕裂的、流脓的疮口,不忍目睹。这样的废墟,这样与周围景致格格不入的废墟,应是早早归沉于大地的海洋,融化为草原芬芳的泥土,才是她应有的生命归宿。
翌日,我们的车队穿越玉门市茂密的“风车森林”,来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玉门老市区。1939年8月,玉门油田的第一口油井——老君庙油井出油,自此中国石油工业的生产拉开帷幕,玉门在此设市建城。历经70年的石油开采炼化,玉门油田原油开采开始枯竭,加之油矿居于22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玉门市政府和玉门油田生活基地先后实施了异地搬迁,玉门老市区又慢慢成为一个被废弃的城市。我们的车队穿行在玉门老市区的街道和楼群中,城市破败的境况虽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但许许多多楼房都被拆除了门窗,院落或楼门被封堵了起来,部分城市公用设施已经关闭,街道上的行人稀少零落。刚好是中午下班时分,仅存的炼油厂等几个单位的下班职工,稀稀拉拉地步行去吃午饭,往日最热闹的街心公园内,也不见人影,只有中国石油地质师孙健初的雕塑像孤立其间,静守着衰落的城市和寥落的居民。石油是这座城市赖以生存的命脉,石油枯竭了,依附其生活的城市和人群终究是要衰亡的,那只是个时间问题。她的结局不难预料,往近比就是阿克塞老县城废墟;往远比,就是我们境内的锁阳城遗址、桥湾城遗址和周边的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
锁阳城遗址、桥湾城遗址和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在国内外考古、历史和文物学界都是大名鼎鼎的。我曾多次前往这几处废墟遗址考察,就在这次去草原冰川之前,我刚刚又去拜访了她们。
锁阳城遗址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历史延续时间最长的古城遗址。她始建于西汉时期,绵延1500多年时间,城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城墙总长度6.4公里。因疏勒河改道和云谲波诡的征战变迁,锁阳城终被遗弃在历史的风烟中。站在她高耸的城垣上远望,可以看到西部最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胜迹。我所认识的甘肃诗人徐建群看完锁阳城遗址后,赋诗叹曰:“烈日蒸云在晋昌,无边戈壁最苍茫。登高不望祁连雪,何处花开有锁阳。”
因"康熙夜梦桥湾城"的历史故事而闻名遐迩的桥湾城遗址,城郭残损的轮廓依稀可见,只是曾经气势凌人的康熙和傲骨凿凿的城垣,都敌不住时间的漫漫侵蚀和历史的层层拷打,她的城垣已被滚滚黄沙和连绵风雨剥蚀的不成样子。好在她又被现代人赋予了反腐倡廉的时代主题,展览厅中陈列的“人皮鼓”,娓娓地向人们讲述着康熙大帝惩治腐败的绝敢气势。桥湾城遗址只能凭借“康熙夜梦桥湾城”的历史故事,生动鲜活地珍藏在历史典籍中了。
据史家说,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在西汉时期就是居延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她地下出土的文物,占了已知出土的西夏文献的90%,其文物价值难以估量。这座城市的废弃,源于1226年成吉思汗率兵破城,明朝初年再次破城而致。“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战火的连连焚烧和人为的杀戮劫掠,今天残存的黑水城遗址,已被流沙重重地湮没殆尽,废弃近700年了,一切也在情理当中。而黑城昔日的繁忙和辉煌,我们只能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和清代《重修肃州新志》中的有关描述来领略和感知。
对于城市的遗址和废墟,我经常处于一种两难的矛盾心态之中,让她任其自然荒废遗弃吧,因与人类有过亲密无间的生命缠绕和厮磨,心理上难以顿然隔别,怀旧和思念过去又是人类情感的依托和慰藉。何况,她毕竟投入了一代代人的汗水和心智,她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人类摩挲的痕迹、体温和气味,间或闪现出人生命的影子。正因如此,余秋雨才说:“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碾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
有心全都将城市废墟精心呵护保存下来吧,人类投入的财力又过多,耗费的精力又过密,投注的情感也会越来越浓郁,牵扯掺杂的经济、文化、历史、军事和情感的因子太过稠密。让城市的废墟承担了太多太多的重荷,相应地,曾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人以及她的后辈们,心灵上背负的重担也就不会轻松。如果让城市的后来人都承载着代代层累的厚厚历史赶路,细碎的脚步能快得起来、能走多远,还能看到天高地阔的美景吗?而地球上如果摆满了人类建造的一座座城市废墟,无论我们走到哪儿,举目望去都是一片片城市废墟的海洋,一座座城市废墟的森林,我们的视野该怎样穿透城市废墟投向蔚蓝色的大海、翠绿的森林和辽远的天际。当地球村被人类开凿成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城市废墟的世界时,我不知人类的精神该皈依何处,人类的灵魂应安放哪儿?
正因如此,余秋雨又发出了“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的无奈声音。
我絮絮叨叨说了半天,还是割舍不下这一座座遗址和废墟。那就让我们裹挟着被提纯清洁了的废墟的神脉,淡然走向现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