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回忆“杭州座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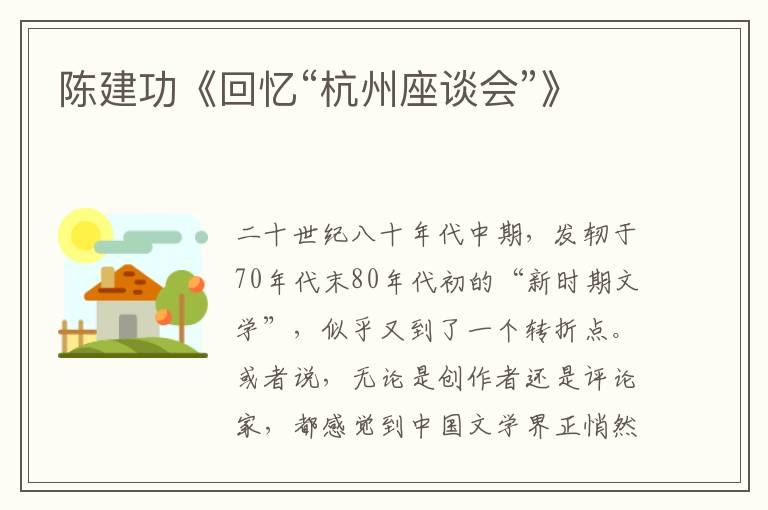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轫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似乎又到了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家,都感觉到中国文学界正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萌生着一些新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1984年年底在杭州展开的那场青年作家与评论家的对话,是应运而生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前瞻》——会议的议题是平实的,却提供了话题纷呈的可能。然而会议的成功似乎还不能仅仅归结于议题上。那个时代的文学,还保持着激情——作家评论家们都秉持着升华民族情感和丰富民族审美经验的“己任”,还洋溢着刚刚被释放出来的个性化的豪迈。那日子,颇有点建安时代的气氛,人人都有股子“抱玉握珠”的自信。当然,我那几天倒是没精打采的——从会议开始,就捂着肚子,一边为李陀吴亮们新见迭出击节而叹,一边被不争气的肠胃炎所困扰。与会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多是当时文场的猛将,几乎每个人对创作的动向都是敏感的,开会前似乎也凝聚了太多的思想能量,所以各个才情迸发宏论滔滔,比如关于小说叙事的“多样化”问题、文学批评的传统与创新问题、“语言”问题、现代主义问题,等等。三十年后,仍见有研究者提及这次座谈,认为它对1985年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影响巨大。甚至有论者认为,此后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的出现——“寻根文学”,正是得益于它的“催生”。
作为参会者之一,说是“躬逢其盛”也好,“忝列其中”也罢,面对研究者的言说,都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不过,在我看来,一个阶段的文学转折或取得突破性成果,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那儿,作家的情感和思考聚积到了那儿,当然,时代的火花也迸发到了那儿……因果关系或许是有的,但“因”并不单纯而绝对。当然,这次“回顾与前瞻”对文学的发展有所助力,无论大小,确不应湮灭。一群思想和才情都属活跃的人聚集一处,发出真诚而有趣的声音,唤醒同仁乃至更多的人解读生活、思考文学,对创作的走向,题旨和审美的开拓,有所推动,是值得赞赏的。我对这次会议也有很深的印象。首先是它直面文学实际的坦诚,不管提到什么作品,是称许还是批评,都无须顾及什么情面,也无须左顾右盼,而是专注于作品为文学发展提供的可能和启示。这种讨论的气氛,现在已难得一见。其次我还赞赏它的平等。不管是创作者还是批评者,不管是新秀还是前辈,更不管是为官还是为文,大家尊重每一位言说者的看法,就算某位言语激烈见解偏颇,也不见谁“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顶多了,有人有点儿“不敢苟同”的微笑,最终,还是有所启示的欣然。我至今还记得当年茹志鹃李子云等几位前辈倾听的神态,那神态被永远定格于1984年岁末的晨光里,告诉我们那个时代做文学,实在是一件轻松而愉快的事情。
我记得轮到我不得不发言时,会议已近尾声了。大家谈得昏天黑地,也顾不上一直捂着肚子躲在角落的些小吾曹。到了最后一天的清早,(黄)子平兄送来了两包“保济丸”。那两袋药丸果然神奇,驱妖降魔般使我的肚痛了无踪影。这才觉得“捂了几天肚子,屁都不放一个”,殊为不妥。当然,发言在心里也是酝酿了很久的。想说的是,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在剧变。作为一个作家,在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上求变,迫在眉睫。当着满堂的文学理论家,我觉得用口语化来表述似乎更好些。于是在发言时就改成了现在所见到的——“我别无他念,就是在琢磨‘换一个活法儿,换一个想法儿,换一个写法儿’。”我没想到30年后还有人会回望一下这次会议,更没想到有人会注意到这三个“换”,这便成了最近湖南一家文学理论和批评杂志约稿的话题。约稿者称:“这喊出了一个作家力图契合文学发展内在要求的呼声。”又说它可为重读“寻根文学”提供一些背景,对当下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发。
还是说过的那句话,那个发言不过是个人在面对转折时的一点儿心得。当然我可以证明的是,当年那些“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们,在80年代中期所开始的创作,的确是有着理论的自觉和文化之思考的。那种“自觉”和“思考”,从他们当年的文章里,可以一览无余。
那么,回顾一下我当年的心态。
“换一个活法儿”,其时是大多数中国人“走进新时代”的念想。“活法儿”一说,是那时时髦的“北京话”,之所以时髦,应可看出澎湃其间的“走异路,寻他乡”的人生渴望。同样,关于“活法儿”的思考,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更为峻切。经过新时期文学的崛起,过去年月的遭遇和感受,已经写过不少,但面对新的现实,作家们大都有人物积累情感捉襟见肘的危机感。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海明威所讥讽过纽约作家的一段话是刻骨铭心的。他说,纽约作家们不过是试管里的蚯蚓,他们只知道互相吸吮着别人身上的养分,其实已经失去了广袤的空间。(大意)“换一种活法儿”,传递的就是作家对“现有的”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的某种危机感,表达了对新的情感资源的渴望 。
“换一个想法儿”,其实是对思维角度和思想资源的期待。就拿新时期文学来说。我们经历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到了80年代中期,仍使文学停留在一般的悲情诉说和社会批判层面,是不是过于肤浅?文学能不能向历史的、民俗的风貌和心理的深层结构开掘?再者,文学是不是应该而且可以为民族审美经验的丰富与提升有所贡献?若可以,到哪里去寻找、借鉴,如何进行尝试?……当然,社会生活以及创作实践向作家们提出的问题是多向度的,也还不仅止于文学本身。而思考方式的更新,又与形象思维相交集,很难一言以蔽之。不过,思想的匮乏的确是令当时文学界焦虑的话题。当年读到前苏联文学理论家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的发展》一书,他指出,我们总是指责苏联作家们没有生活,其实他们最致命的问题是——没有思想。我得承认此话使我有振聋发聩之感,“换一个想法儿”之说,得益于他的启示。文学发展的实践也证明,思考方式的更新和创新,为文学新境界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如前所述,“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典型的范例。寻根文学,从其酝酿之日就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理论自觉,要突破悲情诉说和社会批判层面,使文学向更广阔、更具深度的领域走出的坚实一步。在叙事美学方面,寻根文学对民间文化精华的撷取、海外文化的借鉴也有诸多自觉的尝试,其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最后,“换一个写法儿”。其实指的就是作家“创新”和“变法”的自觉。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统的“典型化”的创作手法已经受到挑战(尽管时至今日,有资格进入我们的“典型画廊”里面的人物,依然寥寥可数。)“各式各样的小说”(李陀语)和形形色色的流派尝试,已经登上当代文学的舞台。文学既是创作,冲破陈旧僵化的藩篱,大胆运用新鲜生动的语言,根据所欲言所欲诉,寻找最美的表达方式,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非但不是对传统的抛弃,而是对我们民族审美经验的丰富与提升。“换一个写法儿”,其实就是为了传递这种艺术变法的理念,并不是要赶时髦。当然,随着中国作家创作实践的展开,对“换一个写法儿”的思考早已愈发深化了。比如对传统审美经验的“颠覆”,如何和哗众取宠相揖别,真正展示艺术征服的魅力?对语言创新的追求,如何和佶屈聱牙相揖别,真正营造为中国读者所倾倒的语言世界?对海外文化之优长的借鉴与汲取,如何与生吞活剥相揖别,化入中国个性的表达……不仅仅是理性的思考,就作家的创作实绩来看,也已经丰富得多了。
30年旧话重提,还有啥用处?于我,不过是因为有文债追逼,又先有了命题,所以才荡漾起旧事的涟漪罢了。当然,为专注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朋友们,提供一点儿当年的思想痕迹,或不无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