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烽燧》李振娟散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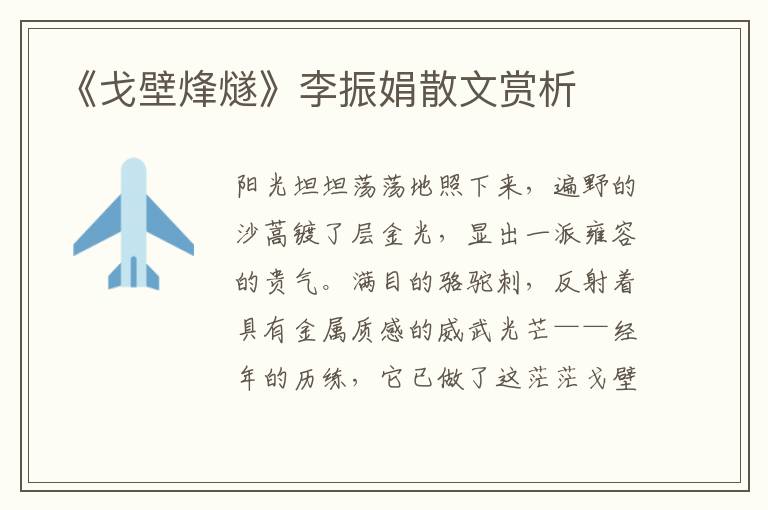
阳光坦坦荡荡地照下来,遍野的沙蒿镀了层金光,显出一派雍容的贵气。满目的骆驼刺,反射着具有金属质感的威武光芒——经年的历练,它已做了这茫茫戈壁的山大王。七月的毒日头不依不饶地炙烤着荒原,才翻过了三座山,我就喝干了军用水鳖子里的水,站在山头上淌汗喘气。远远地,看到前方山峰上的大土墩子,不消说,就要回到厂里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天,我们举家随父亲“农转非”踏进青铜峡铝厂时,我就对着这座大土墩子注视了很久。平生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土墩子,又高高地矗立在山巅上,且无论春夏不论寒暑,总是纹丝不动地矗立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仿佛一本厚重的史书,沉甸甸地占据着我的心。直到在铝厂学会了普通话、走惯了沥青路,一天,围坐在厂东大门对面的家属院前,听一位老技师指了指不远处的大土墩,神情庄重地说:“那,不是一般的土墩子,那是明朝时期修建的烽火台,曾历尽战火,现在烽顶上狼烟熏过的黑印子还在。”
此后,每天清晨出门,我都会站定,痴痴地朝东望上一会儿,饱含古国沧桑的烽火台,它的亘古、它的神秘、它的静默,让我很快收拾起零散的心情,端庄地开始新的一天。
出生在乡村的我,在泥土芬芳中度过了整个童年,搬入工厂之前,我整天关心的是老院子里储满古老传说的老槐树,深秋黄叶落尽后,那曲虬的树杈又多了几个喜鹊窝;惦记着院门前的小溪,雨后的鱼群会不会此起彼伏腾跃得水花四溅;比较着翩跹在土豆花海里的蝴蝶,到底是花蝴蝶的舞姿优美还是白蝴蝶的舞姿优美。我寻思盘腿坐在堂屋炕上念佛经的祖母,是不是仍旧闭目重复诵念着阿弥陀佛的佛号;在麦田里除草的母亲,是戴着草帽还是扎着花头巾;村头铁匠铺的铁屑堆里,扔下的那些像马像狗像鸡的废铁屑,会不会又被小伙伴们抢光……
举家搬到工厂后,厂房、高压线、大烟囱、沥青路、电解槽、铝锭、铸造机等,由陌生到熟悉再到亲切,它们散发出来的金属气息逐渐取代了乡村的泥土气息,一点一点融入我始于工厂的青春。在厂里,我经常会看到下班后仍然穿着灰色工作服的工人,三三两两勾肩搭背有说有笑地去小饭馆吃饭;骑着老旧自行车上班的老厂长,神色凝重,若有所思,过往的职工向他行注目礼也浑然不觉;留着飒爽短发的青年女职工,穿行在沥青路上,洒下一串爽朗的笑声。静谧的夜晚,我时常回味着这些情景,枕着远处厂房传来的时远时近的机器轰鸣声,安然入梦。
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漫步到厂东大门口驻足眺望古烽燧——天空辽远,淡云悠游,没有飞鸟,也没有昆虫。天空下面的戈壁上没有绿树,也没有青草,没有任何能够证明风存在的植物。掀动衣袂的风吹过去就没了踪迹,丢失了。茫茫荒原,惟有这座古老的烽燧,寒来暑往,饱经风霜,无言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与站在村口眺望田野时那种甘露沁心的清冽不同,在工厂的东大门口眺望古烽燧,西部边塞的浑厚、苍凉、辽远会让我心中顷刻涌上一股难言的怆然,眼前浮现出丝绸古道、迤逦驼队、骁勇马帮……庸常的日子里,只消驻足朝它望上一会儿,俗世里钝化了的心,很快被激活了,涌动起诗歌、梦。
那时,每逢周末,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都会相约一起去爬山。我们背着双卡录音机,带着军用水鳖、茶叶蛋,走向戈壁深处的山脉。录音机里回放着《海阔天空》《一路上有你》《忘情水》《大约在冬季》《同桌的你》……歌声在山脉间回荡,男生站在高高的山峰上情不自禁地对着山谷吼唱,唱到动情时顺山脉飞奔而下,引得女生笑得前俯后仰。有的同学干脆不管不顾,在平坦的山腰随着奔放的旋律跳起了迪斯科,摇头甩胯,沉醉不已。歌声、笑声、踏踏的舞步声,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戈壁山塬。
尽兴了,疲惫了,该返回了。翻过几座山,到了最后也是最高的一座山时,烽火台就矗立在我们面前了。此时,夏日午后的太阳暑热不减,我们舔着干裂的嘴唇仿佛奔向甘泉般疾步朝烽火台斜切下的一片阴凉走去。每次爬山回来,我们都把烽火台当作一个驿站,在它凉爽的背阴里缓缓劲、歇歇脚,整理一下行囊,简单地道别后,各自回家。在那些闪光的日子,少男少女的心里,满满的都是情愫和憧憬,再也装不下他物,一次次误把这座承载着历史烟云的烽燧当作歇脚处。
大专毕业后,作为一名国企子弟,跟大多数国企子弟一样,我没有太多的迟疑就循着父辈的足迹回厂里上班了。头一个月发工资,买自行车,买皮鞋,买皮包。自此,每天穿着皮鞋、背着皮包、骑着自行车,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涯。
工厂方圆五里大,跟村庄一样,处处都是熟人。休息的日子,我会打扮一新,到公园、广场、柏油路上溜达,遇见熟悉的大妈大婶嘘寒问暖,遇见要好的小姐妹诉一诉心事。若是获了先进评上优秀,厂里的无线广播会播放几天。这样的时候,心里就美滋滋的,真想把那光荣的日子永恒定格。
起初的那些年,每天充实地工作,逢年过节全家人聚在一起包饺子。至于工资,心里是没有多少概念的,那时干部职工都拿的差不多,住的都是厂里分配的60平米砖混家属楼,都是骑自行车,夏天吃小白菜冬天吃大白菜,过节吃厂里发的米、面、油、肉、鸡蛋。
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后的一个春节,分厂工会主席组织各车间职工代表给分管副厂长张厂长拜年。要去厂领导家,心里是忐忑的,一路上想象着领导家的高门槛、气派的门楣、考究的摆设,不免心生敬畏。临近午饭时间,我们到了张厂长家,我怯怯地打量了一下,心里顿时放松了,原来张厂长家和普通职工家没什么两样,也是两室两厅的砖混家属楼,房间里摆放着几样古朴的木制家具、一台20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最出乎意料的是,张厂长家餐桌上正端上来的居然也是一大盘普通职工家饭桌上的大烩菜,香浓的热气正冒着。“嗬!这正好,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来来来,大伙儿一起吃,一起吃!”系着围裙的张厂长热情地招呼着,张厂长夫人更是忙不迭地沏茶斟酒,俨然邻家大叔大婶。我的疑虑顷刻打消,八个人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起来。大家吃着喝着聊着,张厂长如数家珍地讲着厂里历年的国家级、省部级劳动模范和那些获得国家技术专利的项目,讲到动情处眉飞色舞:“你说吴升升那家伙,一个瘦高个,饭量也不大,咋就那么大精力,能耐大得很,把一区的电解槽子捣鼓得灵便得很,尽出双零铝,那在伦敦交易所吃香得很!”一高兴,大伙儿酒杯就频频地碰了起来,已分不清哪是领导哪是职工了。
那时,我对外面的世界不大晓得,每天对着厂东大门外的古烽燧望上一会儿,联想一下古国风云战场硝烟,就回到宁静如水的日子里。反正要终老在厂里,就像父辈,所以并不曾担忧未来的日子。
多年以后,我有了家有了孩子。此时,市场经济呼啸而来,房价翻倍,物价飞涨,孩子的择校费飙升,而各地国营民营铝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很快产能过剩,铝价下跌,效益连年亏损,职工工资持续下降,生产线被迫拉闸。每个月精打细算,微薄的工资仍然难以为继。国企子弟、国企职工,这曾经让我自豪、让我衣食无忧的身份,而今提及,恍然如梦。
随工厂浮沉二十年,再眺望这古烽燧,我有一种想对它倾诉的渴望。那是一个阳光尚好的秋日,我踩踏着沥青路边的落叶静静地向它走去。二十年了,烽火台还是初见时的样子。近处,戈壁,山脉;远处,仍是戈壁,山脉。远远近近都是黄土、沙砾、骆驼刺,偶然遇见一两株马兰花,瞬间点亮眼眸。二十年过去了,戈壁草木荣枯,工厂世事变迁,我也从亮丽青春走到沧桑中年,而古烽燧依然巍然屹立,不可动摇,一如英雄的梦想。
从我踏进工厂,它就屹立在那里启示我脚踏实地劳动、生活。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虽然付出比往昔更为艰辛的努力,我们的工厂仍然无法再现曾经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荣光。而今,古烽燧仍旧那样静默地注视着工厂,注视着曾经高压线如织、管网密集的现代化厂房日渐陈旧沉寂,注视着曾经柳树成荫、槐花芬芳、玫瑰花遍地的园林式生活区越来越破败、萧条,注视着曾经爽朗自豪的工人越发沉默、不甘……
遥想五十年前,西北这片戈壁,如同西北大地上所有的戈壁一样,黄土,沙砾,时断时续蜿蜒着残破的明长城,或东或西散布着古烽燧,精瘦的养只,机警的马蛇子,漫无目的四处飘荡的风——眼前的这座古烽燧和戈壁上所有的古烽燧没有两样。若不是那时在这里建成这个工厂,我的父辈、同辈、晚辈们的目光又怎会相继眺望它五十年之久,直望得它四周的戈壁也通了我们的情意,有了慈祥的面目和温暖的色彩。
它屹立在这里五百多年了,任岁月剥蚀,风霜浸染,风化了棱角,脱落了表层,与戈壁黄土的颜色融为一体。站在它矗立的位置俯瞰工厂,我们的工厂微小成了一片灰色海洋,厂房、烟囱、高压线、管道、家属楼都小成了一个个点、一条条线、一段段面。曾经完成一次次国家经济建设使命,曾经培养出一个个技术精英、劳动模范,曾经的勋章,曾经的丰碑,那一声声劳动的号子,那一串串熟悉的名字,都沉淀在这片小小的灰色海洋里……
屹立了五百多年的戈壁烽燧,与工厂相望,它在后来的五十年里受到了我们几代产业工人的庄重注视,饱含了工人的情意,成了一座有情的烽燧。我不知道我们的工厂会存在多少年,还能存在多少年,就像我不知道这座已经存在了五百多年的烽燧还能存在多少年,但它必将伴着古烽燧的沧桑,载着一串串劳动者的名字,汇入工业历史长河中,向永不止息的未来滚滚而去。
神驰间,阵阵凉风过耳,不知不觉,晚霞已从西边洇了过来,浩瀚的戈壁一片金红。极目处,金红的戈壁和彤红的天际融合在一起,消解了天地间的所有忧患。这一刻,瑰丽的晚霞镀在古烽燧上,站在厂东大门的方向回望,它仿佛一尊古老的雕塑,庄严,厚重,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