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瓦》孔帆升散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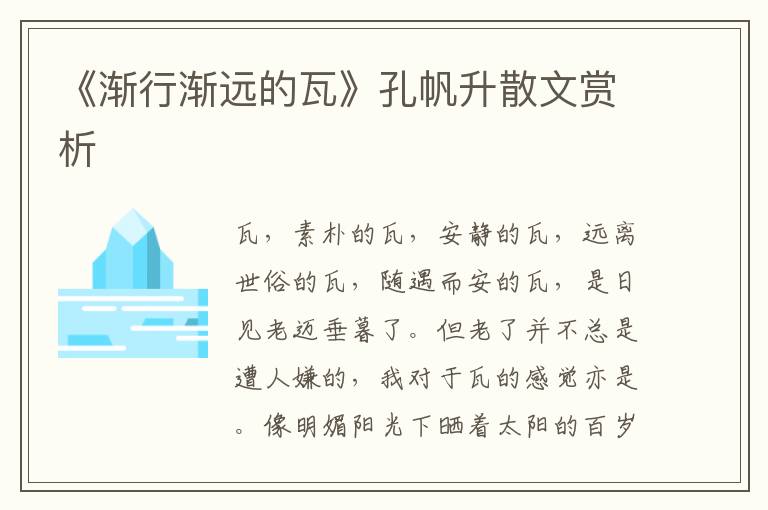
瓦,素朴的瓦,安静的瓦,远离世俗的瓦,随遇而安的瓦,是日见老迈垂暮了。但老了并不总是遭人嫌的,我对于瓦的感觉亦是。像明媚阳光下晒着太阳的百岁老人,他们慈眉善目活菩萨一般令人感到亲切。每回路过乡下屋场,我总忍不住停下来,好好看上村庄几眼,用眼睛和心灵说上两句话。
每去乡村,第一眼瞧的大都是瓦屋,然后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一沟清水,一两棵百年古树,或者一两条水牛与一两个荷犁男人。要是没有,我倒是想一个人坐在田埂上,摊开一张素纸画上心头的欠缺,这样也就 不枉又一次亲近土地与乡村了。乡村的元素在心底发酵、酝酿与生发,唤起我最亲切、最美好、最心之所系梦之所萦的乡情。重重叠叠、高高低低、方方圆圆、弯还九转、鳞次栉比的瓦屋,是何等巧妙的美学构图,勾起多少温柔的情愫!乡村亲我懂我,正如瓦在山水间静谧成古朴之风。有时不免生出忧郁感:这样的画面怕是早已生疏,快要别离了。
瓦把一生都交给了人和房子,像三从四德的女子。房子是土巴墙的,它安贫;是金碧辉煌的宫廷,它安然。房子是怎样形状,它就是个啥形状,或歪七斜八,或端庄雄伟,这些都改变不了它承天接地、遮风挡雨、营构温馨家室的本性。瓦是多么慈和啊,排列成人字形的屋脊,盘龙的屋垛,吉祥鸟的屋角,怎么着都不会张牙舞爪,都能給人一种熨贴。屋场里的静谧或偶尔高一声低一声的俚语,在瓦的庇护下,更加深了时光慢慢、日子长长的味道。每一条东流水与西流水,都会很好地配合老屋倾诉乡村的厚重。
瓦是大地使者,以仰望的姿态承接上天的眷顾。南方雨量充沛,尤其是春秋两季,最是雨打瓦屋如弄琴,催醒了大地上每一个蓬勃的生命。瓦片上的雨声丝丝绵绵,梦一般带给人幻想,陶醉了一样铺开了新景象,花就凌寒开了,叶也就浓重起来,被风熏染得色彩缤纷。我想,我这忧郁又阳光的性格是否也与听雨有关呢?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屋檐滴水点点不移”,听不明白却总是痴痴地看石板上留下的滴水痕迹,想探究水为何这么不厌疲倦地做着毫无意义的事。中年后才领悟到瓦从容的倾诉里,有着亘古的人生寓意,只是这哲人般的举动鲜有人真正重视过。我们更多的时候脱离了瓦的影响,变成了泛流,变成了漫涌的洪水,漫无目的地乱撞。
倘若时光回溯,我愿与相爱的人共处山野一室,静静聆听水滴的声音,听它对星空、云霞、山花乃至一只喜鹊与猫的絮语,忘了世外纷争。
可惜童年少不更事,哪有心思与情怀去关注与温饱和快乐无关的瓦?
我瓦下的日子,蚁一般不堪一提,又常常忍不住要怀想。也许人生注定要有那些贫瘠,那些简陋与闭塞,才可丰富得足以令人追记。几片薄瓦,盖住了白天的繁重与喧闹,盖住了那些从梦中惊醒的惶恐与惆怅,青涩的时光一分一秒在风吹瓦屋木窗的呜咽中,慢慢镀色,形成自然而然的抵御。日子就这么翻过了一页,却又不知下一页要如何去翻动。碎与不碎,遮不遮风,挡不挡雨,谁也说不定。我们过的就是瓦一样纯粹、脆弱、安分、不变的日子,从来没想过会离开泥屋,离开大山,离开牛羊鸡犬耕织的田地。你耕田来我挑水,男耕女织的生活,是多么令人神往,却又何其难遇。在县城住了几十年,每天看到高楼,看到粗硬的钢筋水泥结构,心也磨起了茧,不知不觉间就恋起瓦屋,哪怕它是埋在心中的伤疤,也要毫无羞涩地展示。因为,它是最人之初的具象。
我印象中的乡下并不总是明媚的。阴郁的日子,忧伤的情绪如柴火焚烧过的烟,从来不往地下钻,它越爬越高,钻过瓦床,冲出屋顶,忸忸怩怩,恣恣扬扬地飞上天,弥漫在整个村庄里。天灾人祸的时候,这种氛围分外浓重。尤其是乌鸦,呱呱地叫着,谁都怕它落在自家屋顶上。可是,又有哪家能绕得过生离死别呢?
瓦是有安抚魂灵作用的。农人活着上有片瓦,是种安慰,死去了,有瓦相伴也是不错的。其实,老人大都有了瓦的性情,把死当成瓦脱胎于泥土,用另一种形式存在。一丝魂儿悠着,说去未去,似已撒手人寰,就有人用三片瓦慎重其事地给躺在木板上的老者枕于脑后。农村里都把丧事热闹着办。吹吹打打,唱唱叹叹,这才是一种完全,瓦全,是对将远逝者最贴切的慰藉。一个人在土地上生活了那么久,即将回归土地,泥瓦便是最好的祭奠,最好的通行证。倘若有一两件烧制品如水壶之类伴之,在那头也不寂寞孤单了。至今,我仍然痴想:那些去了天国的祖人,因为其勤俭善良,总会有一丝灵魂缠在老屋的上空,以便后人追思。就像那瓦,在现代人生活中没多大用处了,但它仍然是一种传统,一份情结,对人的灵魂总会有清洗过滤的益处。我想我这是在对抗某种遗忘,对瓦,我们该永远怀一份诚挚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