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里乾坤大》吴昕孺散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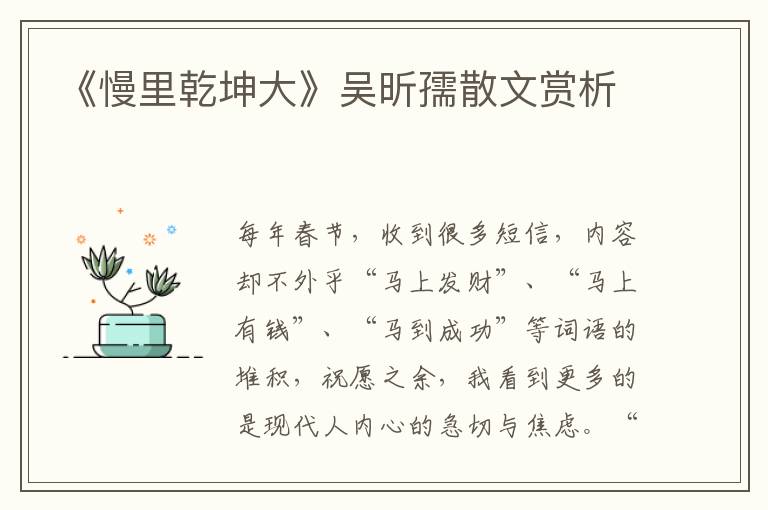
每年春节,收到很多短信,内容却不外乎“马上发财”、“马上有钱”、“马到成功”等词语的堆积,祝愿之余,我看到更多的是现代人内心的急切与焦虑。“马上”的本义是马背上。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满腹经纶的太中大夫陆贾,时常在汉高祖面前谈诗论经。高帝骂之 :“乃公马上而得之 ,安事《诗》《书》!”陆生答曰:“马上得之 ,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到了唐代诗人孟郊的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里面,走马看花就有了迅疾之意。直至清末,“马上”开始成为“须臾”、“即刻”的同义词,并因更为简洁通俗而成为无数中国人的口头禅。
将一个空间概念强行转换成一个时间概念,说明人们对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到了现代,他们恨不得把空间全都换成时间,于是才有涸泽而渔式的开发、敲骨吸髓式的利用和焚琴煮鹤式的娱乐。现代人拼命勒索资源与时空的架势,大有路易十五“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鄙吝与贪婪。
慢,渐成过往。现在你即便想慢下来,也好比是在火车上打坐,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焉能容得下你的悠哉游哉!慢镜头,必须回放;慢节奏,必须回顾;慢生活,必须回忆。而慢,已然是发黄册页里的那些清茶淡饭、衣香鬓影,闻其味不知其趣,睹其形不见其人。
据说,上帝创世时很是性急,他用七天时间就创造了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飞禽走兽。造成之后,他就后悔了,愧疚于自己的随意、草率,万物有如刍狗。于是,他决定静下心来,完成一个完美的造物:人。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道出了上帝造人的真谛:“上帝的磨盘转得很慢,却磨得很细”。的确,上帝给予人的一切配置,都体现了一个字:慢——慢慢发育,慢慢成熟,慢慢死去。人是万物之灵,可人的发育在动物中算是很慢的,三岁的母马可以产仔了,而人在三岁还是婴孩;三十岁的马处于临终状态,人类此时却正当盛年。在早期发育的每个阶段,人类都被其他动物远远甩在后面。小猫降生不久就能横穿房间,几周后能抓老鼠,而婴儿要花上几个月才能迈出第一步,几年后才能学会系鞋带。人类飞不过鸟,跳不过猴,跑不过羚羊,力不过虎豹,然而,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看看我们的人类世界,再看看其他动物们的世界,便知道上帝有多么偏心了。
人类的所有趣味、情感、思想、智慧,都从慢中得来,在慢中消化、凝聚、升华。一旦加快,人类就变得寡淡、无聊、自私、暴戾,就和其他的动物无异。在人类慢的世界里,那些生长迅速的草木、虫鱼、鸟兽都无一例外地成了人类悠闲生活的背景与工具:
唐人陆羽写茶:“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茶之牙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
清代文人李渔写鸟声:“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鸟音宜晓听……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鸟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也,此其独宜于晓也。”
法国人法布尔写昆虫:“蜣螂在神圣地滚动着它的圆球,好像是清道夫在解释星体运行;蝉在地下的黑牢里,一年又一年地谱写夏日交响曲;蟋蟀在圆窗口、在草影中拉琴,遥远而浩大的银河并不让它气馁。”
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写树叶:“我坐在小白桦树边,满心想听听小叶子颤抖的簌簌声,却什么也听不见……苍头燕雀趁机一个劲儿欢叫起来。听它欢叫,真叫人兴奋——你会想到,生活在大地上是多么美好!然而我真想听听那棵白桦树上浅黄色、亮闪闪、有一股清香、还不大的落叶的簌簌声。不!它们还是那般幼嫩,只会颤抖、闪光、发香,不会作声啊。”
可见,人的生活节奏一慢,就有了闲情、逸志和雅趣,他们对大自然的体悟与认识,那是行色匆匆的花鸟虫树们自己永远无法抵达的。因了慢,人类藉此将自己的感知触角,悄悄地,远远地,深入到每一类事物的内部,窥探到它们奇妙的组织、独特的规律与幽秘的心灵运行。
与异种和他物的沟通、共鸣,是人类文学艺术萌生的必要条件。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有一首诗,写的是一个哑孩子千方百计去寻找他的声音。偷走他声音的是蟋蟀王,当哑孩子最终找到他的声音时,他欣然穿上蟋蟀的衣裳,变成了一只昆虫。这就像中国诗人顾城所说的,成为一名诗人要经过长久的等待,诗人需要混迹于上帝赋予的万事万物中,在那里慢慢发酵,好比水酿成酒,土冶成陶,丝织成锦,各种符号变成绘画、旋律和文章。因了慢,人们才开始在生活的腹地,构筑诗歌的城堡,树立美的信仰。我们不能只有“三天一层”的经济高楼和百十年一换的政治大厦啊!顾城说得好:“昆虫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没有妄想的生命,它不会变得很大”。这其实正是诗人自身的写照。
因为慢的指引,于是,我们看到约翰·缪尔像一只快乐的鸟儿,和一条狗、一群瘦弱的羊组成的队伍,一起走进内华达山区。大自然清爽的风像神谕般,从他的《夏日漫步山间》扑面而来。
我们看到约翰·巴勒斯在哈德逊河西岸筑起了自己的“河畔小屋”,他在《鸟与诗人》一书中平静地述说着麻雀飞过时翅膀发出的声响、海鸥有节奏的叫声以及松鼠隐藏在老橡树中的奇妙小巢。
我们看到梭罗向朋友借了一柄斧头,孤身闯入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树建造了一座小木屋。他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瓦尔登湖》既是文学经典,又是一种理想生活模式的写照。
我们看到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一个废弃农场居住了十三年,他不仅写出可以与大自然媲美的名著《沙乡年鉴》,还每年和家人栽种上千种树,完全以劳动者的身份,与土地打成一片。
我们看到约翰·布罗斯将一座谷仓改成了书房,他在那里与四面八方相接,每一件细小事物发出的哪怕是最为轻微的颤抖,都让他怦然心动。他说:“当外面大雨滂沱、树枝剧烈摆动时,我多么想听听它的历史和曾经摇过它的人的生平故事。”
我们看到林语堂提倡心灵的“边缘化”,用幽默和热情为人生的黑幕画出日月星辰。他希望千年之后的大街上,人们依然不是那么匆忙,不坐汽车,顶多坐坐牛车,最好是穿着拖鞋漫步,一边问候每一个行人。
我们看到韩少功决意离开都市,定居湖南汨罗八景峒水库边。他在那里读书、写作,也在那里种菜、务农。《山南水北》是在乡村漫长黑夜里熬炼出来的精神之火、灵魂之光,是从传统的劳动生活里掇拾的串串珍珠。
然而,在飞机、高铁与电脑的时代,慢显然早已不合时宜。人们竞相拥挤在快车道上,一门心思为了快发财、快晋升、快成功,甚至连快乐都被异化成了“快”乐。《说文·段注》说:“快,喜也。”可见,快乐本是一个联合词组,快也是乐,而不是时下流行的“尽快行乐”。“快”含有喜义,它表明的是一种心理感受,而不是物理速度。当代人正在努力用物理速度来取代心理感受,用感官来置换灵魂,用物质来消解精神,他们在功名利禄的快车道上不停地加速、超越,加速、超越……即便因高超技巧没有发生追尾和撞车事故,也会被高度的警觉与不断加码的追逐弄得身心俱疲,焦虑不堪。
中国人好酒,有联云:“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我不擅酒,遂改成:“慢里乾坤大,书中日月长”。以此自勉,并赠予有幸读到该文的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