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姝《水流休息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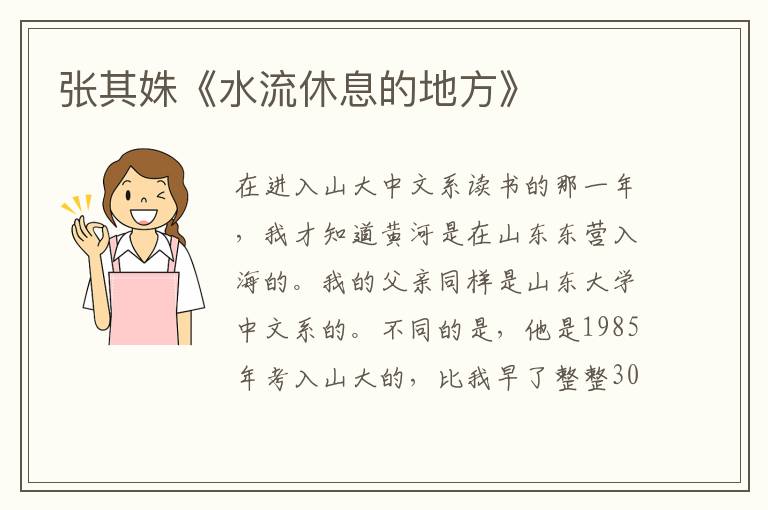
在进入山大中文系读书的那一年,我才知道黄河是在山东东营入海的。我的父亲同样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不同的是,他是1985年考入山大的,比我早了整整30年。由于同校同系的关系,我在家里常常戏称他为学长,然后被他笑我没大没小。
爸爸对山东的感情比起我要深厚太多,每当能从法定节假日中抽出几天来济南,他一定要坐在山大食堂里吃三个牛肉包子,然后去北门吃十块钱的把子肉。这个国庆节,他又不远千里从西安驱车赶来,说要带我看看其他的“学长”——他在滨州的“下铺的兄弟”以及东营的同学。
历史上的广饶、利津两个古县以及1943年才有的明显带有奋斗色彩的垦利县,构筑了今天的东营。作为方位指示,东营的“东”字,意思很明确。可为什么是“营”呢?细查,果然有故事。营,从宫,荧(yíng)省声。宫,房子,与居住有关。本义:四周垒土而居。营,有多个义项,基本意思有,军队,军营;军队的单位;筹划,管理,建设;谋求等。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帀居也。帀各本作市,今依叶抄宋本及韵会本订。考集韵作市,类篇,韵会作匝,葢由古本作帀,故有讹为市者。帀居谓围绕而居,如市营曰阛,军垒曰营皆是也。
我知道,看我这篇文字的人,不会把这段考据类的文字看完。即使偶有看完的,也是碍于情面、耐着自己的性子才坚持下来的。毕竟,我自己就常常这样。很多人都曾喜欢木心的《从前慢》。不知道木心写这诗时,是否想到了古人的话语方式?应该知道,我前面引述的那段需要耐着性子才能读完的、古人关于“营”的解释文字,是不可能在快节奏的阅读中完成的。它需要“慢”,需要一字一字地咀嚼式慢读。于此,忽然想到,我们所欣羡的“从前慢”是否也和从前的文字表达或话语方式有关?然而,生活,尤其是我们的生活,的确快了。
我知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迅疾如闪电的“快”,也让很多故事,包括我们的生活,只有结局没有进程。所谓“索然无味”,不过如此。
可是,东营,或者说我眼中的东营不是这样。
现在的东营,固然已不像古人解释得那样慢,但它依旧把残破的生活带到了水流休息的地方。在这里,鸟飞得慢,人走得慢。“清早上火车站”,虽然不是如木心描述的“长街黑暗无行人”那样,但绝不堵车。它永远都不会像长江入海口那样繁忙在金融的行脚里。
在东营,要想吃口好吃的饭,同样也慢。印象里,在东营吃特色的饭,比如河口镇的野生鱼,有点儿像从前的进京赶考,必须要走很长的路。所以,在东营赴宴,主人要有在包间里等待的耐心,客人要算好自己的行程。稍有差错,饭时就后延了。
诗人荣荣这样描写“知遇”:“走了很多弯路,只为遇见一个人/像一个砍柴的遇见一把磨快的刀。”当我们一家从济南赶到滨州去接我爸爸大学时的下铺舍友共赴东营时,我才知道弯路有多少重重——导航和爸爸的同学同时迷路了。在导航和人工的双重误导下,我们一行人上高速、下高速;再上高速、下高速,从滨州到高青,再从高青到滨州,基本是折腾了一个小时后,才在最初下高速的地方见到爸爸的同学。此时,东营的叔叔已经订好了午饭的包间。
一路狂奔。
饭店很像部队的营房,楼不高,规模很大。也许是大厨也等急了。落座不久,凉热菜就办了一桌。
之前,曾有叔叔调侃地告诉我,鲁菜的特点就是,黑乎乎,油乎乎,咸乎乎,黏糊糊。但东营的菜,还真是不是如此。或许是海鲜与河鲜较多的缘故,大厨的手下,多是清蒸和水煮。
很多没有内线的西北游客,一到假期说起海鲜,喜欢直奔日照、青岛、烟台或威海。那里,当然也好。但要说海陆双鲜,还是东营。 秋风起,蟹脚痒。东营不仅有鲜美的梭子蟹,还有丝毫不逊于苏州阳澄湖的大闸蟹。
“形模虽入妇人笑,风味可解壮士颜。”
当我们一家正津津有味地按照从蟹黄到蟹脚的程序,认真完成那个“从前慢”的动作时,东营的叔叔却说:“吃个大概就行了。”这不经意的一句,真是豪极。毕竟,黄河刀鱼、野生鲫鱼、油焖嘎鱼以及河虾、海虾和各类贝壳,都已上桌。而且,不论海鲜还是河鲜,都要在最好的温度里食用,才能鲜美。彼时,慢或从容,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只好舍弃螃蟹那些费时又费力的腿脚之类的边角料了。
美味和温度的关系,很早就被人重视。但温度和饮食速度的关系,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一个日本人从小孩子吸吮母乳特别来劲这一现象出发,研究母乳的温度究竟是多少,研究溫度和饮食速度的关系。他通过控制吸管的粗细,来控制顾客吸食饮料的速度,进而使得顾客吸食他的饮料时,使得饮料的温度就像婴儿吸食母乳时母乳的温度。他成功了。东营的叔叔或许并不知道那个日本人的研究成果,但他“吃个大概就行”的豪言,不是土豪耍阔,而是要我们在最好的时间,享受最好的美味。
沈从文曾经多情地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喜欢“正当最好年龄”这几个字,它强调了时间的意义。在山东,正当最好的年龄的我遇见同学,遇见朋友,遇见美食。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有金圣叹序文一篇说:“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何以言之?用违其时,事易尽也。”这里的“用违其时”,也是在说时间的意义。
遇见是缘,但在最好的时间遇见,才是最好。
东营黄河湿地的美,也不仅仅是美食,还有美色。但我们去的那天,风实在是大。标志性的天鹅以及各种鸟儿,都避风于巢。想象中百川入海、波澜壮阔的景象没有看到,因为天灰蒙蒙的,能见度不过百十米,黄河掩映在一片薄雾之中,我们无法目睹,也无法伴随它走完最后一程,只能暗暗猜测构想着一条线融入一个面的依偎。失望之余忽然看到了站在另一边的爸爸,他正在帮妈妈照相,微蹲着,很投入。我自豪又幸福地看着这个画面,想着马上要蹦跶过去跳进这个其乐融融的视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照完相起身的爸爸,突然闪了一下,几近瘫坐在地上。
我有些发愣,妈妈有些惊慌。
我还有一点难过。
一定是因为风太大了吧,风太大才让他没能站好?如果他还是30年前那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定不会这样。
不过,我没有立即过去,而是等着他拍拍身上的土站好,才蹬蹬地跑过去,那一瞬间我就是想抱着他。他问我:“怎么了?是冷了吗?”我把头埋进他的胸膛点了点,外面的风虽然狂暴酸涩,但我的心在那一刻像黄河汇入渤海一样盛满了幸福。
秋风冷萧瑟,芦荻花纷纷。黄河和渤海在东营不分彼此,我爸爸1985年走进山大;2015年,我也走进山大。同一所大学同样的专业。30年间,一所低调得快让人忘记的大学也让我们这对父女不分彼此。诗人叶匡政的《葡萄藤》中写道:“我三岁的女儿/她喊我哥哥/她喊我姐姐/ 她喊我宝贝/我都答应了/因为我渴望有更多的亲人/傍晚,坐在后院 /我们一起仰起头 /我们一起喊:“爸爸,爸爸……我们喊的是邻居屋檐下 /那片碧绿的葡萄藤 /我们多么欣喜 /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因为我们都喊对了/它是我们共同的父亲。”山东大学,还有大山东承载了我爸爸青春最好的日子,这里有他最直接的冲动、最发狠的狂想,如今,我亦在山东的怀抱里成长,我亦把我最好的日子呈给它。我们都是山东最赤诚的子民,最乖巧的孩子。在东营人司空见惯的景色里,我在爸爸的怀里,我们也都在山东怀里。就像潮水般涌进眼眶,远处是年迈的波浪,近处是年轻的波浪。我对爸爸的爱,爸爸对我的爱,爸爸对山东的爱,我对山东的爱,都这样像黄河汇入渤海一般地有了抵达。
彼此,很近,近到可以促膝。近到我就在你的怀里。秋日的东营,即使所有的鸟儿都藏起自己的欢喜,它还会因为一望无际的芦荻,有着自己草本的芳香和柔软。
“仿佛一株含羞草。有时很爱很爱你,也只是静悄悄卷起了叶子。”当东营卷起叶子时,我在那卷起的叶子里,感受柔软、芳香以及来自爸爸和山东的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