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瑞贞《一锅鸡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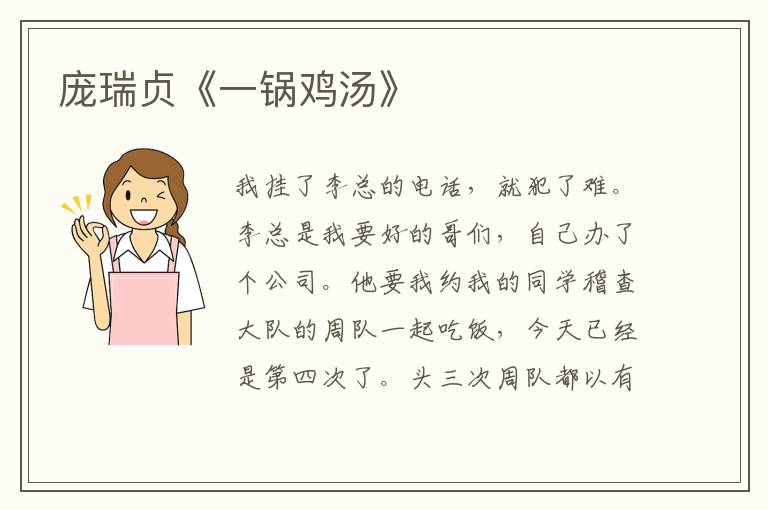
我挂了李总的电话,就犯了难。
李总是我要好的哥们,自己办了个公司。他要我约我的同学稽查大队的周队一起吃饭,今天已经是第四次了。头三次周队都以有暗访小组为由婉拒。
我这同学本来是个爽快的人。只要我出面,随约随到,送物要物,送卡要卡,来者不拒,连句客气话都不说。自从去年,就像变了一个人,让人费解。
记得去年正月里,也是受李总所托,约周队吃饭,他爽快应允。我去接他时,他问安排在什么酒店,我说是香格里拉。他很不高兴,说,怎么安排在那地方,很危险。我说没事,是我请客,老同学一起吃顿饭有什么?他犹豫了一会,还是去了。这顿饭他吃得心事重重的,没有吃完就找借口走了。第二次是五一小长假,他答应得也算痛快,但提出要安排在不起眼的小饭店,吃个土菜就可。过年的时候再约他,他就要求安排在公司的伙房,熬锅猪肉大白菜,使上大豆腐粉条子就很好,不要搞复杂了。
今年从正月一上班就约,直到现在玉兰、紫荆、丁香、紫藤花相继开放,满路滿城的烂漫,也没松口。不管怎么难,李总是几十年的哥们,委托我这么点事,肯定要约,义不容辞。我忐忑不安地拨通了周队的电话,电话铃嘟嘟地响了一段时间,对方终于还是接了,我便立即说:“老同学好,想你了。”
周队说:“有屁快放,我这里还忙着呢!”
我说:“老同学,从穿着棉衣就约你吃饭,到现在已是遍地花开,你打谱什么时候给个面子?”
周队在那边叹了口气,停了一会,说:“明天,明天是周六。你找个看山小屋或者看园小屋,神仙找不到的地方,煮上只鸡,泡个煎饼吃就好。”
获得了他的恩准,我如释重负,赶快说:“就照你说的办,我选好了地方立即告诉你。”
我立马拨通了李总的电话。不用说,李总是高兴无比,说:“地方嘛——要不我马上过去。”
李总的公司离我单位只有一个红绿灯的路程,不一会他就过来了,一腚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上,说:“你老兄觉得到哪里吃好,吃什么合适?我去操办。”
这时我就想到了前几天我表弟的小姨子的公公,论起来我应当叫表叔的赵老头,在我家说的一通话。他是托我给孙子找了个好学校上学,为了感谢我,就把他在山上散养的鸡下的蛋送了一盒过来。赵老头是个幽默健谈的人。他坐在沙发上,从鸡蛋说到了母鸡,从母鸡就说到了公鸡。
他说,他在山上养了十几只母鸡,每年都用自己的母鸡下的蛋孵化几十只小鸡。为了孵化小鸡就养了一只公鸡,这只公鸡一养就是六年,因为它老调戏那群母鸡,我就叫它“老流氓”。“老流氓”一般都是在树上睡觉,而不是在地上。山上的老鹰经常在天上踅摸它,它看到老鹰就躲进草棚。有一回,老鹰嗖地从蓝天上扎下来,就得了手。我想这回“老流氓”算是完了,可是老鹰的爪子竟没抓透“老流氓”的老皮,“老流氓”蹦了一个跳,甩掉老鹰就钻进了酸枣丛里藏了起来,老鹰害怕密密匝匝的酸枣棘子,只好在天上盘旋一会儿,悻悻地飞走了。“老流氓”今年特别地发情,逮着只母鸡就踏到背上办好事,把十多只母鸡的脊背跐蹬得都没了毛。都戏谑秃头的人聪明绝顶,俺家的母鸡就秃背不绝顶。赵老头说到这里哈哈大笑了起来,我也禁不住跟着笑了。
赵老头笑过又气愤地说,你说可恨不?老流氓除了调戏母鸡们,还老爱在母鸡面前逞能。有一次,我正悠闲地看母鸡们在树下刨虫子吃,冷不丁地就感到腿弯被什么东西叮了一下。回头一看,是“老流氓”。它两眼圆瞪,脖子上的毛根根直竖。我一见到它就来了气,顺便给了它一脚,谁知“老流氓”不但不躲闪,还跳起来和我搏斗。这一来我心里又笑了,想想不就是只鸡吗?不值得和它一般见识,就放了它一马。它却更加逞强起来。我小孙子到山上来看我,追着一群毛茸茸的小鸡玩,结果就被“老流氓”从背后一口啄了脖子,生生地叮下了一块皮,流了一脖子血。这“老流氓”不是自己找死吗?坚决不能再留它。可惜今天我没逮住它,要不就连它一起给你送过来了。这家伙六岁多了,肉肯定很香。我说,你好不容易养了这么多年,我怎么好意思吃呢?赵老头说,表侄,你表婶子信佛,不杀生。不犒劳你还犒劳谁?这两天我一定逮住给你送来。
我就对李总把赵老头的话说了一遍。
李总说:“快打电话给你表叔,晚上无论如何逮住这‘老流氓’,它会飞,好色,还有智慧,它的肉要是用木柴大锅煮了,肯定赛过龙肉。至于钱,他要多少,咱给他多少。”
我当即给表叔打了电话,并且自作主张地说给他三百块钱。把老头恣得一个劲地夸我,并说过几天攒了鸡蛋再给我送些来。
李总满心欢喜地说:“太极老兄,真是厉害,再想个合适的地方。”
他们叫我太极,不是说我会打太极,而是因我善于借力打力。我在单位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小科长,但我凭着借力打力,能搞定很多事。也即张三托我找李四办事,我就使出咂奶的劲去办,成了;王五又托我找张三办事,张三感激我给他办了事就尽心地给王五办好。就这样一路混过来,竟成能人了。
我想了想对李总说:“我有个堂弟,在城东搞了个苗圃。现在正好是樱花未谢,海棠花热烈,紫藤花乍开,一园好景。园子里有三间瓦房,干净卫生。瓦房的南边,玉兰树下用大理石板铺了几十个平方米的地面,就在那里露天就餐,野风野味。周队去了肯定屁欢屁欢的。”
李总豁达地说:“真是好主意,就交你办了!”
李总走后,我先打了堂弟的电话,堂弟爽快地说:“我的苗圃就是你的苗圃,里面有韭菜,大葱,冰箱里有些鱼肉,需要什么你尽管用。我在工程上,不能过去陪你。晚上我把钥匙给你,离开时把钥匙放在西屋山头的水桶底下,锁好门就行了。”
我又电话约了几个朋友,都是和周队说得来的,总共八个人。
第二天清晨,我先到老赵表叔家拿了“老流氓”,到集贸市场上找卖鸡的屠杀拾掇干净,然后到了堂弟的苗圃把它大卸八块,放进八印锅,舀水,放料,用木柴煮了起来。
从九点煮到十一点,锅里渐渐飘出诱人的香气,不久就溢满了屋子,飘到了屋外,满以为“老流氓”已经煮烂,可是掀开锅盖,用筷子插了插那块最大的鸡块,却是硬硬地打了个滚。我就又从外边抱来一堆木柴续进锅底。烧了一会儿,再用筷子插,依然是硬。最后干脆把一根碗口粗的木棒填了进去,着了半天,仍然没有煮烂。看看玉兰树下的围桌而坐的朋友们,无奈只好连肉带汤舀到了盆里尴尬地说:“咬不动肉,咱就光喝汤吧!”幸亏预先从附近酒店要了几个炒菜,每人再盛一碗鸡汤,算能凑付过去。这时李总手机响了,他接完电话,端起酒杯说:“刚刚周队来电话,突然接到一个任务,十分紧急,过不来了。他说让我们谅解,改天他请客,给哥们补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说完,一口就喝了半杯,其他人也都跟着喝了一半。这时平日里爱开玩笑的一哥们开了腔,说:“今天是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李哥是不是心情有点不快啊!”
李总强装笑脸说:“这怎么说的!周队不来,我们兄弟的感情一样黏糊。”说完就让大家喝鸡汤。
我看李总心情真的有些不快,就讲了赵表叔跟我讲的这只“老流氓”大公鸡的故事,以活跃气氛。大家却乘着酒兴,张口一个喝碗“老流氓”汤,闭口一句“老流氓”喝碗汤,仿佛在场的都是“老流氓”,唯有缺席的周队干净了。
直喝到走路拐弯,尿尿画圈的地步,方散。我草草地打扫了一下战场,按堂弟的嘱咐把钥匙压在西屋山头的水桶底下,锁了门,坐上李总的车回了家。
第二天我接到了堂弟的一个电话,说:“昨天下午,苗圃的三间小屋起了火,烧得只剩下了一个砖框子。周围的十多棵树也烤死了,直接经济损失约六万元。老婆正在和他吵,寻死觅活地不算完。”我听了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大概”、“或许”、“也可能”地应付到堂弟挂了电话。
第三天,我接到了周队发来的一条短信:幸亏前天我没有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