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丽《槐林深处是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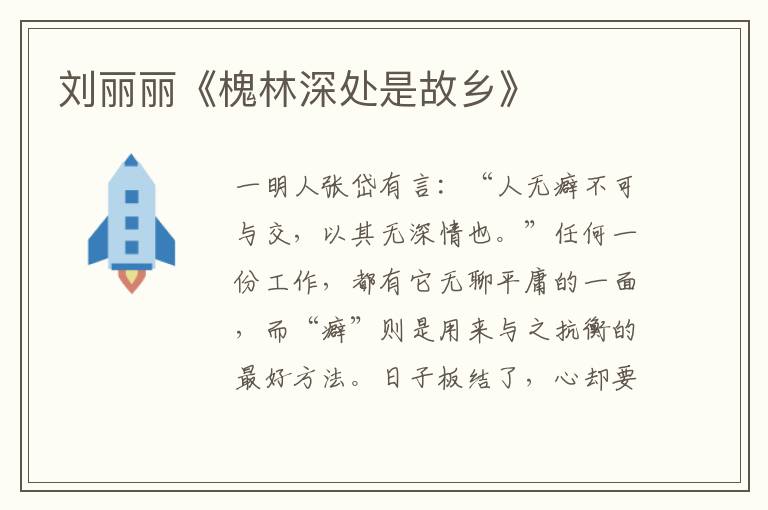
一
明人张岱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任何一份工作,都有它无聊平庸的一面,而“癖”则是用来与之抗衡的最好方法。日子板结了,心却要温润,乡人之“癖”就是种树。田间地头自然不在话下,街头巷尾见缝插针,自家庭院的里里外外更需要好好谋划一番。按照自己的意愿栽下树苗,栽下花花草草,小葱小菜,这些边边角角的“自留地”是他们精彩活着的有力证据。你看见一个男人扛着铁锹走出家门,他不一定去掘地培土,去堵口子,有可能就去自家的树旁边转一圈,修一修疯长的枝杈,揸一揸树身的粗细,顺便把路旁的一摊牛粪埋到树底下。太阳偏西,他把虚土踩实在了,然后再扛着铁锹回来。在他的呵护下,榆柳槐杨都绷着劲儿地往天上蹿,他高兴,表面上他还是那个不动声色的汉子,谁都猜不出他心底的快乐。
树是村庄的另外一张脸。生为阳,死为阴,在风水学上讲究“生”是阳气旺盛的表现。树木植被茂盛的地方,感觉有生机活力,让人很舒心。树长得直溜挺拔,主人的腰杆也硬气。树长得葱茏,这一户人家的日子就显得格外精神。相反,整个村落里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找不出来,嫁闺女找媳妇,这样的村子是坚决不考虑的。连一棵树都长不好的地方,活得有多么憋屈?有树木就有了生机。树上藏着各种各样的鸟儿,从早到晚的鸣叫声让人觉得热闹。树下鸡鸣犬吠,老母鸡咯咯地领着一窝小鸡雏在太阳底下啄食,那些绒团团跟杨花柳絮一样,毛茸茸、圆滚滚的。“门前一棵槐,有财自然来”,新房子盖成,讲究的人家大门前一定要栽棵槐树,逢年过节,还要贴一张“出门见喜”上去,准备迎接生活随时可能赐予的惊喜。院墙外要栽高大的树,它们容易成活,苫荫快,用不了几年就能苫蔽房顶,洒下一地阴凉。柳树,桐树都是首选。当门的位置,栽下一棵苹果树。结不结苹果不要紧,每个春天都能开出一嘟噜一嘟噜粉红的花儿来,推开屋门,一树粉红让人看着火火腾腾,心情舒畅。假如堂屋盖好,剩下的砖头不够砌墙的,就栽一溜树,权当最初的篱笆。合计了一下,男主人栽了几棵洋槐。这树长得快,不挑肥水。果然,几年下来,院子里的梧桐高过了房檐,叶子干净挺括。洋槐和柳树各自成荫,再长长,盖厢房的檩条就有着落了。女主人还在一旁的宅基地上种了几畦青菜,篱笆下栽了几株豆角,场院边上点了几棵南瓜,这样整个夏秋两季的青菜就不愁了。菜畦边上还种了半分地的棉花。每天下地回来,她钻进厨房忙活出一家人的饭食,月亮就升起来了。趁着明快她又钻进棉花趟子里,掐杈子,打花心,捉虫。干这些活都是零打碎敲的工夫,牺牲掉的是她的休息时间。她攒着,省着,把零碎工夫和心思一点点投进去,零存整取,到了冬天,一家人的棉衣和女儿的新被子就有了。日子就这样长长久久地谋划出来。
二
四月的天也攒着,聚着,等候一个孩子的欢呼响起。
米白色的花儿如同宁静的月光,在阳光不曾降临之前酿制一种属于春天的季节病。也许是一种忧郁,也许是一种躁动不安或者茫然失措,存放在叶芽里,存了一个冬天。四月的阳光照到树梢,寄存的情绪终于被催醒,最终发酵成了甘甜,在某个清晨去唤醒孩子的味蕾。在矫健和轻盈还属于童年的时代,乡下的女孩子也能轻易地爬上大树,攀上房顶。我喜欢把头扎在槐叶丛中闻那香气,新鲜的花香浓郁到可以触摸,可以大口大口吃进肚子里。童年的记忆中,我感官印象深刻的,除了稻田的香气就是树木的香气,只要闻到这个味道,就有说不出来的安宁和快乐。洋槐花的花蜜藏在花蕊处,米白色的花朵莹白如玉,“羊脂玉”这个词应该是贴切的,可惜它们没有香气。花蒂泛着黄褐色的槐花是最好吃的,味道超过其他类型的槐花。年纪小一点的,仰头在树下等着。树上的孩子吃个差不多才开始往下扔。母亲也在树下等着,一边提醒着树上的孩子多加小心,不要被洋槐的刺扎到胳膊,一边把地上的花枝收拢,采下花朵放进篮子里。
早餐的香气像洒进厨房的一道光。烙槐花饼是一个技术活,尤其是发面的槐花饼。死面饼虽然出锅快,但是怕对孩子的肠胃不好,母亲被嘴刁的孩子逼成了高手。发酵好的面团略微带一点酸味,母亲把它们揪成一个个面剂子。槐花清洗干净,用篦子沥去了水分,放在盘子里备用,有时是纯粹的槐花,偶尔会磕一个鸡蛋,洒点细盐,搅拌均匀。发面饼擀皮是个技术活。擀厚了,香气出不来;擀薄了,在锅里一翻个,里面的槐花馅就会漏出来。要不薄不厚,刚刚好地包裹住那团花朵。厨房是家里熏得最黑的地方,也是最亮的地方。灶膛里,明亮的火焰舔着锅底,母亲一边往里添柴烧火,一边用铲子小心翻动,翻看饼的成色,不长时间,灶间就弥漫出一股香甜的气息。铲出来的槐花饼放在盖垫上晾着,这一家的三个小馋猫早就迫不及待地一人抢了一個跑出去,母亲的叮嘱声从身后追来:“别烫着,一个个急嘴子!”槐花饼,真好吃啊,又薄又脆,有一股地道的槐花香气、麦香气,暖洋洋地香到心底。
在鲁北平原,整个槐花飘香的季节,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可能都会在餐桌上见到槐花饭、巴拉子、槐花饼,讲究的人家还会敲几头新蒜,蘸了蒜泥吃,胃口格外好。晒干之后的洋槐花可以用来冲泡槐花茶,整个夏季,它们被存放在一个铁皮盒子里,放在大衣橱的顶上。有客人来,先要踩着凳子去够那个橱子顶上的铁皮盒子,“砰”一声,随着盖子打开,一股熟悉的茶香混着槐香的味道扑鼻而来。依照客人的喜好,泡茉莉花茶或是槐花茶。一杯热茶,是贫寒人家待客的基本礼数,有调着花样的好吃的一起分享,也是乡村的诚恳。
三
吃完晚饭,大家习惯拿个马扎坐在院门口歇凉,有蚊虫,所以必须拿把蒲扇扑打着。那时光景说来如同做梦,天上有星星,地下有流水,中间一群与世无争的人,有的坐着,有的拿了一领蒲草席子半躺着。梧桐花谢了,洋槐花谢了,叫油子咯咯咯地拖长声音鸣叫。葫芦开着白色的花,草木的气息润泽着村庄,正是方便讲古说今的时候。乡人说话都喜欢扯着嗓子,不习惯细声细气。生存于天地之间,凭着良心说话,也就没有那些小节的拘束。虽说村里的人家都是小门小户,多少有几个喝过墨水的,有几个跑外“赶脚”的,他们从书本上,从生活中比一般庄稼汉多了见识。当白天的辛劳过去,这一刻说笑打趣逗闷子,连性情严厉的人也松开了眉头,对孩子们的管束也不那么严厉了。
“问我祖先来自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村庄起源的介绍,暗夜的星河在头顶滚滚奔流,生平第一次感觉有神秘的力量在昭示指引,指引着血脉中的某种东西扯向传说中的故乡。槐树,怀念。想象我们的先人一步步远离故土,带着简陋的行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故园,然后风雨漂泊,种子一样在黄河滩上扎下根来。每当到达一个新建村庄,他们都喜欢在最显眼的地方种上一棵槐树,以此表达对移民活动的纪念和对祖先的怀念之情。新槐长成老槐,那一棵棵散布在鲁北大地上的槐树成为他们精神上的皈依和寄托。另外一个说:“咋不是,我去陕西,那边大牌子上印着‘三槐并茂’,有些院子就叫‘槐蔭山房’,那可都是出大官、出大贵人的地方。”这样的一番话落地,引来人们的一些赞叹。这一家的男主人没有说话,他看看自己家门前的槐树,看看身边跑着笑闹的儿女,心里暗暗地打定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是关于未来的,他还没来得及跟妻子商量,但是心里已经开始攒劲头。
树大合围,必出贵人。儿女上了学,每一年的八月十五或者过年,男人必然要把村里学校的老师请到家里来做客,摆一桌丰盛的菜,买上好的酒,恭恭敬敬请先生对自己的儿女严加管教。先生被让到“上席”,有时叫上一两个陪客。男人不善言辞,虽然只上过两年小学,可是不想让儿女短了学问。老师让买课外书,他就骑车到十几里外镇上的代销点去买;学校里要求勤工俭学,他就领着儿女去野外打草,割蒲子,一一教给他们方法。每个早晨女人也早早叫醒睡梦中的孩子,夜里,督促他们写作业,听他们摇头晃脑地背诵课文。傍晚时分,忙完了一天的活儿,搬个凳子坐下来歇歇,在梧桐树荫下,紫色的花朵落下来,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常常催开他们额头的皱纹。过年时一张张簇新的奖状也成为这个贫寒之家最值得骄人的物件。树们一年年长起来,那几年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学生也多,一茬一茬,中专生、大专生、研究生,“和睦村”走出来的学子似乎成了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这一家的女儿也在某一年跳出了农门,成了端上“铁饭碗”的公家人。透明的心底,折射出的第一道光影便是父亲干活的轮廓。多年之后回望父亲平日一锨一镐的耕耘,那份勤勉踏实,依然让她受益终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走出村庄的人回头来看,发觉故乡的人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犟。清一色的牛脾气,凡事爱钻个牛角尖,为了一句话,两个人可能吵架吵到脸红脖子粗,即使亲兄弟,也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而闹到多年不搭腔。那种死不开窍的叫“榆木疙瘩”,那种特别耿硬的叫“槐木橛子”。榆木疙瘩虽然不开窍,可是做家具的时候还能顶用,槐木橛子就不行了,不抓钉子,也难上胶,现在的木匠们都绕着它走。“槐树不上房,苦楝不做床”,这耿硬的橛子除了让人生气外,真还派不上大用场。就说这个“耿”,有啥说啥,心里咋想就咋说,不会拐个弯,不会变通。比如为了不占公家的便宜,打算盘打一夜,也要把一分钱的账目对齐了。为了一分钱的小钱,熬得双眼通红,这是何苦?“硬”就是硬气,敢于得罪人,哪怕是自己的上级,也要争一个理儿。大喇叭里村支书喊过的事情,他觉得不对,就敢跑到村支书家里去辩理,也不怕将来村支书给自己小鞋穿。假如你好意劝劝他,他可能梗着脖子反问:“为着良心说话,怕什么?”
不光耿硬,他们也热情善良,见不得穷人,见不得苦人。尤其是母亲,家里来个讨饭的,常常把新蒸好的馒头给乞丐,自己吃陈干粮。村里谁家有个三灾八难,大家伙一起凑份子,三十块、五十块到几百块不等,渡过眼前的难关再说。一户人家坐落在村庄最东边,再向东没了邻居,油漆路也到了尽头。凡是下田劳作的,临时想起缺东少西的,都喜欢到这家里来借。上学路过的孩子们,下雨之后也常把车子放在这户人家,等散了学,道路干爽了再骑回去。男主人下地回来,把车子推到干爽处,用钩子把瓦圈里的泥巴一点点抠出来,车胎瘪了的给充上气。学生娃们放学回来,喊他一声“大爷”,他就知足了。村庄里最常遇到的是过路的,干渴的讨水喝,迷路的问路。走路累了的,让到槐荫下歇歇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几句。
哪个村的?小董家的。
哦,村里有个董金泉你认识吧?认识,原先当过会计股长,后来下乡修收音机、电视机。
他当会计股长的时候我们一块去天津大港参观过。
嗯,他家里的就是我一个叔伯妹妹。
几句话下来可能就续上了亲戚。这茶水也就递得格外勤了。小善积大德。虽然他们讲不出深刻的大道理,虽然他们说话不太漂亮,但是他们的心肠热,像一棵树一样堂堂正正地活在天地之间。
四
村人爱树。除了爱惜自己千挑万选的树,对那些野生的、雨生的、粪生的苗木,也有一份怜惜。不管是鸟叼来的,兽类肚腑中还没来得及消化的,只要落地生根了,只要不碍事,那就任由它活下去。施肥的时候,多抓一点,浇水的时候,多灌一瓢,有别人吃的,就有它吃的,没娘的孩子得多给一口饭吃,自己心里才过得去。
父亲是个大忙人,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很难见到他的身影,因为他是个党员,生产队里的事情总比家里的事重要。生产队长,虽然是个芝麻大的村官,却也关系到全村150多口人的命脉。春耕、夏锄、秋收、冬藏,还有全村的副业、基本建设,全在他的号令下进行,甚至谁家夫妻吵架、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去做主。难得狂风暴雨让他在家安静地待上一天。风雨交加的时候,我们关好门窗,心神不宁地望着外面恐怖的乌云、暴雨和狂风。他在一边若无其事地干一些家务活,修补房屋、收拾农具、编织苇席。好像没有他不会做的,两只粗糙的大手,却能编织出很细密的苇席,那些苇篾子在他的手里,像一群乖巧的小兽,在他的指令下,乖乖地各就各位。
记得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厨房的塑料纸“砰”的一声响,似乎是什么东西坠落下来。本来就是令人恐惧的风雨之夜,这样怪异的声音更让我们的心都提了起来,汗毛全都炸起,耳朵指向那奇怪的声音。父亲不紧不慢地放下手中的活计走了出去。昏暗的灯光中,父亲那模糊的背影是那样高大,足以挡住一切外来的恐惧。
我们趴在炕上,大气都不敢喘,一种莫名的恐惧夹杂着兴奋燃烧在空气里。似乎是漫长的等待之后,父亲进来了,搓着两只手说,是一只鸟,个头好像不小。炕上一下抬起三颗乌黑的头颅,六只眼睛瞪起来了,父亲继续淡淡地说,野的,抓住了也养不活。明儿天好了,自个就会飞走。炕上的头陆续低下去。
父亲若无其事的神态,让我们都安静下来。父亲睡了,我们却一直惦记着那只大鸟,竖着耳朵在风声雨声中分辨大鸟的异响。
第二天早晨,我们打开厨房门,柴火堆上留下了几根羽毛,那只鸟已无踪迹。我轻轻地拾起其中的一根,仔细看这支羽毛,想象那只鸟的样子。这是一根半尺多长的羽毛,弧形的羽干很硬实,根部毛茸茸的,前端结结实实,应该是一只巨大而勇猛的鹰隼,它好像是在风雨的淫威下尋找一个避难的场所,是父亲容留了它,又在清晨打开大门,放大鸟一条生路。也许是对父亲的善举的回赠,大鸟留下了羽毛,我和哥哥各自收藏一支。
有时,也有陌生的路人被风雨逼进我家,父亲像照顾兄弟一样照顾他们。记得有一个避雨的人带着一股寒意被让进屋里,落魄的样子,让我想起那只闯进我家避难的大鸟。父亲让他擦干头发上的雨水,换上干爽的衣服,两个人就在堂屋的方桌两端坐下,天南海北地拉话,一根接一根地卷着旱烟,喷云吐雾地抽着。偶尔有椅子的咯吱声和咕咚咕咚喝水的声音。我很想听听两个陌生的男人之间会说些什么。我打起精神,侧着耳朵,好像张开一个大布口袋一样等着他们的消息。可是零星的词语无法串成完整的意思。他们压低了嗓音,生怕被人听了,很像电影里的地下党接头。
早晨,我们起来时那人已经走了。没有像大鸟那样留下羽毛,只是满地烟蒂,好像是整夜未眠。鸟巢一样的故乡白天放飞多少只鸟儿,夜晚就能收容多少秘密,游子村人,跋涉千里,天涯赶尽的时候,这里是可以息心的庇护所。
五
身姿矫健的童年属于风筝,属于乔木,属于云朵,从天上降落到人间的过程中,童年一天天远去。直到身边的孩子喊“妈妈”,才把我从怅惘中拉回到现实。多少年过去,窗外除了风霜,仅剩下挂在枯枝上那只一瘦再瘦的风筝。村庄被岁月压弯了腰,坏消息大多通过一根电话线传来,亲人入院,老人去世,琐碎纠葛引发纠纷,一双双泪眼等待你去安慰。在一次次狼狈的往返中,草木凋零,亲人的骨骼还给泥土,眼睛还给天空。后来人不识,那颤巍巍走到墙根下晒太阳的人,那个吃罢了晚饭就呆坐如同石头的人,那个歪在躺椅中连一句话都不能完整表达的人,当年走出村庄时,两只大脚板也是踢踏有声,跺一跺脚,街口都会发颤。他曾经牛一般地拉车,铁塔一般的身子拉着一群儿女,掌舵掌得稳稳当当,不让一点风雪打到儿女的身上。
灼灼的花开了一春又一春。故乡的面貌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电话线里陆续传来一些令人愉快的消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养老金啦,土地流转不用下地就能领钱啦,村前村后搞环卫一体化变得干净啦……这些消息让我的心里温暖着,敞亮着。电话线那头的人,骨头继续变硬,但他说只要身子还能感觉到疼痛,就是证明自己还活着。活着多好,可以吹到春风,淋到春雨,可以让儿孙推着去看那一亩一亩的槐林。当年,这个老党员工作战斗过的地方,而今被改造成了一片湿地。当年的泄洪渠的轮廓还在,它像一条长龙横贯东西。在河流的两岸,万亩香花槐齐齐整整地开了,一朵朵,一穗穗,香甜的槐花挂满枝头,那花朵灿烂如同云锦,连绵起来形成一条花朵的长廊。当地人扶老携幼,外地人慕名而来,走进这一幅生机盎然的画轴里。在花香中漫步,阳光照进心底,他想起那一年唱着进行曲去上学。那一年,坐着马车带着铁锨和镐头去整修京津区域的另外一条河流,劳动的号子比枪声还响,响彻云霄。此刻,他的骨头比北风还硬,头颅比槐花还白。
从村庄走出去的儿女进了城,有的去了更远的地方,有的偶尔回来看看,有的就永远扎根在异乡。只是每个梧桐花开的日子,他们会怀念父亲,每个洋槐花飘香的日子,他们会怀念母亲。每一个深夜难眠的日子,他们会怀念那个被槐林拥抱的小小的村庄,想起那些不太会说漂亮话但心肠温暖的村人。他们也会怀念那些陪伴他们长大的树。槐林深处,隐藏着他们童年的惆怅,掩埋着那些闪烁着晶莹光泽的小小的疼痛和秘密。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听见娘站在胡同口拉长了调子呼喊她的乳名。声音真切,如在耳畔。她赶紧答应着跑回来,父亲也从家里走出来了,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俩人都笑了。她也跟着笑,忽然就醒了,感觉脸上凉凉的,一擦,全是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