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北《借君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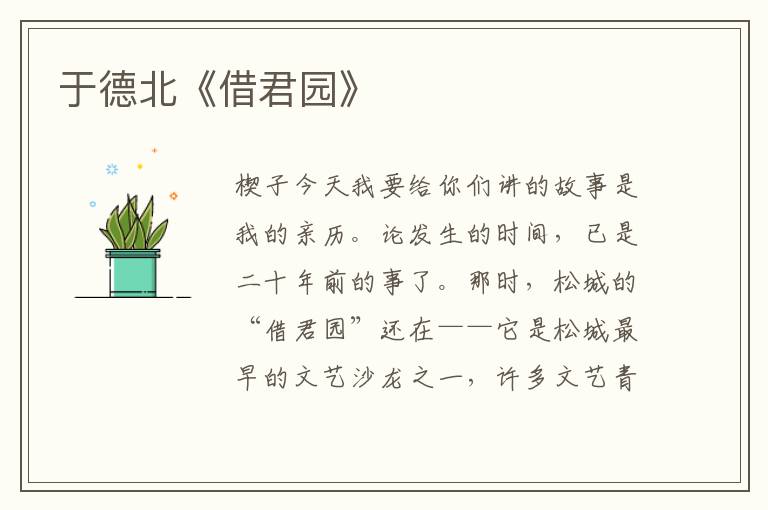
楔子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我的亲历。论发生的时间,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松城的“借君园”还在——它是松城最早的文艺沙龙之一,许多文艺青年聚集在这里,畅谈理想与未来。那天晚上,来了三个画画的人,二男一女,一男一女是师大美术系的毕业生,恋人;另一男是艺术学院的在读生。他们三个是朋友,也是“借君园”的常客,经常在这里混吃混喝,因为来往于“借君园”的各色人等中不乏工薪阶层中的高薪者,他们会把一些好的吃食带到这里,以供大家享用。
早在一个多月前,这三个人就在“借君园”里酒后打赌,他们要在学校暑假期间各自封闭创作一幅油画,画作完成之后,按约定时间回到我这里,每个人讲述一个与创作有关的故事——也是该作品的背景资料,最后,由我评定,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有谁在未来的日子最有可能成为一流的艺术大师。
需要说明一点,因为“借君园”本是我的居所,所以,我被强制为借君园主。
现在,这三个人践诺来了。
梦
(师大的男生讲了第一个故事)
我认识一个朋友,长期在野外工作。他是学植物的,喜欢写散文,写出的散文清新自然,有山谷里小溪的气息。我是这样来形容他的文字,不知道别人是否同意。他是一个喜欢行走的人,更喜欢独处,很少和别人说话。我们交往密切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也喜欢植物,一直想写一本“东北野生可食植物的药用价值”的书,所以,一旦他从长白山回来,我就会住在他那里,向他请教相关的问题,而他的思绪一接觸到植物,话语便滔滔不绝,像堰塞湖突然决口一般;还有一个原因,我帮他整理那些在野外宿营时写下的零散文字,准备为他出一本类似于《大自然的日历》的书。书里边是有许多插图的,他委托我来画。
工作之余,我们各自躺在椅子上,一边吸烟,一边说一些闲话——所谓闲话,既和植物无关,也和散文无关,完全是家庭主妇般的穿云入地,海阔天空。
似乎没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却也很生动。
他说他的梦——开始便语出惊人。
他说:“梦做久了,变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非常真实。”
“从何说起?”我问。
“心里这样感觉,总是不好受。”
“梦的内容?我是说……”
“过日子。”他打断我的话。
第一次梦见那个女人是在野外,他一个人躺在睡袋里,天上尽是星星,身边是微小的露珠。他仰望星空,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不知不觉就和一个女人相处在一起。那个女人个子不高,很白,脸上有一个淡淡的痦子。她的眼睛很空洞,也可以说很清纯。梳了两条短短的辫子。那女人吸烟,说话的时候,口气里有些许香烟的味道。她笑着和他说话,那意思是叫他快点吃饭。他觉得这个女人眼熟,很像自己的初中同学,又很像自己单位里的旧同事,仔细去分辨,又不完全是,于是心里很急,又不便问,急来急去,醒了。
醒了之后很感伤,再去看天空,依然是闪闪烁烁的星星。
那个女人在梦里笑着说:“你呀!”
无比娇羞。
他想,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为什么还像少女一样羞怯呢?
她穿着朴素,很符合他心里对女性的标准。
第二次梦是从野外回来,距上一次梦月余,他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他放下背包,就开始整理植物标本,厚厚的一沓,分门别类放好,做好标签,就倦意袭来,非睡不可。于是,衣服也没脱,倒在沙发上就睡,一直到深夜。
也是梦见她,背对着他坐着。
他一惊,又一喜,心里想:莫非是她?
那女人回过头来,笑着说:“是我。”
样子还是那么娇羞。
她走过来,坐在他的身边,他尴尬地往里边靠靠,不想她竟也向里挤了一挤。
她看着他,慢慢地脸红起来,突然,她俯下身,在他的脸上一吻,嘴唇温热,十分柔软。他已经四十岁了,从来没有和女人亲近过。被这女人一吻,不觉起了反应,急忙坐起身,逃到厕所里。
大量地冲水,借以掩饰内心的恐慌。
冲水声音巨大,把他吵醒了。
又一次醒了,比上一次更感伤。
自那以后,她就经常到他的梦里来,像过日子一样。据梦中的暗示,他们已经是夫妻,他一直很有负担地充当着一个丈夫的角色。她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可是他永远也记不住。有时,半恹半醒间,反复叨念,提醒自己要把那两个字记牢,但是,丝毫作用不起,等他醒了,名字依然如同窗口的风一样,稍不留神,就吹走了。
又一次,他对她说:“告诉我你的名字。”
她只笑不回答。
他内心酸楚,竟落下泪来。
她急忙来哄他,拥他在自己的怀里,说了自己的名字,还劝慰他不要着急。可是,宿命一般,她一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就把名字忘了。
“有过那种事吗?在梦里?”我很好奇,问他。
他吸了一口烟,说:“有吧,但总也做不成。”
“为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又一次,是在出租车上,他们两个人都喝了酒,他除去她的衣服,她也配合地除去他的衣服,两个人就要有夫妻之实了,不料,那驾车的司机突然回过头来。他受了惊吓,理智也重新回到体内。那司机不是人,而是一株他寻找多年的稀有植物,他放开她,伸手去抓,那植物瞬间消失了。
这样的梦缠绕了他五年之久。
这期间,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一律不看,有一次,竟脱口对人家说:“我已经结婚了。”
把对方吓了一大跳!
曾有一段时间没有梦到她,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正焦急万分的时候,她却无声无息地来了。来了,是为了和他道别,说了许多希望他珍惜自己,要照顾好自己的话,他听了半天,听明白了,她得了重病,要死了,不能再给他当妻子了。他不等她把话说完,已经泪如雨下。他想起那个有星星的夜晚,想起她的吻,想起出租车,想起他们在一起的可堪记忆的每一个细节,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
哭醒了,天也亮了。不由分说,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火葬场门口,望见一行行送葬队伍,不知道哪一行属于自己,细想想,哪一行也和自己无关,内心升起巨大的委屈。他下了车,一个人坐在路边,内心越来越压抑,终于放声嚎哭,惹得那些送葬的人都停住了脚步。
……
“后来呢?”我问。
他吸了一口烟,说:“哪有后来呀。”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
我侧头去望,他的脸上分明又流过一行泪水。
又一次,是在出租车上,他们两个人都喝了酒,他除去她的衣服,她也配合地除去他的衣服,两个人就要有夫妻之实了,不料,那驾车的司机突然回过头来。他受了惊吓,理智也重新回到体内。那司机不是人,而是一株他寻找多年的稀有植物,他放开她,伸手去抓,那植物瞬间消失了。
师大男生画的就是这个场景。
似水年华
(师大女生讲了第二个故事)
可以确认,这是一个夏天。
老砖堆砌起来的墙壁依然固执地坚守传统布局的屋宇,但房檐上的青草正茂密地展示着新生命的灿烂与美丽。由宽宽的门洞望进去,深深的巷子里,生活一成不变地演绎着普通生命的最朴素的日子,如果静耳细听,你可以尽收婴儿强有力的啼哭和垂死老人的可怜的无奈的同时也是释然的呻吟般的叹息。
画面静止的一刻出现了五个半女人。
地点是松城的三道街。
那时,我十岁。
先說那半个女人,她之所以是半个,有两个原因:一是她还不满十四岁,严格意义上还是未成年少女;二是我静止这幅画面的时候,她只有半个身子在我的记忆里。
这个懒散的下午,老师刚刚家访,因为这个女孩和同年级的另一个男孩躲在学校后边的小树林里说话,老师将其定义为:早恋。她的父亲出差了,而她刚刚从纺织厂下岗的母亲除了哭泣别无他法,只能任凭这个女孩负气离家,直至夜里九点才回来。据她自己说,她一直在伊通河幽僻的堤坝上坐着,据她自己说:“伊通河的落日十分美丽。”
画面中的第一个女人是一个区的妇联干部,爱人是报社记者。她爱人喝多了酒,在外面找了一个三陪小姐,结果染上了淋病。他按电线杆子上的野广告去找野医生,打三百元一针的“一针灵”,连打三针均无效果,不得已,在午休的时候向妇联干部坦白。妇联干部没有过多地询问他的病情,而是突然感到自己阴部瘙痒,急忙赶往医院,希望正规医生可以消除她的疑心。
第二个女人是建筑设计师,乳房极大,却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或许也应该称之为生理疾病。她性冷淡,一过性生活就紧张,疼得浑身是汗。刚结婚的时候,由于责任与义务,勉强应付丈夫,到后来干脆分床而居,一对夫妻像小旅店里不期而遇的房客,自己拥有自己一片独立的天地。邻居都说,这样的女人多半婚前被人强奸过,因为走不出那片阴影,所以导致心理锁闭。但建筑师矢口否认,并拿出新婚之夜的手帕为证,弄得丈夫十分尴尬。此时,她去婆婆家,丈夫已经等在那里了,当然还有他们领养的那个孩子。今天是婆婆的生日。
第三个女人是高中毕业生,刚刚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的背影很纤细,但脚步却很坚实。她和建筑师擦肩而过,破例问了一声:“阿姨你好!”她们以前是不说话的,因为建筑师的丈夫以补课为名,对她进行过性骚扰。
第四个女人距离我的记忆太远了,画面中她的面孔一片模糊,像清晨难以复述的梦。
第五个女人了。
她赤裸着上身,半倚在邻街的窗边,口出狂言秽语。她是一个疯子,三年前在火车站把孩子弄丢了。寻找孩子的大半年时间里,她思维敏捷,行动干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绝望使她彻底崩溃。她骂街。在她的眼里,街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偷孩子的坏蛋,所以她对他们一律怀有刻骨仇恨。开始的时候,她骂人如莺歌燕语,三年一过,她的声带已严重破坏,说话的声音堪比老式蒸汽机。
……
风吹来,檐草低飞。
那苦涩的清香犹在身侧!
我今年二十二岁了,十二年的时间如何能让记忆风干!
她赤裸着上身,半倚在邻街的窗边,口出狂言秽语。
师大女生画的是这个场景。
偶尔静止的旅行
(艺术学院的男生讲了第三个故事)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衣衫!
甬道一直延伸到水的那一边。水上有鸟,低低地叫着,好像在寻找葱郁的芦苇。这个地方是一定有苇子的,因为那种叫红蓼的草已经矮矮地生长起来。早晨,太阳还在山的那头,阳光却转了弯子似的,冲过高高的山顶的树梢,普照下来,把前前后后的景物都照亮了。
四周无人。
只她一个。
她穿了一件白色衣衫,在甬道上慢慢地走着。她好像突然进入这甬道,不知道来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去路在什么地方。这是一座人为的迷宫,如果你想走失,想必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女贞墙上的爬山虎绿了,微风一吹,有股涩涩的味道。爬山虎的叶子一片连着一片,每一片都想露出稚嫩的面孔,以便把自己的新绿寄托在那些有意流连在它们身畔的观赏者的心底。
一只小小的虫子在叶子上爬。
虫子的颜色是赤红的,很小,很灵活。它从一片叶子跳跃到另一片叶子上,一刻也不肯停息地追逐那斑斑点点的光。
她停下脚步,目光被赤红的虫子所吸引。她发现,虫子的背上有细细的花纹,是百合的图案,纹路细密,充满生命的神秘。纹路是淡淡的天蓝,不仔细观察不易发现,但那天蓝是美丽的,泛着金属一样的光泽,像火焰被静止在那里。她看见了虫子的脸,安详、幸福、充满希望,同时也掩藏不住对未知命运的坚忍。虫子停下自己的跳跃,昂起头,静静地注视她,细小的触须随风抖动,让她感觉到交谈的欲望。她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要把赤红的有着金属般光泽纹路的虫子捧在手中。她的手是惨白的,干爽,沁凉。可是,在一瞬间,小小的虫子在她的眼睛里无限地放大开来,她看到虫子温和地摇头,目光中有一丝让人难以拒绝的又无法认知的痛楚。
她的手停在那里,像风中的一缕干枝。
啾……
耳边传来一声鸟鸣,只能听见声音,却不见踪影,甚至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移动。头上是天,现在已经完全鲜亮起来,像给涂了油彩一样。鸟呜就在耳边,清晰得无与伦比,鸟鸣所带起的常人绝对无法捕捉的空气的摩擦还在她的耳郭。
可是,没有踪迹。没有。她想,是早先见过的、水上的那一只吗?她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经一掠而去,隐没到水的那一边的幽寂中去了。
她下意识地把手拿回来,放在自己的身后。
紧接着,她看到了槐花,洁白、奶黄,透着一串一串的馨香。这里的槐树高大,傍山而生,身子却深深地探入水面。槐花的影子映在水上,惹得痴心的鱼儿半张嘴巴,死死地守在那里,对周边的一切绝不理会。槐花,一串,落了。水面荡起大大的涟漪。可是,那痴心的鱼,一动不动,如同雕塑一般。她站在原地,如同雕塑一般。半个身子都冷了。槐花,又一串,落了。那鱼激灵一下,不等槐花落定,身子已经悬了起来,在半空处衔住槐花,尾巴一摆,浸入水底不见了。原来,它等的是这一串!
她感觉自己透明起来。
自己!
透明起来!
突然,女贞墙上传来说话的声音——
……
一片白色的云朵从她的头顶飘落下来,直直地飘到她身侧的堤坝下边。落地。翻滚,再翻滚,最后停止在水边。水,远远地看,都是碧绿碧绿的,可是,近岸的地方,都是各种各样的垃圾。四周变得吵嚷起来了,天地间一下子多了许多人,一个小男孩用尖厉的声音叫喊——看哪,水边有一个人!
她穿了件白色衣衫。
她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要把赤红的有着金属般光泽纹路的虫子捧在手中。她的手是惨白的,干爽,沁凉。可是,在一瞬间,小小的虫子在她的眼睛里无限地放大开来,她看到虫子温和地摇头,目光中有一丝让人难以拒绝的又无法认知的痛楚。
艺术学院的男生画的是这个场景。
他们的故事讲完了,三幅油画也竖在了我的面前。说实话,我是一个色盲,对绘画一窍不通,让我一句话来评定他们的未来,那无异于是指鹿为马,盲人摸象。万般无奈之下,我沉吟了半天,说了一段模棱两可又两全其美的风马牛不相及的“评语”。
我说:“我也讲个故事吧。也许,我的答案就在这个故事里吧。”
大幻觉
(我讲的故事)
这一切都是幻觉。
到西安的那天晚上,我醉了。在车站,因为买票认识了一位东北大哥,两人一见如故,就找了一家店,吃羊肉,喝白酒,直到半夜。
在那灯红酒绿的地方, 我为自己的生理寻找飞翔的理由。
那是一个女孩,言语大方,皮肤白皙,才开始接触,就让你心动。我醉酒了,就对她胡言乱语了一番,那些话一定粗俗不堪,而且直入主题,但女孩始终如一,用最平静的微笑面对我。温柔、温暖、温和,让你不自觉地感动。
我们去了她的住处,一个狭小的空间,但绝对是疲倦的旅人的天堂。
我干了什么,我不知道,在余下的黑夜里。
我只记得,她对我说:“我带你去‘楼观台’,我带你去‘楼观台’。”
楼观台位于终南山麓,是道教圣地,相传为老子当年讲经的地方。
雨后,楼观台周围的山竹青翠欲滴。她对我说,看楼观台首先要看竹子,竹子是那里的特色,也是那里的风格。那些竹子看似纤弱、平常,可看了之后,会让你终生难忘。
“这也许就是平凡的美丽,也是平凡的魅力。”
她这样说。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正在去楼观台的路上,在一个叫大王庄的地方吃早点。长长的席篷,简陋的桌椅,简单的饭菜。她往我的碗里盛一点豆腐脑儿,又把卤汁儿浇在上边。
她说:“竹子从来不让自己与老子有关。”
我突然感觉到异样,心灵瞬间澄净。我原来极为崇尚苏东坡的一句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现在,我觉得这句话和刚才她所讲的那些话相比,如同兰草与垃圾一样。
接下来是在“上善池”。
我已经完全沉浸在女孩如水的讲述中。
道观前是一眼龟池,称“上善池”。取“上善若水”之意。相传陕西周至地方曾闹瘟疫,数月之内,民死过半。当时“楼观台”的道长夜得一梦,梦见观前有青石一块,石下有泉,泉水可祛百病。于是,命人开启,果有涓涓溪流。又命观中道士先饮其水,二三时辰之内,体复康健。道长大喜过望,传告四乡,一时相携争饮。数日之内,瘟疫盡除。
女孩说:“善有多种。”
一生坎坷可称之为善;心系一处可称之为善;温柔可人可称之为善;美誉他人可称之为善;心性若水可称之为善;宁静致远可称之为善。大善若水,无色无味。
我感到自己在分裂,一半向上,一半向下。
状如挣扎。
游遍“楼观台”,我们准备回程。
就在女孩拾级而上的时候,她的衣衫被风一一拂去。她变得赤裸,变得透明。穿过她的身体,我可以看见她的笑脸,那么安详,那么平静,那么美丽。
从始至终,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后记
这是一段陈年旧事,如果不是整理书房,并在发潮的日记本上无意间看到这些记录,我的记忆早就已经把它们消除了。可是,时隔二十年后,它们又重见了天日,并以自身的发酵,酝酿出一些无法言说的独特气息。回想起来,“借君园”原本是有一些艺术藏品的——大画家孙文铎、袁武、朱辰的画,大书法家周昔非、景喜猷、刘彦湖的字,包括以上三位的在内绘制的一些油画,可惜一场暴雨冲坏了“借君园”正在做防水的屋顶,我恰巧出门在外,拙荆又仓皇出逃,这些藏品无一幸免,全都被浸泡污染,无法修复。师大一男一女和艺术学院一男的作品作为实物彻底消失了,可是那三幅画的画面我尚能回忆起来,就算是背景模糊了,有一点是不会忘记,那就是,他们画面上的女人都长着同一副面孔,五官是那么清晰。我当时问过他们,画画期间见面或者通话没有,他们尽数摇头,并发誓起怨,创作的当口绝对没有沟通过任何信息。这就让我不能不产生疑惑,却又找不到丝毫可以让自己释然的解脱。他们也深为惊诧,面面相觑,无法找出一个合理的可以应对我的理由。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二十年,我大概有十几年的生活十分萧索,羞于和外界联系;待稍有好转,陆续又恢复了一些“借君园”旧友,关于彼时的那三位青年画家,我又获得了一些消息——师大的一男一女结为了夫妻,可惜那一男四十岁便得肝癌去世了,死前也早就不从事绘画这一行当了;一女呢,丈夫死后自己开了一个画班,辅导考前的中学生素描及色彩构成。艺术学院的一男先搞装修,后开酒店,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整个人比原来大了三圈。据说他在师大一女寡居之后追求过她,但是一女早对婚姻生活失去了兴趣。
我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借君园”,也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那三幅画和那三个故事,不,加上我讲的,应该是四个故事。我不是宿命论者,不相信天堂与地狱以及因果报应,但是,那些曾经留在时间深处的箴言似的叙述,是不是我们命运中的一个节点呢?但愿是,也但愿不是!
“借君园”解散之后,我一直尝试着写小说,写了这么多年都不咸不淡的。应该说,“借君园”是有故事的,现在,我尝试着写一则,希望读者能够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