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举芳《花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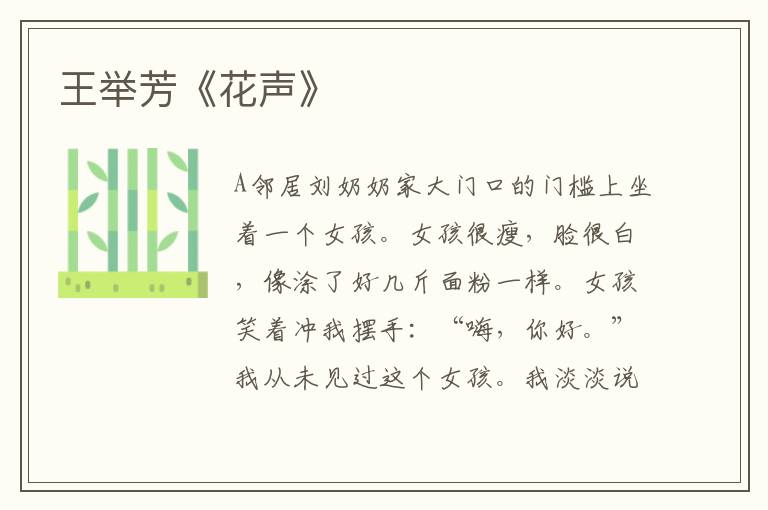
A
邻居刘奶奶家大门口的门槛上坐着一个女孩。女孩很瘦,脸很白,像涂了好几斤面粉一样。女孩笑着冲我摆手:“嗨,你好。”我从未见过这个女孩。我淡淡说了声“你好”,快走几步,进了家门。
我蹲在奶奶身边问:“刘奶奶家大门口坐着一个女孩,脸可白了,你知道她是谁吗?”奶奶往火炉里续了一把柴,扭过来脸看着我说:“跟你一样,一个苦命的孩子。”奶奶的叹气声很轻很轻,但我还是听到了。奶奶用粗糙的手摸摸我的脸,继续烧火做饭。我起身去屋里写作业。
作业写得有些恍惚。恍惚中我看见爸妈在朝我招手。我快速向他们奔去,我就要抓住他们的手了,他们突然奔跑起来,他们跑得那样快,一下子把我甩下好远,眼看就要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我急得大哭起来。
“小楠,小楠,快醒醒……”奶奶边叫我边给我擦泪。我的泪水淌进奶奶皴裂的手纹里,在那些龇牙咧嘴的伤口上撒下不着痕迹的盐。
奶奶把我搂在怀里说:“又梦到你爸妈了吧?那俩没良心的,咱不想他们。他们太狠心了,出去打工一年到头也不回来。那天是我生日,他们说好一定一起回来吃饭,我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没想到等到天黑,等来的是他们双双没命的消息。那个该死的司机,他为啥要喝酒呢?喝酒就喝酒吧,咋还非要开车,他喝了酒在路上开车没个准儿,可就要了我儿子儿媳的命啊……”奶奶的泪无声地落在我的脸上,奶奶赶紧抬手给我擦去,又抬手擦擦自己眼里的泪,说:“小楠,快去洗脸,你爷爷快回来了,准备吃饭。”
乡村的夜静得很快,才晚上十点,村庄便已进入了安睡的状态。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歌声,从未听过的歌声。那歌声丝丝缕缕钻入我的耳朵,纤细、高亢、清亮。
“奶奶,你听,有人在唱歌。”
“哪有人唱歌,快睡吧。”奶奶给我掖掖被子。我闭上眼,依旧睡不着,那歌声像一只小虫在我耳朵里爬来爬去。我晃晃眯着眼睛佯睡的奶奶,说:“奶奶你听你听,真的有人在唱歌呢。”奶奶睁开眼睛翘起半个身子侧耳倾听,一会儿她重新躺好说:“嗯,是真的,是有人在唱歌,好像是小雅在唱歌。”我问奶奶小雅是谁。奶奶说小雅就是你放学回来看见的那个女孩,是你刘奶奶的外孙女。
“小雅她也没有爸爸妈妈吗?”
“有。”
“那您咋说她和我一样?”
“她爸妈都活着,但谁都不要她,就把她送到你刘奶奶这儿了。没见过这么狠心的父母哩,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要了。”奶奶又给我掖掖被子,说:“睡吧,不说这些闹心的事儿了。”奶奶翻身睡去。
我屏息静听,终于听清了一句,唱的是“我想要怒放的生命……”这歌声单曲回放般在我的耳朵里绵延着,绵延着,这歌声像村前那条溪流,流淌着,流淌着,想要奔向外面的大河里去。
B
“小楠。”女孩轻声叫我。那天我放学回来,女孩又坐在刘奶奶家大门口的门槛上。我冲她笑笑。女孩说:“我叫小雅。”我说我知道。小雅说:“来,陪我坐一会儿。”
我和小雅肩并肩坐着,谁也不说话。好一会儿,小雅说:“小楠,明天周末,你能陪我去村后的田里转转吗?外婆不让我一个人出门。”
我说好。小雅伸手牵住了我的手。小雅说:“小楠,咱们做好朋友好不好?”我点点头。小雅很开心,把另一只手也放在我的手上。一股莫名的亲近与温暖在我心底升腾。
春日融融,草长莺飞。我和小雅走向田野。河边垂柳曼舞水袖,似柔情妩媚的仙子般,眸子里温情流泻。乡间的小路两边是绿草红花织成的五彩地毯,无名的野花娇小的容颜绽放出自己的美丽,在这春风里沉醉……
小雅兴奋起来,松开我的手向五彩地毯跑去。突然,小雅倒在了地上。我快跑过去扶起她。我说:“小雅你没事儿吧。”小雅拍拍衣服上的土说:“没事儿没事儿,外婆老不让我动,我的腿都有些软了。”我和小雅躺在暖融融的花地毯上。小雅说:“小楠,将来我死了,我想让外婆把我埋在这田野里,埋在这里不會觉得害怕,你看,好多花草陪着我。”我说:“小雅你咋说这样的话儿,我们还是孩子呢。”小雅说:“我只是说说。”我看见有泪在小雅的眼里闪烁。
“小雅,你怎么了?”
“小楠,你知道吗?我生病了,很重很重的病,花多少钱都治不好的病。算了,不说这个了。小楠,你今年多大了?”
“十三,你呢?”
“我十五了。要是我不生病,再过几个月就要中考了。小楠你知道吗?我特别想上市里的重点中学。可是我没有机会了。”小雅的眼泪静静地从眼角流出来,顺着耳朵滑向脖子。
“小雅,我相信你的病会好起来的。”除了这句,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小雅。我突然也很想哭。我的眼泪无声地流出眼角,顺着耳朵滑向脖子。
“小楠,对不起,我不该对你说这些,惹你伤心了。”小雅起身坐起来,我也起身坐起来。春天的风用温暖的手擦干我们脸上的泪水。
“小楠,你喜欢唱歌吗?”
“我五音不全,唱不好。我喜欢听。”
“我想妈妈的时候就唱歌,妈妈喜欢唱歌,我没生病的时候,妈妈经常教我唱歌,有时候我唱歌妈妈为我打拍子,有时候妈妈和我一起唱。”
“那你妈妈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去年我经常感觉头晕乏力,开始以为是就要中考了学习压力大,爸爸妈妈对我说别那么努力学了,考上重点高中固然是好,但身体更重要,要是落下病,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请假在家休养了一段,还是头晕乏力,爸爸妈妈带我去医院做了检查,查出我得了白血病。看到诊断证明的那一刻,我们全都傻眼了。医生说现在白血病也不是那么可怕了,只要进行骨髓移植便能活命。爸爸妈妈都做了配型,妈妈的骨髓和我匹配。可移植的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妈妈没有出现,从此妈妈再也没有出现,至今杳无音信。爸爸为了给我治病,卖掉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最后连房子也卖了。现在卖房子的钱花也完了,爸爸说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他说他得去打工维持生活,就把我送到了外婆这里。我感觉爸爸也放弃我、不要我了。”
“小雅,你比我好,你的爸爸妈妈虽然不在你身边,但至少他们还活着。而我的爸爸妈媽,永远也回不来了。”我的眼泪又跑了出来。
“可是我活不了多久了。”
“小雅,我也去医院给你配型。”
“谢谢你,小楠。不用了,医生说我已过了最佳移植期。”小雅仰起头望着天空。刚刚还晴好的天气,此时阴云集聚,有些沉郁。
“小楠。”安若在我身边坐下来。安若是我同班同学,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安若,咱们该回家了。”安若妈妈走过来看着我和小雅,对安若说:“安若,以后不要和她俩在一起,她俩都是不祥的孩子。小楠,你不要再去我们家找安若了哈。”说着拉起安若走了。
我忽然觉得心脏疼痛异常且憋闷无比,像被一块巨石无情碾压。
小雅握住我的手说:“小楠,我们不哭。小楠,我给你唱首歌吧,唱我小时候,妈妈最喜欢给我唱的歌:‘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睡落床/明朝阿爸要扑鱼虾啰/阿妈织网要织到天光……’”
C
小雅站在胡同口,看到我说:“小楠你咋才回来?我等你半天了,看,这花好看吧?送给你。今天我求外婆让我一个人去花地毯那儿了。”小雅把一捧野花举到我面前。
“谢谢你,小雅,这花你拿回去养在玻璃瓶里放在桌子上,可好看。”
“小楠,这捧是送给你的,我采了两捧,另一捧我已养在瓶子里了。”小雅把花递到我手里。走到刘奶奶家的大门口,小雅对我摆摆手说:“小楠,你快回家写作业吧。”转身迈过门槛,又折回来对我说:“对了,小楠,这些花枯萎了,不要把它们扔掉,一定记得哦。”
“花枯萎了还留着做什么?”
“我有用。小楠你一定不要扔掉哦。”我点点头。小雅开心地进了家门。
小雅开始经常去田野里采花,每次都是两捧,留给我一捧。小雅把那些枯萎的花集中放在一个塑料袋里,眼看着塑料袋就要装满了。
“小楠,你能陪我出去一下吗?”小雅提着满满一袋子枯萎的花,手里还拿着一把小铁锨。
“小雅,你是不是像林黛玉一样,要去葬花?”
“小楠,你咋这么聪明呢,你自动升级了,不只是我的朋友,现在成了我的知音。古人说:此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太幸福了!”小雅连声呼喊着:“我太幸福了!我太幸福了!”
小雅在山脚下一块向阳的坡地边停下来,说就是这里,外公带我来看过的。碎石横生的坡地荒草丛生。我和小雅拔除杂草,清理碎石,用铁锨挖出一个小坑,把那些枯萎的花放在里面,小雅边填土边轻轻唱:“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小雅的歌声凄婉、纯情、孤傲,还带着些许的清苦之味,扎心辣眼睛,我禁不住哭了。小雅也哭了。小雅说:“小楠,外公说未成年的孩子如果死了,只能埋在荒野里。将来我死了,就埋在这里。我自己选的,你看这里好吧,有山有水,阳光也好,还有这些花,以后我会再埋下一些花,我喜欢花,以前住楼房,养花总是不太方便,这下好,总算如我愿了。”
我哭着说:“小雅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好不好。”小雅泪眼婆娑地说:“好,好,不说这个了。来,我告诉你个秘密。”小雅拿出手机,打开相册,点开其中的一张,一个男孩阳光俊秀的脸微笑着看向我们。
“小楠,我喜欢这个男孩,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我俩一个班,但从没说过话。我生病住院后,他和同学们来医院看过我,这张照片是我偷拍的。住院的日子很痛苦,快要崩溃的时候我就看他的照片,就不那么难受了。小楠,你有喜欢的男孩吗?”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说:“小雅你咋竟乱说。”小雅咯咯笑了,说:“小楠你害羞什么啊,你这都进入青春期了,被男孩子喜欢和喜欢男孩子都是很正常的啊。”
桌上的花儿枯了,小雅就送来新的。望着花儿,我的心充满了忧伤。想到小雅也许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就会情不自禁地哭泣。
“你刘奶奶和小雅今后可怎么活啊……”奶奶扯起袖口不停地擦眼泪。
“怎么了?”我的心忽然无比慌乱。
“你刘爷爷跟着村里的人去给人家修屋想挣点钱好给小雅治病,谁知踩空了掉下来,摔了,听说很严重,恐怕不行了。”奶奶禁不住哭出声来。
“啊?!”我飞快向刘奶奶家跑去。
小雅呆愣愣地坐在门槛上,像个痴人,嘴里喃喃着:“都是我不好,我害了爸妈,又害了外公,是不是所有对我好的人,都会被我害了?”我抱住小雅说:“小雅,这不是你的错。”
小雅继续痴痴地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我的。爸爸是我的吗?妈妈是我的吗?可是他们像风一样,消失了。我是我的吗?也不是,你看,死亡在不远处朝我微笑……”
D
“小楠,我想进城找爸爸,你能陪我去吗?我觉得我身体越来越差了,我怕一个人出去要是突然晕倒了,没人管我。”我说:“行,我陪你去。”
下了公交车,我和小雅走在喧闹的市声里,我有些紧张,我从没进过城,从没见过像蚂蚁搬家般涌动的车流。小雅牵住我的手,说小楠你别怕,有我呢。小雅领着我七拐八拐,在一处四周围着篷布的门口停下来,小雅探头探脑往里看,一个满脸胡子的大叔走了出来:“看啥呢?这里是工地,小孩子,去别处玩。”
“我要找我爸爸,我爸爸在这里工作。”
“你爸爸在这里工作?他叫什么?”
“徐庶平。”
“徐庶平?他十多天前干活砸伤了脚,走了再也没见回来过。”
“走了?您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这个,我不知道。”
“叔叔,您帮我问问我爸爸要好的工友是否知道我爸爸的去向,好不好?求求您了,叔叔。”
胡子大叔犹豫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电话:“喂,黑子,徐庶平离开的时候跟你说去哪儿吗?哦,这样啊,我知道了。他女儿来找他。”胡子大叔把手机装回口袋里说:“你爸爸徐庶平走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只说回家养伤了。”
我和小雅沿着马路边茫然地走着。我说:“小雅,你爸爸是不是回你奶奶家了。”小雅说我奶奶和爷爷早就去世了。
“你说我爸爸能去哪儿呢?他的脚受伤了,能去哪儿呢?”小雅的眼里汪着一团泪。
“小雅,你可以给你爸爸打电话啊。”
“对啊,我怎么忘了。”小雅兴奋地跳了一下,眼里的泪也跳了一下,跳出了她的眼眶。
小雅拿着手机,拨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小雅生气地把手机扔在了路边的草地上。
“什么破手机,连电话都打不通。”
“怎么了?”我拾起手机,按了通话记录的第一个号码,重拨,传来的是一个温柔的女声:“您好,你拨打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我也真想把手机摔在地上,我看看小雅,忍住了。
“小雅,你最近是哪一天跟你爸爸联系的啊?”
“爸爸十多天没给我打电话了。那天爸爸在电话里对我说,让我好好听姥姥的话,还说外公走了,他现在要更努力挣钱才行。都是我不好,让亲人们都活得这么辛苦。爸爸的脚受伤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照顾他。”
小雅又领着我去了几个地方找了几个他爸爸以前的朋友,都说不知道他爸爸的消息。太阳已经偏西了,我说:“小雅咱们回去吧,再晚了就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小雅点了点头。一路上小雅靠在我的肩膀上,闭着眼睛无精打采,看上去很累的样子。我也有些累了,将头靠在座位靠背上迷糊。
一连几天,我没见到小雅。桌上的花儿都枯萎了,小雅还没送花来。我写完作业,去刘奶奶家看小雅。
小雅躺在床上睡着了。我悄悄退了出来。刘奶奶说,自打那天你俩从城里回来,小雅就病了,那天你俩走了不少路吧,小雅累着了。她这个病啊,不能累着。
“小楠,小楠。”小雅喊我。我进到屋里,小雅靠在床头坐着。“来,过来坐。”
我说:“小雅你感觉咋样了?”小雅说:“今天好多了。”小雅望着窗台上的花儿说:“花儿都枯萎了呢。”我起身把枯萎的花儿从瓶子里拿出来放进塑料袋里。我对小雅说:“明天我放学后去采花。”
小雅说:“小楠,我们把那些开得正好或是含苞待放的花儿摘回来是不是很残酷?花儿也是有生命的,如果我们不摘,它就能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们摘它等于缩短了它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杀手’?”我说:“小雅你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我说:“小雅,如果你是一朵花儿,希望被人摘回来养在瓶子里躲避風雨还是愿意在田野里忍受风吹日晒呢?”小雅说:“我要是一朵花儿,一定要开得热闹,落得迅疾。开得热闹,就是一开一大片,让人想采都无从下手;落得迅疾就是开够了,一眨眼就落了,让人来不及采摘。”小雅说完冲我做了一个鬼脸。
我勉强地笑笑说:“小雅我回去了。”小雅说:“小楠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说:“小雅,我们的音乐老师回家生孩子了,班主任说把音乐课改成语文和数学。同学们最喜欢音乐课呢,学习累了,音乐课一唱歌,立马满血复活。老师咋就不给我们再找个音乐老师呢,临时的也好啊。”
小雅“哦”了一声后,眉毛微微皱着,若有所思的样子。一会儿,小雅说:“小楠,你可不可以帮我问问你的班主任,看看我能不能当你们的代课音乐老师。”我一听,马上鼓起掌来。
班主任王老师说他一个人说了不算,但他会向校长汇报这个事儿。我把小雅的经历全跟班主任说了,我说:“老师,您就多替小雅说说,帮帮小雅吧。”王老师说:“我会尽力的,不过这事儿成不成得等校领导们研究后决定。”
小雅想当代课音乐老师是为了钱。她说她的一种救命药现在涨价了,她想趁自己现在还能做点事儿,挣些钱,减轻一点爸爸和外婆的负担。
小雅心想事成,成了我们的音乐老师。小雅说,我虽然是临时的,但我会尽我的能力做好的。
小雅领着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是《丁香花》,她曾对我说,如果有一天她死了,她多希望她喜欢的那个男孩在她的坟前为她唱这首歌啊,她一定能听得到。“就这样匆匆你走了/留给我一生牵挂/那坟前开满鲜花/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你看啊满山遍野/你还觉得孤单吗……”这首歌,我们唱得泪流满面。
E
小雅晕倒了。那天小雅说觉得浑身是劲儿,想教我们跳舞。跳着跳着,她忽然像一枚飘落的花瓣轻悠悠地跌到了地上。
王老师和我们三五个同学把小雅送到了镇医院。医生说小雅晕倒是因为贫血,她的病情有进一步加重的迹象,以后晕倒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王老师说:“小楠,你回去告诉小雅姥姥吧,医生说小雅得转到市里的医院去。”刘奶奶一听急坏了,放下手里正在择的菜到了医院。住院需要钱。小雅让我扶她去卫生间,她拿出手机给爸爸打电话,打了几次都没有接通,小雅说,爸爸好久没跟我联系了,他的电话已从“欠费停机”变成了“已停机”,爸爸真的不要我了。说着哭起来。我抱住小雅说小雅,还有我们呢。
王老师发动学校的同学和老师给小雅捐了些钱,与治疗费用还有些差距。王老师对小雅说:“要不,我把你的情况发到网上,众筹吧。”小雅说:“谢谢王老师,您让我想想。”
小雅要我留下来陪她,让其他人都回去。小雅说:“小楠,我不想让王老师把我的事情发到网上为我众筹治疗费。”我说:“为什么呢?王老师是帮你。”小雅说:“我知道王老师是真心实意地帮我。可我的事情发到网上,必定有人会问我爸爸妈妈为啥不管我,热心的网友也许会人肉搜索他们。”我说:“那样岂不更好,你就能找到你爸妈了。”小雅说:“不,一旦他们被暴露在大庭广之下,一定会遭人谩骂和唾弃,使他们处于尴尬和不堪的境地。那样他们会很难受。”我说:“你害怕他们难受,他们不管你,都没想过你难不难受。”小雅说:“他们是我的爸妈啊,我不想让他们难受,我的病已把他们拖累得够苦的了。”小雅望着窗外,忍着眼里的泪。
我说:“小雅,你恨你爸妈吗?”
小雅说:“说不恨是假的。我曾非常恨他们,特别是对妈妈。但现在,我对他们的恨已经渐渐消失了,我常常想,他们也是不幸的呢,含辛茹苦抚养我十几年,我却得了不治之症。他们难受的程度一定不比我少,甚至比我还要难受。我相信妈妈离开不是故意的,移植那天她没有出现,一定是有不可抗拒的因素阻止了她。妈妈那么疼我,她一定不会主动放弃我。有一次我发烧,爸爸没在家,妈妈背着我到医务室,输完液又把我背上楼。妈妈那么瘦小,我那时比她高也比她重。我现在只想他们能好好地活着。小楠,我想你能理解我的想法。”
“嗯,如果让我以不能与爸妈相见来换取他们生活的安好,我一定也愿意。”我牵住小雅的手说:“小雅,你真棒,我很佩服你。”
小雅病情稍稍平稳就要求出院。刘奶奶抹着眼泪说:“小雅你太懂事了,你越懂事我的心越疼得受不了。”
小雅说:“姥姥,我想村后那片花地毯了,待在医院里,我心里憋闷得很。”
风暖暖地吹着,不时送来布谷鸟的叫声,春天已经落幕。初夏的田野,野花们开得更欢了,红的、黄的、紫的、粉的、复合色的……像巧手的绣娘用五彩的丝线在绿色的绒布上绣出灿烂无穷。蜜蜂在花间飞来飞去,草丛里传来各种小虫的叫声,那些叫声高高低低,一会儿独唱,一会儿齐唱,不用指挥,也不需要歌谱,它们是天生的歌者。小雅說,这田野,多么清爽怡人啊。
我快要小升初了,功课紧张起来,有时候星期天也要加课。小雅说,小楠,你要好好备考,这阵子不要来看我了。我会好好的,等你考出一个漂亮的成绩。
F
考试终于结束了,我没回家先奔进了刘奶奶的家。小雅躺在床上,脸色越发地白了,连嘴唇都是白色的了,她看到我,想起身,却起了几次都没能坐起来。我把她扶起来,在她的身后垫上枕头让她半躺着。小雅说,小楠,你觉得考得怎么样。我答非所问地说:“小雅,你去医院吧,我整个暑假都可以陪你。”小雅摇摇头,说:“我不想去医院,在家你陪更好。”
小雅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连唱歌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天下了一阵雨,雨后天很快晴了,空气里飘散着泥土的芬芳,风很清爽,让人感觉舒坦。小雅的精神很好,让我扶她去院子里。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小雅说,小楠,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有你这个朋友,我很高兴。我说我也很高兴和你做朋友。
小雅对刘奶奶说:“姥姥,我忽然想吃东西。”
“你想吃什么?告诉姥姥。”
“我特别想吃雪糕。姥姥你买两支吧。”刘奶奶出了院门。
“小楠,我要走了,我快不行了。”我的眼泪唰一下淌了下来。我说:“小雅不会的,奶奶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小雅你要坚持。”
“小楠,你别哭,你看我都不哭。活着真好啊,如果我能活下去,我一定去和我暗恋的男孩表白,一定好好孝敬爸妈。”小雅闭着眼睛,气喘吁吁。我说小雅你别说了,歇歇。
“小楠,你能吻我一下吗?我还没被我爱的人吻过呢。”
我擦干眼泪,嘟起嘴唇轻轻地吻上小雅的嘴唇。小雅的嘴角微扬,露出纯美的笑意。
小雅的雪糕只吃了一半就停止了呼吸。
放寒假回家,走过刘奶奶家的大门口,再也看不到那个很瘦脸很白的女孩微笑着和我打招呼,眼泪不自觉地滴落。我向村后的山野走去。远远看见小雅的坟前站着一个人,走近,是个女人,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女人,拄着双拐。那女人回过头来,她满脸都是扭曲的疤痕,像经历了一场激烈火山运动后的纵横沟壑。女人看看我,嘴角动了动,没出声,拄着拐一步一挪地走了。
小雅坟上的野花野草都已枯萎了,在朔风的呼啸里发出一种无言但芬芳的清响,那清响一声接着一声,声声悦耳,似泉水叮咚泛着微澜,又似一个女孩浅浅的笑。
作者简介:王举芳,女,山东新泰人。新文体绝句小说倡导者。《山东文学》等杂志绝句小说专栏组稿编辑。自幼喜爱文学。2010年8月开始写作,已在《意林》原创版、《读者》《羊城晚报》《时代文学》等几百家报刊发表各类文章百万余字。多篇文章被选入各种文集、学生读本和年选版本以及设计成学生语文阅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