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野《夜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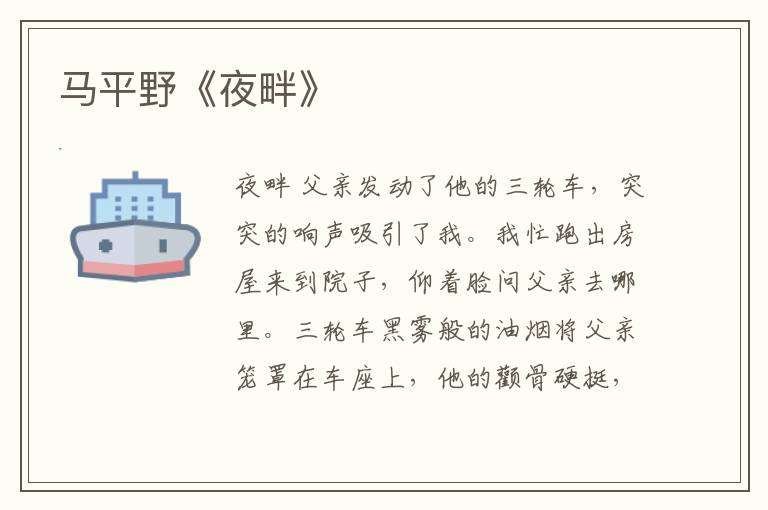
父亲发动了他的三轮车,突突的响声吸引了我。我忙跑出房屋来到院子,仰着脸问父亲去哪里。三轮车黑雾般的油烟将父亲笼罩在车座上,他的颧骨硬挺,点上一支烟,吐着烟圈看我。烟圈和油烟混合,继续笼罩着父亲。我与父亲相离咫尺,却被烟雾阻隔。
父亲将我放在他车座前部的空地,躯体前倾包围着我。我闻到了更刺鼻的油烟,还有熟悉的父亲身上的烟草味。三轮车突突响个不停,我震颤着。三轮车像猛兽冲上官道,父亲轻车熟路地驾驭他的猛兽。我仰起头,看到了父亲密密胡茬的下巴。
走,继续走。过官道绕村道,我不知道父亲要去哪里。我只管将手搭在车把上,迎着秋风,看着路上的车与人、路边的田与木。我丝亳不担心前方,三轮车有规律的突突声让我安定,时淡时浓的烟草味让我安定,偶尔一两粒烟灰从眼前洒落,也让我安定。不知走了多久,不知绕了多远,路边的风景没有变,无非绿烟树与绿田地。但我明显感觉离家远了。
父亲的三轮车停在了一个陌生村庄前的土路上。土路经秋雨淋湿又经秋阳曝晒,高处亮黄中部浅黄深处褐黄。土路两边,绿毯一样摊开的,是花生的叶子。父亲让我在三轮车上等待,他进了村庄。
父亲让我等,我便等。我呆呆地坐在车座上,父亲的余温尚在。我看父亲走向村庄,身影渐渐模糊,最后消失。我看天看地,又看花生的浓密的叶子在午后的秋风中翻动。没有声音,又有声音,那是远处的蛐蛐在弹琴。我等了很久很久,风吹了一遍又一遍,花生的叶子翻了一遍又一遍。远处的村庄不动,有几棵杨树像青烟,淡淡地悬在村庄上空。
父亲终于出现在土路尽头,我不再看向四处,乖乖地坐在车座上,等他回来。父亲近了,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女子,那个女子的怀中,是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父亲到了眼前,女子和婴孩也到了眼前。我忙从车座上下来,站在土路上,看着眼前人。我向父亲微笑,父亲也向我微笑,他的眼中有慈爱亦有歉意。我又向那女子笑,她也向我笑。我准备向女子怀中的婴孩笑,只是她怀中的婴孩正在吃奶,仅将小脑瓜对着我。
三轮车又发动了,女子抱着婴孩坐在车中的椅子上,我依旧坐在父亲车座的前部。油烟气随着秋风向车后飘去,父亲驾驶着三轮车原路返回。暮色渐渐重了,秋阳落入远处的村庄,天红色与地青色马上要闭合。凉意袭来,我瑟瑟抖了两下,仰头看父亲。他的颧骨成为高光,高光是夕阳余晖与大地墨色的融合。
我睡去了,矇眬中听到三轮车依稀的突突声,闻到花生叶子青冷的味道。父亲拔了路旁的花生放在车中,将外套脱下铺在花生软软的叶片上,我便睡在了绿叶与父亲的烟草味中。那个女子就坐在我身边,黑暗中,我又向她递去一个微笑。黑暗中,我也好像看到了她的微笑。
我又沉沉睡去,好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梦,青冷无边的漫长的梦。矇眬中,我又躺在了木床上。
这木床摇晃着颤抖着,吱吱呀呀,要喘不过气。这木床又像一只木船,摇荡在茫远的波涛或泥潭中。四下里全是黑,黑雾黑云黑水;四下里又全是热,热水热风热雾。这船又好像摇荡在无边无岸的虚空中,勾起我内心的焦躁、惊惶、无助。我想下船去,可是我却不能动弹,我死死地粘在了船底。父亲变成了这无边的黑暗,那个女子也变成了无边的黑暗,黑暗中又吵又闹。我浑身是汗,汗水好像洇湿了黑暗大地,蒸腾那满地的墨绿花生叶。我终于在晃动中坠下船去,坠入无穷尽的墨色的深渊。我开始哭,大声地哭。哭声惊醒一旁的婴孩儿,他也开始哭。哭声响彻了虚空,木船停止了晃动。
父亲满身是汗,抱着满身汗的我。他光着上身,敲响奶奶的房门。奶奶的灯亮了,父亲站在奶奶的昏黄灯光中。我模糊着双眼,叫着奶奶,奶奶冷着脸,看着父亲。父亲将我放在奶奶床上,扭头回了自己的院子。
清晨,我推开虚掩的大门,进了院子爬上三轮车。我记得三轮车上有父亲昨夜拔的花生。我坐在花生棵中的椅子上,不顾四处的露水,翻找着花生剥来吃。邻家奶奶登上房顶,问我昨夜家中是否来人,我朝她噘了噘嘴,继续吃我的花生。
我跑去问奶奶,新来的女子我该如何称呼。奶奶说:“叫姨吧,她带着孩子来,应该不会久留。”不叫妈,我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夜畔》发表于《东方新韵》202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