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的扬雄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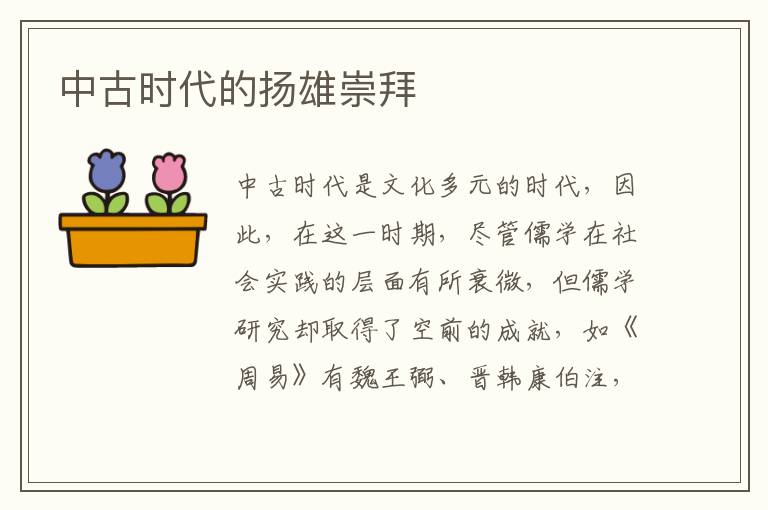
中古时代是文化多元的时代,因此,在这一时期,尽管儒学在社会实践的层面有所衰微,但儒学研究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周易》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左传》有晋杜预集解,《春秋谷梁传》有晋范宁集解,《尔雅》有晋郭璞注,《论语》有魏何晏集解等,这些著作上承两汉,下开唐宋,几乎占据了《十三经注疏》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见中古儒学的成就是很高的。人们通常尊奉的中古儒学式微的通行观点,实际是将儒学的社会实践与儒学自身混为一谈了。文化之多元来自文化信仰之多元。中古的士林精英,能够以纯理性纯文化纯学术的眼光和襟怀来审视和接受真正的伟人及其思想,这是其最为卓绝不俗之处。
除了孔、孟、老、庄,扬雄在中古时代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中古士人崇拜的文化巨人之一——被视为诞生在汉代的新圣,具有极高的文化地位。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二十四“齐楚圣人”条引桓谭《新论》:
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
张子侯与桓谭的对话表明,在东汉时代,他已经被视为和孔子一样的光耀华夏的圣人。汉王充《论衡·超奇篇》:
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窅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王公子问于桓君山以扬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诸子集成》,第七册,王充《论衡》,上海书店1986年版)
所谓“蹈孔子之迹”,“参贰圣之才”也是说扬雄乃是孔子以外的圣人,而桓谭则认为扬雄是独步于汉代的文化巨人。再如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三《吴失》第三十四:
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轲、扬雄,亦居困否。有德无时,有自来耳。(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称“扬子云齐圣广渊”,卷十上称“子云玄达,焕乎宏圣”,都是同样的意思。这些评价都是一致的。这里我们再以嵇康和陶渊明为例,进一步说明当时人们对扬雄的推尊。《世说新语·简傲》第3条: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儁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輟,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嵇康和钟会问答之语中的著名的“所字结构”本于《法言·渊骞》:
七十子之于仲尼也,日闻所不闻,见所不见,文章亦不足为矣。(汪荣宝《法言义疏》,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
在中古时期,扬雄的《法言》是驰誉学林的名著,所以嵇、钟二名士随口便可称引。《法言·问神》:“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李轨注:“童乌,子云之子也。仲尼悼颜渊苗而不秀,子云伤育童乌而不苗。”“颜渊弱冠而与仲尼言《易》,童乌九龄而与子云论《玄》。”(汪荣宝《法言义疏》,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童乌是中古时代著名的神童,他九岁就能和父亲扬雄讨论《太玄》的问题。这位神童引起了魏晋名士的广泛关注。嵇康《秋胡行》:“颜回短折,下及童乌。”(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上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嵇康对童乌的了解正来自《法言》,这可以为笔者关于“所字结构”渊源于《法言》的推测作一旁证。
陶渊明由晋入宋以后,更名为陶潜,前人对此多有解说(参见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之问题》,《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这实际也是受扬雄《法言》影响的结果。《法言·问神》:
或问“神”。曰:“心。”“请问之。”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敢问潜心于圣。”曰:“昔乎,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间耳。神在所潜而已矣。”(汪荣宝《法言义疏》,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
“神在所潜”就是陶潜之名的寓意。陶渊明不仅熟读《法言》,对《太玄》也极为谙熟。《连雨独饮》诗:“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天岂”句,古直注引扬雄《太玄·玄摛》:“近玄者玄亦近之,远玄者玄亦远之。譬若天,苍苍然在于东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无不在焉,及其俛,则不见也。天岂去人哉?人自去也。”(古直《陶靖节先生诗注》卷二,台湾广文书局1964年版)可见这四句陶诗不过是《太玄》此文的翻版而已。至于《饮酒》二十首其十八直接歌咏“子云性嗜酒”,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嵇康和陶潜对扬雄的推崇并非特例,扬雄作为魏晋玄学的祖师爷,其影响对中古士人是深入骨髓的。我们只有通过文本细读才能发现这种文化崇拜的痕迹。
作为汉代之新圣,扬雄的突出特征在于“尚智”,这是中古士林崇拜扬雄的首要原因。《法言·问明》:
或问:人何尚?曰:尚智。
所谓“智”,就是智慧,就是知识。在扬雄看来,追求知识和智慧是人的本质特征。知识就是美,智慧就是力量。他把“智”放在了高于儒家道德、仁义和礼仪的位置上,这是对传统儒学的重要突破。而扬雄一生的文化实践始终贯穿着“尚智”的理念,充分体现了柏拉图所说的那种“爱智的热情”,他是一个“为知识而知识”的人。《汉书·扬雄传》:
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括于势利乃知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班固《汉书》,第1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所谓“括于势利”“好古乐道”,“用心于内,不求于外”就是《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對此,我们可以引用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的话加以解释:“本真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贵族的事业,只有极少数人甘愿寂寞地选择了它。原初的求知欲是对人生而俱来的挑战,但仅仅依凭这种求知欲就不可能有科学的风险。……有史以来研究工作就不属于普通人所能从事的工作。一个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做一种内在需要时,才算是真正参与学术研究。”(《什么是教育》,邹进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对扬雄而言,“追求真理”是他一生最本真的“内在需要”。这与其纯洁的心灵和静穆的性格是相一致的。这是中古士人崇拜扬雄的第二个原因。扬雄的这种品格使他创造了不朽的学术辉煌。出于“爱智”的热情,他曾经对屈原的自杀深表惋惜。确实,如果屈原不自杀的话,以其《离骚》和《天问》所体现出来的科学文化修养从事于科学文化研究,也许就会成为我国先秦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而扬雄的清醒和冷静就在于,他珍惜自己的生命,为了从事学术研究必须留在宫廷之内,以获得和保持探求真理的必备条件,所以他不惜与王莽之流以及世间的俗人虚与委蛇,隐忍不发,毕生的勤奋与执着,使他成为我国中古时代的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其思想之深湛,涉猎之广博,精神之崇高,建树之卓越,求诸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史,殆罕其匹。扬雄一生,默然自守,辛勤耕耘,在文学、哲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天文学、地志学、谱牒学、诸子学和历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譬如,其所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为现代方言学与方言地理学开疆奠基,导夫先路,领先西方学术界一千多年,至近三百年成为我国学界之显学。其孤光独照与孤明先发,千载以下,仍然令人震撼。其所著《太玄》,更是旷世的奇书:“卓然示人远矣,旷然廓人大矣,渊然引人深矣,渺然绝人眇矣。”(《太玄·玄摛》)(司马光《太玄集注》,刘韶军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张衡“常耽好玄经”,曾经对崔瑗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传》)魏晋时代玄学的兴起和昌盛,证明了张衡的预言。而以司马光之博学,其于《太玄》也未能完全懂,故其文化密码尚有待于人们去研究去破解。在文学方面,扬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昭明文选》收录了他的《甘泉赋并序》、《羽猎赋并序》、《长杨赋并序》、《解嘲并序》、《赵充国颂》和《剧秦美新》等六篇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扬雄也给予极高的评价。杰出的学术成就和卓越的文化建树是中古士人崇拜扬雄的第三个原因。
扬雄生前是寂寞的,也是缺少知音的。《汉书·扬雄传》:
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巨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
在《文心雕龙·程器》中,刘勰列举“文士之疵”,称“扬雄嗜酒而少算”,意思是说扬雄爱酒而不善于为自己谋划,是其一病;而与扬雄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刘歆在看了《太玄》《法言》之后,说扬雄是徒劳无益,因为当时的学者大都以追逐“禄利”为第一要务,连《周易》都看不懂,更别说《太玄》了,所以担心后人会用这部名著去遮盖酱瓮。当时,对扬雄所知最深的是桓谭。在扬雄去世不久。桓谭对王邑和严尤说:“子尝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桓谭预言扬雄在未来可能会“度越诸子”(《汉书·扬雄传》),即超越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而西晋太康时期的著名诗人左思在《咏史》八首其四中对扬雄生前的生活和身后的辉煌进行了精彩的描写: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文选》卷二十一)
“济济”八句写新莽之际趋炎附势的世态和浮华的人心,“寂寂”六句写扬雄甘于寂寞,著述不辍,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了扬雄的高尚品格和人生追求,而以“悠悠”二句作结,将扬雄推上不朽的文化巅峰。也就是说,在新莽时代虚矫残酷的专制主义社会和人性的荒原中,在举国趋利、终日驰骛的世俗氛围中,在以读书做官为普遍追求的价值体系中,在“为官之拓落”,“位不过侍郎”,“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汉书·扬雄传》)的讥讽和嘲笑声中,扬雄以其寄情来世的远见卓识和清净自守的文化品格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但是,作为一位文化巨人,他的现实感和历史感都是很强的。在《解嘲》中,扬雄曾经激情澎湃地宣称:
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班固:《汉书》,第十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这是一代文化巨人的道德宣言和历史预言!扬雄对历史的预见和预判,完全被历史本身证实了。那些手握权柄、好人佞己、妄自尊大的王莽之流,早已在历史的秋风中烟消云散了,而扬子所创造的文化辉煌却永远垂范于后世,为华夏文明和人类文化增光添彩。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当秉持扬雄式的道德操守和文化品格。
扬雄的人格和思想以及文化建树,为中古士人彰显了一条无限宽广的文化道路,也指引了一条趋向永恒、垂声后世的人生道路。在扬雄辞世2000年的今日,扬雄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