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古诗的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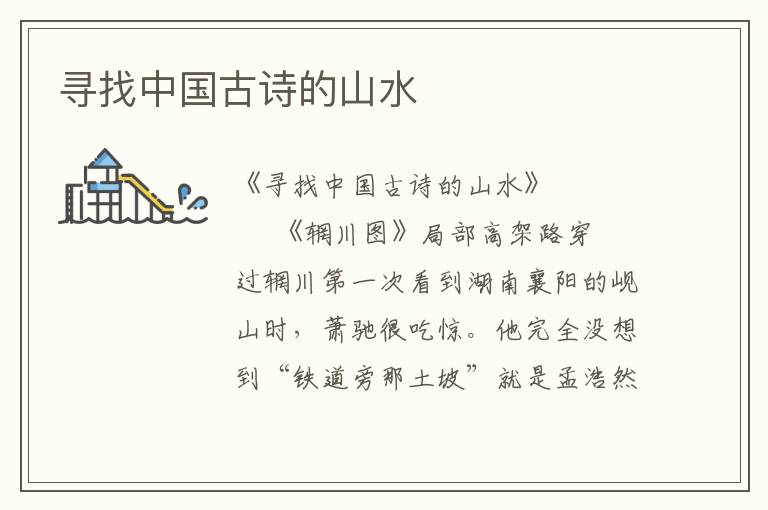
《寻找中国古诗的山水》
《辋川图》局部
高架路穿过辋川
第一次看到湖南襄阳的岘山时,萧驰很吃惊。他完全没想到“铁道旁那土坡”就是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所写的山峰,“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的景象似乎只存在于诗中,而不是他眼前所见的岘山。萧驰记得,古时,在汉江改造之前,岘山是人们送行的地方,许多诗人在这里送别友人,吟咏不舍之情。他想起汉学家宇文所安的那本《追忆》,里面第一章就写岘山“承担的名字太多了”,人们都想要在这片风景中占有一席之地:高风亮节的士子、情溢言表的墨客……如今,岘山周围盖了个“唐城”,它的身份更像是一个环境被破坏的影视基地和旅游场所。
岘山并不是萧驰第一次去的怀古之处。早在2010年,萧驰就去了浙江温州的永嘉县,走访了谢灵运诗中的白岸亭、绿嶂山等地。游历山水,对萧驰来说并不只是消遣,他的身份也不是单纯的背包客。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专注于中国诗学与思想史的研究。游历山水是为了学术研究,“需以文献和现地咨询去反复查证,才可能去重构当初诗人身处的实地山水”。
七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十次前往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王维、白居易等重要中古诗人的吟咏之地做实地考察。最终,他结合案头研究与户外考察,写出了新著《诗与它的山河》。
非虚构的中国山水诗
二十多年前,萧驰在美国留学时,曾随当地人经过一片空旷干燥、岩石裸露的群山。那时,美国人对此景象的赞叹令他感到惊讶,因为在萧驰的精神世界里,令人神往的山水之美应当是“高岑巑岏,云烟缭绕,屹立于大江之畔,或悬淌着瀑布湍流的山”,而非眼前所见之景。他开始想:所有民族皆对山野林泉有某种向往之情,却为何在许多更为具体的趣味和习俗上迥异?
带着这个问题,萧驰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山水书写,开始上路。出发之前,萧驰有个念头。他想梳理出从南北朝的“山水诗派开山人”谢灵运,到晚唐的杜甫等人诗歌中的山水书写的变化。
2010年,萧驰去了浙江中部和南部,开始了第一次实地考察。因为缺乏经验,萧驰事先不知道考察要准备什么,只是查好了诗歌中的地名,翻阅了相关地方志就上路了。
到了现场后,他发现沧海桑田,诗人笔下的山水世界早已是另一番模样。“不要说村子,山林和水都改变了很多,水(河流,湖泊等)很多是没有的了。”直到后来,他才逐渐摸清门道,明白考察前要去看当地做乡土文化工作的村民写的文章,也要向他们寻求帮助。
经过多年的跋山涉水,萧驰发现诗人们的山水书写和他们的经验相对应,即谢灵运开创的山水书写的“非虚构”特质。南朝宋武帝永初三年,谢灵运贬守永嘉,游历周围山水,多有吟咏,后人亦尊其为山水诗鼻祖。在这些诗作中,谢灵运以山水对仗的形式构建了一个澄净的山水世界,如“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山水交加,相映成趣。他将当地的风景写实地组织成诗作,呈现出源自山水的独特美感。萧驰到访谢灵运笔下的剡水、瓯江、南溪一带,发现汀渚于水中错落参差的曲线,正是谢灵运所写的如画风景。更甚是,谢灵运在永嘉、始宁书写的山水景观皆可寻获具体的地理参指方位。《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中的“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洲岛骤回合,圻案屡崩奔”等诗句,都是这一结论的最好佐证。
“考察是为了重建诗人和山水之间的互动,或者说对话。”萧驰说,“中国的(山水)诗歌都是‘非虚构’性的,它基于诗人自己的经验,如果它是虚构的,那你自己去考察就没有意义了。”
《诗与它的山河》
萧驰/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1月
¥ 120 . 00元
“这简直跟李白写的相差太远”
随着考察的继续深入,萧驰发现了山水书写的更多奇妙之处。第一次考察时,萧驰还去了《山居赋》中所写的石鼓山、白岸亭等地。晋朝时,这片地区尚有大片的处女林,郁郁葱葱。他想起谢灵运在《山居赋》中写道:“干合抱以隐岑,杪千仞而排虚,凌冈上而乔辣,荫涧下而扶疏。”茂密的林木出现在诗里,增添了喜人的绿意。然而,萧驰察觉到,谢灵运对森林的书写仅止于此——他并未去观察森林内部的四季,还忽略了天象、气象等因素。江南多雨雾天气,更何况是在那“缅邈水区”的剡水、瓯江等地。那被淡烟疏雨晕染的山水,在谢灵运的笔下全成了晴朗澄净的景象。
这几次行程,令萧驰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使这些山水书写是“非虚构”的,但也不意味着谢灵运等诗人给了读者一个全然的“客观的”世界。
带着这些观察,萧驰深入探究。他去了张家界天门山,发现李白用《望天门山》一诗“欺骗”了世人。“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中那两山对峙如门的画面,只存在于诗人的想象之中,现实是两山的体积与浩荡的大江完全不成比例,毫无雄伟之状。
“之前我看到一学者解读这首诗,说从诗的角度(李白)写得很好,但一到那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山和水相比太小了。”目睹了“真相”的萧驰,一开始异常失望,还打趣说自己都花了好多钱到那儿,没想到却被李白骗了,就连后世的地理书和方志都沿袭了李白的夸张。后来,他才逐渐释怀:“诗人实际上是一个审美主体,他不是一个照相机,他写的东西与摄影者拍的东西不一样。”
南朝文学家江淹爱写丹霞地貌,其中多渲染神仙道教气氛。《赤虹赋》里,“朱髻白毳之驾,方瞳一角之人”便是带有道家形象的仙人。儒释道似乎一直不曾在山水书写中缺席。“儒释道对山水书写的影响正好说明山水书写是不可能客观的,而是有一定思想和个人感情的诗人与山水的对话。”
曾经,有学生问他,能不能像他一样,用实地考察的方式完成博士论文。萧驰听罢,立马打住了他的念头:“你且慢,我是在做一种学术冒险,你做博士论文千万别这么干。”起初,萧驰对自己的研究并非信心满满,他怀疑自己的视野狭窄,只想着考察山涧、瀑布这些地貌。
一直到他在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人的“桃花源”里发现了山水书写的新天地。“桃花源是中古文学的重要母题,它不只是一个无可问津的乌有之乡,而是转化成一个愉悦有闲阶级的‘另一片天地’。”萧驰觉得豁然开朗,“我的视野范围逐渐扩大,路子越走越宽,后来感觉这些路子走对了”。
今古相接的一刻
萧驰进行第六次考察时,去了安徽南部的许多地方。他吃惊地发现,在皖南,凡是李白歌咏过的地方都造了亭子、祠堂等纪念性建筑。萧驰知道古人爱诗,却并不知道古人爱诗爱到“把诗刻到山水里”,即使这些连接古今的建筑,很多都早已变得残破,甚至不在了。
在湖南襄阳,萧驰去了孟浩然故居涧南园。据考察,涧南园旁边应该有一个园林水池的残迹,周围还有些石板、小路,而如今当萧驰亲自前往时,围绕在涧南园周围的,是污浊的水坑和成堆的垃圾。
与涧南园有着相同命运的,是孟浩然在《送张祥之房陵》一诗中吟咏的南渡头。六年前,萧驰经过一处渡口,觉得它很可能就是孟浩然当年送别友人的南渡头。那时,他还能感受到孟浩然那“我家南渡头,惯习野人舟”的闲适淡然。如今,南渡头也已不在,诗人的吟诵就此成了绝响。
岘山、涧南园、南渡头……被破坏的历史文化遗迹的名单,在萧驰的寻访之路上变得越来越长。他原以为这些曾被诗人书写过的山水大部分还在,没想到却大多遭受到了始料未及的破坏。人们似乎只关心寺庙、宫殿、城郭之类的历史文化遗迹,却并不了解这些地方的历史文化价值,也不会意识它们一旦被破坏,就再也不可能完全复原。
对诗人笔下的山水如数家珍的萧驰,时常为这一问题神伤,“(就算)恢复了也没有历史沧桑感,失去了原有价值”。
萧驰也不是没有见识过政府保护历史文化环境的举动,也有诸如谢灵运庄园、诸葛亮故居等被重视的历史文化遗迹,但在萧驰眼里,这些以发展旅游业为主要目的的保护项目,往往会破坏其原有的人文生态,弄得不伦不类。“如果在周围修建现代化的一些旅游设施,游人就再也无法体会到诸葛亮躬耕隆中的生活世界,不能去触摸历史了。”随着萧驰足迹的延伸,他不出意料地发现,这样的过度开发,只是现代化建设给山水带来的破坏中的冰山一角。
为了考察王维的山水书写,萧驰曾去过辋川。这一位于西安市蓝田县的小镇,曾是王维当年隐居的地方。在那首传诵极广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辋川是一个林木郁郁葱葱,炊烟袅袅升起的秀美之地,那“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的景象曾使王维倚杖于柴门外,在蝉叫中欣赏日落之美。而如今,高架桥穿过的辋川,未来可能出现的高铁轨道的辋川,似乎再也不会有昔日王维所见的美景。
“中国现代化建设速度非常快,传统的一些东西也消失得非常快。”萧驰为那些流传千年的山水扼腕叹息,“如果把它们全部从历史中抹掉的话,中国的现在跟过去就衔接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