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用“虚”(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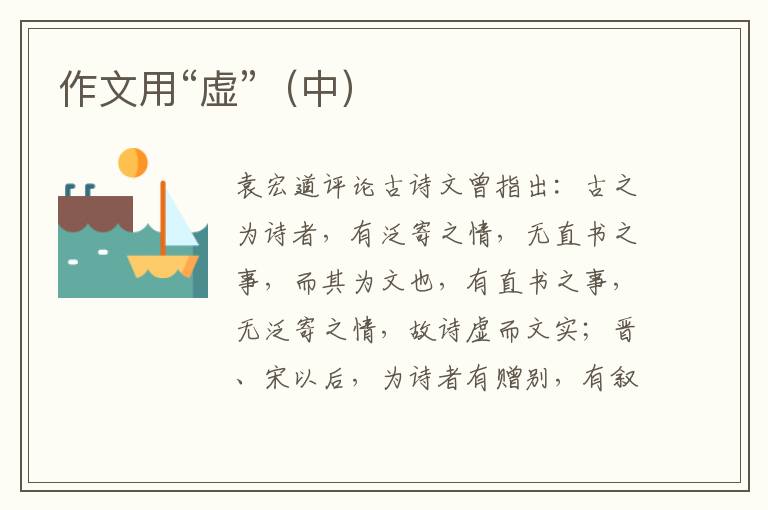
袁宏道评论古诗文曾指出: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宋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雪涛阁集序》)笔者在本刊以前刊载的《说“四六”》一文里曾说过,唐前的所谓“散文”,实际都是“应用文”,写作基本要求是陆机《文赋》里说的“辞达而理举”,所重视的是“辞达”即语言畅达和“理举”即内容清楚。同是明人的李邺嗣也说过:盖文自东汉而后,作者俱用实,而退之独用虚。(《王无畍先生七十序》)这是说韩愈的贡献,強调他能够用“虚”,和东汉以来的文字用“实”不同。上面两段话所述不完全不同,但同样表明写作有“虚”“实”之分,又同样讲唐前的文是写“实”的。至于袁宏道说古代的“诗虚”,是指它“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是说它“缘情”的特征,与本文讨论的“文”的“虚”“实”不是一回事,可另外讨论。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有这样一个论断,和上面说的文章的“虚”“实”有关系: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两大特长。(《中国文学论》)吉川所论显然限于古代文人的诗文,后起的小说、戏曲却不适用。他说的“重视非虚构素材”正是写作内容的“实”,而写“实”的文字要吸引人就得“重视语言表现技巧”。他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上面引用李邺嗣的话,说韩愈用“虚”。实则从文学发展看由注重写“实”到更多用“虚”乃是整体趋势。就“文”说,更充分地用“虚”确实是从韩、柳倡导“古文”开始的。
下面先举出几篇宋人的“记”,看看写“实”和用“虚”的例子。
依常识,“记”者,记事之文也。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里指出: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篇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为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学者以是求之,则必有以得之矣。这里讲的“记”这个写作体裁的“正”与“变”正和写法的“虚”与“实”有关系,又和中国古代散文文体发展有关系。
下面先来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按上引吴讷的说法,记营建,先要“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欧阳修完全合格,他是这样写的: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里写醉翁亭的创建,一步步由远及近,确定其位置;然后谁是写创建者、命名者;归结到命名的意义,完全是写实的。接下来三段描写,一段写醉翁亭四时的自然景致: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一段写人在亭的怡乐。以“滁人游”为陪衬,写“太守”即“醉翁”、作者自己在亭饮宴和作文缘起: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最后一段是吴讷所说的“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因为支持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被罪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次年建醉翁亭。作者在亭欣赏美景、寄情饮宴,抒写优游自得的情怀,流露进退荣辱不萦于怀的意念。写法上历来被人赞赏的是语气词“也”贯穿通篇的运用。费衮《梁溪漫志》评论说:文字中用语助太多,或令文气卑弱……然后之文人,多因难以见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有助语……其后欧阳公作《醉翁亭记》继之,又特尽纡徐不迫之态。二公固以为游戏,然非大手笔不能也。如就写法论,这篇文章,完全合乎本来的“记”的“正”体,表现手法则是“实”写。如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里评论的:文中之画。昔人读此文,谓如游幽泉邃石,入一层,才见一层。路不穷,兴亦不穷。读已,令人神骨翛然长往矣。此时文章中洞天也。所谓“文中之画”,意味着给人以具体的如画面一样的印象。这是写实的效果。
再来看另外两篇文章。
王禹偁于咸平元年(998)因为预修《太宗实录》,直言无忌得罪,罢知制诰,被贬出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市),次年作《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文章立意与《醉翁亭记》大体相同,也是通过记叙楼台风景来抒写贬谪中悠游放达的怀抱,而隐含获谴的不平。但是写法与欧阳修的步步写实不同。开头写作楼用竹,呼应题目“小竹楼”: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接着简单地写筑楼原委:“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榛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然后主要描绘憩息楼上的风光: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黙坐,销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这一段种种景致全然是虚拟的,是“小楼”主人即作者的想象,借以抒发心绪。最后举出四个古代楼台的典故:唐曹恭王建的齐云楼,三国东吴建的落星楼,汉武帝建的井干楼,三国魏曹操建的丽谯楼,以表明小竹楼所建乃“骚人之事”,点出抒写牢愁的意思。接着写自己屡经贬斥、坎坷不平的遭遇: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所谓“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指至道元年乙未(995)因为议论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葬礼,被罢免翰林学士等职,出知滁州;次年丙申改知扬州(今江苏扬州市),再次年丁酉被召还朝,担任刑部郎中、知制诰(“西掖”即中书省,刑部为其所属);然后咸平元年己亥来到黄州。简单地述说经过,牢骚不平意在言外。这样的写法全然是基于想象,立意也不在建楼或享受楼台的乐趣。这是“虚”写。
再看一篇,也是和黄州有关的。元丰二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贬黄州团练副使。应在元丰五年之前,友人张孟德(偓佺)亦贬谪黄州,在所居西南长江边上建亭,苏轼曾有词《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作》(《东坡乐府》卷上),中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句,因命亭曰“快哉”。苏辙受兄长牵连,在苏轼贬黄州同年末贬监筠州(今江西高安市)酒税,于元丰三年五月末赴贬所途中,曾携送苏轼家小到黄州,小住后离开。黄州与筠州相距不远,兄弟二人书信往还、诗词酬唱密切。快哉亭成,苏辙受托作记。苏辙到过黄州,赴筠州经过黄州赤壁也曾赋诗怀古,但快哉亭是后来建的,他不可能见到,所以比起王禹偁记小竹楼来,更要凭空用“虚”来书写。文章两段。第一段: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徳、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这是写亭所处形势和建亭与命名,连带写到附近黄州赤壁古迹。整体上是凭想象的风光。至于所述赤壁古迹,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一句表明的,不可落实为“赤壁之战”的赤壁。这一段算是写景,第二段则全然是议论: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这一段则是纯粹的议论了:先是用《文选》卷十三宋玉《风赋》典,说居上位者和一般人对事物感受的不同;然后一转,感受决定于内心的取向,进而赞扬贬谪中的张姓朋友能够不计得失,放情山水;接着再一转,说“骚人、思士”遇到良辰美景更“悲伤憔悴而不能胜”,从而对友人的遭遇表示同情,也是抒写对于世事的不平。
上面三篇文章,都是记亭台之盛,但写法有“虚”“实”的不同。大手笔写来,“虚”“实”从容自得,都会作出好文章。不过从散文发展角度看,用“虛”则有另外的意义,下面会集中说明。
用“虚”斡旋
笔者在本刊前面谈“古文运动”,谈韩愈的贡献。与论题相关联,下面讲韩愈的两篇文章,一篇和上面讲的同样是“记”,另一篇是“序”,看他是如何用“虚”的。
同样是“记”的是《新修滕王阁记》。元和十四年(819)初,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贬潮州(今广东潮州市),四月末抵贬所,在潮州住半年,遇赦量移袁州(今江西宜春市),次年二月到任。袁州为江西观察使所辖,这一年的六月,朝命王仲舒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九月,王与监军宦官和文武官员在滕王阁举行宴会,议决对楼阁加以整修。王仲舒是韩愈旧交,整修完工,王请韩愈作记。这一年九月朝命韩愈担任国子祭酒,十月离开袁州,文章是离开之前作的。
韩愈曾经三下江南。大历十三年(778),他跟随被贬官的韩会兄嫂赴韶州;贞元十九年(803),因为上疏议论朝政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加上贬潮州,三次往来都没有到南昌登滕王阁。因而如恽敬(1757—1817)所说:如《滕王阁记》,有王子安一篇在前……不可不避,故韩公通篇从未至滕王阁用意,笔墨皆烟云矣。(《与来卿》)比喻笔墨如“云烟”缭绕,正是形容全然是架空虚说,而通篇没有描写滕王阁。文章开头就写自己未至滕王阁的遗憾: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登临之美,而滕王阁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王勃《秋日登滕王阁饯别记》,王绪《赋》、王仲舒《修阁记》),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系官于朝,愿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阳,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其冬,以天子进大号,加恩区内,移刺袁州。袁于南昌为属邑,私喜幸自语,以为当得躬诣大府,受约束于下执事,及其无事且还,傥得一至其处,窃寄目偿所愿焉。然后写九月,王仲舒到任,政平人和,自己无缘到南昌晋谒,又没有到滕王阁的机会。然后写王仲舒举行宴会和修整滕王阁等情。最后写受命作记,表示“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辞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乃不辞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乐,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的希望。
这样,只是如何焯在《义门读书记》里所指出,这篇文章“切新修,切王公,切袁州刺史作记”。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抄》里又说:“通篇不及滕王阁中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澜。”这是典型的用“虚”斡旋的构思方法。
另一篇是《送石生序》。
“序”作为文体,传统上认为始于《诗经》的大序,延续到后来用来序文籍,就是今天著作的“序言”。《尔雅》说“序,绪也”,本意是次第有序,用在文章上则序事之文,后来主要是记赠送燕集。这种文体唐宋时期大兴,和当时士人生活、社会风气有关系。下面介绍韩愈的两篇文章是送行的燕集序。唐代贵族专制体制解体,庶族文人地位上升,这些人求举觅官、迁转黜骘等等,多有交际、奔走的机会。朋友送行,集会赋诗,要写一篇序,遂成为流行的文体。
韩愈的两篇文章是分别送友人温造、石洪应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之召前往赴任(河阳节度使治所在怀州,今河南沁阳市)朋友燕集写的。元和五年,乌重胤(761—827)担任昭义节度使(驻节邢州,今河北巨鹿县)卢从史的牙将。卢从史是骄横纵恣的藩帅,时密与叛乱的成德节度使(驻节镇州,今河北正定县)王承宗私相往来,反象日彰。乌重胤与监军宦官吐突承璀密谋缚从史帐下,以功授怀州刺史、河阳三城节度使。到任后他召请温造、石洪为从事。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国事衰败不振,地方权势大张。无论是割据的藩镇,还是据地自保的或拱卫中央的镇守,都要扩充实力。其办法之一就是笼络人才。而由于朝政腐败,国是日非,仕进道塞,奏请难行,许多士人不得不到各地州、镇求出路。如果翻一翻唐后期文人的传记,许多人都有担任幕僚的经历。韩愈本人年轻时就先后到宣武军节度使董晋(镇汴州,今河南开封市,贞元十二年至十五年,796—799)和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镇徐州,今江苏徐州市,贞元十五年至十六年,799—800)处做幕僚。如前所说,当时各地镇帅、州守对朝廷的态度不同,同样,那些“游幕”的士人情形也不相同。有真正才华杰出的,希望到地方施展抱负;有些徒有虚名的,为了求取个人私利。至于负固割据的藩镇招募无良的人士为助则属于狼狈为奸了。乌重胤在元和五年,就任河阳节度使甫三月,就到东都洛阳召请石洪。当时韩愈正在洛阳。元和四年,韩愈任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五年东,改河南令。这两位都是韩愈的朋友。乌重胤在镇帅里算是能够恭检自守的,又善于网罗人才。从现有资料看,石洪不算才华杰特的人物。但是从韩愈的一贯立场看,他是维护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对于方镇网罗人才当然抱怀疑乃至拒斥态度。写送序,依例要对聘任双方表庆幸之意,而要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寓于其中,十分难于措笔。韩愈巧妙构思,写出了文辞巧妙而又含义深微的文章。第一段,先写乌重胤礼聘缘由和友朋在洛阳上东门(外郭北侧东门)集会相送: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亊之贤者。有荐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间,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饭一盂、蔬一盘,人与之钱则辞。请与出游,未尝以事免。劝之仕,不应。坐一室,左右图书。与之语道理,辩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于人,其肯为某来邪?”从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垣,师环其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吾所处地,归输之途,治法征谋,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沐浴,戒行事,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上东门外。这一段主要是两问两答,四段话。问者乌重胤,言辞简略,但足以表现他好士、求士的诚恳;答者是无名的“从事”,一是夸赞石洪的人品、才华;再是写时下形势,聘任双方重义道合。这一段两番对答,写石洪受聘一事并表送别之意,并非纪实,全出于设想的虚构。第二段则是送别宴席上“执爵”者的四句祝词:酒三行,且起,有执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义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处何常?惟义之归,遂以为先生寿!”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无味于谄言,惟先生是听,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宠命!”又祝曰:“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这四句祝词用笔极其简练,四句各有深意,穿插着分别说乌重胤“以义取人”,石洪就聘是“惟义之归”,希望乌重胤能够坚持所守,石洪能够不图私利。这实则是以祝为议,以祝为讽。最后以再次表达与会者对聘任双方的期望,结以赋诗作序: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为歌诗六韵。退,愈为之序云。韩愈在这次集会上赋六韵的歌诗《送石处士赴河阳幕》:长把种树书,人云避世士。忽骑将军马,自号报恩子。风云入壮怀,泉石别幽耳。巨鹿师欲老,常山险犹恃。巨鹿,邢州也;常山,镇州也。元和四年,节度使王承宗反,诏中人吐突承璀以兵讨之,无功。五年,遂赦王承宗。镇州,今真定府。岂惟彼相忧,固是吾徒耻。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这里也是写“避世”的石洪本来隐逸“泉时”,受到镇帅召请却骑马招摇过市。巨鹿(今河北巨鹿县)指昭义节度使治所邢州,常山即王承宗盘踞的镇州。其时朝命诸军讨伐王承宗,师久无功,韩愈身为留守东都的一介小臣而感到羞耻,督促石洪有所作为。这首诗亦颂亦讽的意味更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