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柯《马哈勒米桥》东方文学名著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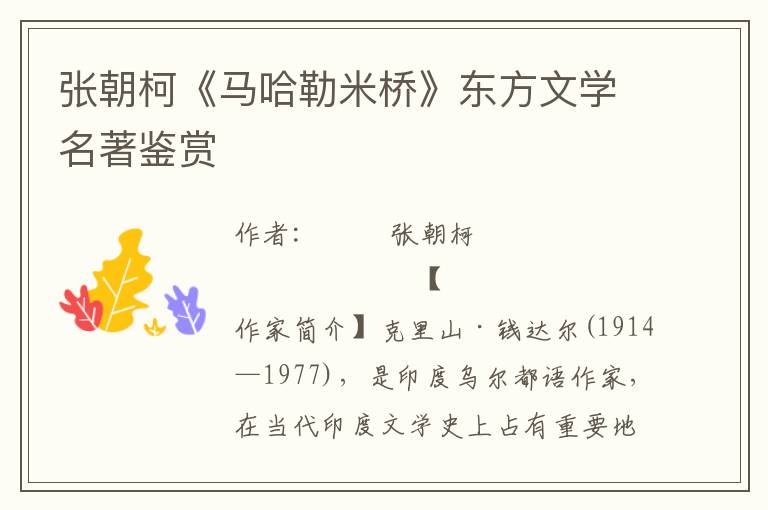
作者: 张朝柯
【作家简介】克里山·钱达尔(1914—1977),是印度乌尔都语作家,在当代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
他出生于一个印度教家庭,青少年时代是在克什米尔地区度过的,因为父亲在这里行医。曾先后在拉哈尔神学院、法学院和旁遮普大学读书,并获得文学硕士、法律学士的学位。一直关心社会政治运动,并积极参加旁遮普贱民协会的工作。从1939年到1943年,在全印广播电台任导演。后来,在电影公司从事编导工作;长期住在孟买。1977年逝世,终年63岁。
他一生创作的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各有30多部,短篇小说400余篇,还有几部中篇小说,对当代印度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主要成就,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共出版了22部短篇小说集。他被誉为印度的“短篇小说之王”,不仅深受印度人民的欢迎,而且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享有世界声誉。
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大约可分为3个阶段。
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是他的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大多以生活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为题材,写了许多动人的作品。如:《渔网》、《月圆之夜》、《奇特的想象》和《漫长的街道》等,都是代表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和理想主义的情调。
从40年代初到50年代初,是他的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时期,从浪漫主义开始转向现实主义。现实生活中的群众斗争和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成为他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屠杀事件为题材的《北夏华快车》、以劳动者悲惨生活为题材的《马哈勒米桥》、以孟买纺织工人大罢工为背景的《花是红的》等,都不再有浪漫主义色彩,全是现实主义杰作。
从50年代以后开始,直至逝世,算是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开始重视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注意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化,抨击帝国主义罪恶的作品,日益吸引读者。以西班牙人民反抗佛朗哥反动独裁统治为题材的《无花果》、以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为题材的《红心皇后》、《给一个死者的信》,都是代表作品。
《马哈勒米桥》,冯金辛译,选自《钱达尔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
【内容提要】过了马哈勒米桥,有一所很大的致富的庙堂,就是一般人称之为马场的。到这所庙堂里去朝拜的人们很少得利;他们往往输得一塌糊涂。就在这马场附近,有一条把脏东西排到城外去的大阳沟。庙堂涤净一个人心里的肮脏,阳沟则涤净一个人身上的肮脏。我们的马哈勒米桥便架在这二者之间。
左边,有六条纱丽在宽大的铁桥栏上迎风飘动。在桥的这头,就在这个地方,人们总看见这些挂在铁栏杆上的刚洗过的纱丽。这些纱丽,正像披它们的人一样,不很值钱。这些纱丽是挂在这儿叫太阳晾干的。每天,当市郊火车在桥下经过的时候,就看到这些纱丽在风里飘动……
这些纱丽,它们虽然是刚洗过的,看起来却很暗淡而死气沉沉。它们的颜色已经失了所有的光亮……现在,它们挂在栏杆上,显得这样的悲哀和忧郁。我从来没有看见它们快乐过或笑过……它们有好些地方已经破裂。若干处可以找到匆忙而马虎地用黑线缝起来的大补钉。好几处,缝线已经脱落。大多数的纱丽上都有着一大块一大块龌龊得永远洗不干净的补钉……
我知道这些纱丽的生活,因为我认识披它们的那些女人。她们住在桥旁的第八号工人大杂院……我对她们的生活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也住在那儿。你们愿意知道一些她们的事情吗?我知道你们是在等候总理的专车。可是专车还要过些时候才能到达。在这时候,从我这儿知道一些这六条纱丽的故事,也未为不可罢。
顶顶左边的那条纱丽是桑达·培的。她的生活的色彩是惨淡的、褐色的,就像她的纱丽一样。她是洗碟子的佣人,有三个孩子,最大的6岁。她丈夫在纱厂干活儿,一清早就得走;她得头天夜里把早饭做好,因为她比丈夫走得还早。她的小儿子还不足两岁,早已没牛奶吃了,牛奶很贵,只得靠玉米和冷水过活了。他们的饥饿随着他们的成长而增长。
第二条是杰瓦纳·培的纱丽,也是深褐色的;但比桑达·培的还要破烂得多,上边还有两块大补钉——是从前一条旧纱丽上弄下来的。她老是竭力想到过去的甜蜜回忆来弥补她目前的苦恼。这个寡妇总是怀念她的丈夫——有一次他大发酒疯而把她揍得那么凶以致她就此瞎了一只眼睛。她丈夫在纱厂里干了35年,因为老了,被开除了,不给津贴、年金和养老金。他觉得,在这35年的岁月中,好像被人取走了他身体里所有的水份,皮肤上所有的颜色,血管内所有的血液,然后像扔掉渣子似地把他扔了出来。杰瓦纳还生过一个女儿,跟人逃跑了。在丈夫死去时,杰瓦纳看见一个穿着亮晶晶绸衣服的气派浮华的姑娘,跪在她脚下像个孩子似地哭着。这时,她突然觉得,她生平直到现在一直认为可尊可贵的东西都完了,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她是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可耻可鄙了。
第三条纱丽,是我老婆的。我是一家公司的职员,月薪65卢比,和纱厂工人的工资一样。我有8个孩子,每月的薪水只能维持半个月,下半个月只有靠借高利贷来对付了。因为没有钱,不能让孩子去上学;来了电报,说我老婆的母亲快要死了,叫她去看看,可我筹不足钱给她买火车票。
第四条纱丽是紫红色的,拉太立亚的。她是谢巴的老婆,一个巫婆。我老婆不喜欢拉太立亚,因为她有妖法,因为她同谢巴没正式结婚。事实上她是谢巴不吸烟、不喝酒,用自己的积蓄买来的。一天,拉太立亚正在一边喂那只鹦鹉,一边唱歌给她听,突然看到受伤的谢巴给一个工人背回来。有的工人说:谢巴和纱厂经理吵了架,经理总是找他工作上的错儿,谢巴一直不吭声,那经理又骂了他,打了他。于是,谢巴痛快地揍了经理一顿。谢巴被经理雇用的打手打破了脑袋。不过他没有死。拉太立亚不得不去当一个菜贩,每天赚钱做家用和作丈夫的医药费。谢巴已经好了,可是再也不能到任何工厂了,因为他的名字上了厂主协会的黑名单。任何一个工厂都不肯用他。一个工人,只有挨打的权利,而没有回手的权利。
第五件纱丽是枣红色镶蓝边的,是曼犹刺的。她是一个年青的寡妇,她就是穿着这条纱丽结婚的,这是六个月前的事情了。曼犹刺才16岁,非常漂亮,因为是一个印度教徒,做了寡妇,就不能再嫁了。她丈夫是被松脱下来的皮轮筒套砸死的;工人几次申请换新的,厂主都不肯;因为新的皮轮筒套是要花钱买的,而一个新的工人却随时能找到。曼犹剌曾去申请抚恤,她一点也没得到。厂方说,那是因为她丈夫自己不小心。她要给自己买一条适合寡妇披的纱丽——一条白布的纱丽,可是她没有钱,所以只得披着做新娘时的服装来当寡妇。
那第六条纱丽,也是桥上最后一条,是鲜艳的深红色的。只是它不应再挂在那儿,因为披它的女人已经死了。这是老梅的纱丽,她是住在大杂院大门旁旷场上的,她是我们大杂院的清扫工,她的儿子西图也是一个清道夫。她是在这座门旁给杀死的。在清道夫罢工时,一颗子弹把她打死了。不,她可没有罢工;可是他儿子参加了,事实上他是领导这次罢工的。现在他的儿子被关在牢里……
对不起,我们总理的专车来了。我原以为它会在这儿停一会的。也许我们的总理会下车到站台上来待一会儿。望一望马哈勒米桥左边栏杆上的六条纱丽的。这些纱丽属于我国的最普通最平凡的妇女,属于成百万平凡的妇女。总理先生,这六条我国最平凡的妇女所披的纱丽想对您说几句话呢。它们希望从您那儿要到一点东西。可是它们并不要求大的东西,像一大块土地、大办公室、汽车……它们要求您的只是生活上的小事:桑达·培的纱丽要求童年时代的绮彩;杰瓦纳的纱丽要求一只光明的眼睛和女儿的名誉;我老婆的纱丽要求孩子的学费;拉太立亚,丈夫没工作,她的鹦鹉已经挨了两天饿了;“寡妇新娘”的纱丽要问问您,为什么一个皮套子的价钱要比她丈夫的生命还贵;老梅的红纱丽,只是要把子弹变为犁头,好叫人的鲜血能像金黄色的谷穗那样在地上开花!
可是总理先生的专车并不停在马哈勒米,所以他也就无从看见这六条纱丽。因此,亲爱的朋友,我就转向于你们了:我的弟兄的弟兄,我的邻居的邻居。我请你们转过头来,望一下那些挂在马哈勒米桥左边栏杆上的六条纱丽。我还请你们再掉头望一下那些挂在同一座桥的右边的绸纱丽。我亲爱的弟兄啊,望一望你们的右边和左边,然后问问自己你要走哪一条路吧。不,我不是要你们做一个共产党员。我不是让你们相信阶级斗争。我只是要从你们那儿知道一件事情:你们是站在马哈勒米桥的右边呢,还是左边呢?
【作品鉴赏】马哈勒米桥的左边栏杆上,挂着六条刚洗过的纱丽,短篇小说的开篇,便开宗明义地吸引读者注意这些纱丽。作家告诉读者“这些纱丽,正像它们的穿戴者们一样,不很值钱”,“看起来却很暗淡而死气沉沉。它们的颜色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光亮”;“它们挂在栏杆上,显得这样的悲哀和忧郁。我从来没有看见它们快乐过或是笑过”。
作家描写纱丽的“暗淡而死气沉沉”、“悲哀和忧郁”,正是为了要表现它们主人生活的凄惨:她们“生活的色彩是惨淡的、褐色的”。所以,作家直接地说出:“我知道这些纱丽的生活,因为我认识披它们的那些女人。她们住在桥旁的第八号工人大杂院”。这个大杂院——贫困的工人住宅区,也可以说是当代印度社会的一个缩影。
在这个大杂院里,每一个工人妻子的不幸,都表现了工厂主的罪恶,使人深切地体会到:工人群众的贫困、饥饿和死亡,正是长期遭受摧残和压榨的结果。从而,激发了人们对资本家、对残酷剥削的憎恶!桑达·培的丈夫是纱厂的工人,每天早出晚归,还维持不了全家的温饱,只好让妻子出去给人家洗碟子,甚至连6岁的大女孩也带去给人家洗碟子,还是维持不了最低的生活。丈夫买不起新衬衫,妻子买不起新纱丽。他们的孩子“睡着的时候肚子饿,醒来时他们肚子也饿”;“他们带着心灵上和肉体上的饥饿、靠着干面包和冷水成长起来,而他们的饥饿则随着他们的成长而增长。”
杰瓦纳·培是一个寡妇,她的丈夫给纱厂干了35年活,棉纱的纤维进入了肺脏,每逢雨季就气喘得要命,不停地咳而又咳,“而最后他的咳嗽变成了一阵长而可怕的号叫,这叫声对纱厂经理犹似警钟一样”,找一个小小的借口把他开除了。“不给津贴,不给年金、不给养老金的开除了”,6个月后,他就死了。
“我”——公司职员的妻子,也买不起新纱丽。我虽然是大学肄业生、能打字、会讲英语;但也还是维持不了8个孩子的家庭生活。
在纱厂里,老实的工人,任劳任怨的工人没有活路;有一点反抗的更没有活路。拉太立亚的丈夫,就是因为同经理吵了架,而遭到报复,被打破了脑袋,再也不许进任何工厂的大门。
工人们实在是忍受不住了,清道夫们进行了罢工斗争。结果,母亲被子弹打死,儿子被关在牢里。
作家通过这些事例,揭示了工厂主的罪恶;但是,谁能拯救工人呢?作家希望得到政府的注意;希望总理的专车在路过时,停一下,“望一眼马哈勒米桥左边栏杆上挂着的六条纱丽”。“可是总理的专车并不停在马哈勒米,所以他也就无从看见这六条纱丽”。这表明:工厂主的罪恶、工人的悲惨处境,政府是不闻不问的。作家向人们暗示: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站在工人群众一边,展开斗争,改变这个万恶的社会制度。尽管作家说:“不,我不是要你们做一个共产党员。我不是要你们相信阶级斗争。”作品在最后,作家问道:“我亲爱的弟兄啊,望一望你们的右边和左边,然后问问自己你要走哪一条路吧。”作家自己早就给读者作出了暗示:他和妻子孩子们都是大杂院的成员,列入了桥的左边。这就是一个明确的号召:愿所有的人都站到工人一边,人民一边,以改变黑暗的现实。
钱达尔一生的创作成就,主要反映在短篇小说上,因而被誉为印度“短篇小说之王”。他的艺术技巧,也同样反映在这一短篇小说中。首先,作家善于运用象征的手法揭示现实生活,使人感到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用退色的失去光亮的、褐色或深褐色的纱丽,象征劳动者生活的惨淡、穷困和悲哀;用桥的左边象征着革命的动力,用桥的左边,象征工人群众、贫穷的人民大众;用总理的专车象征政府或政府官员。其次,作家往往采取对比描写的手法,展示人物形象的变化:曼犹剌没有钱,买不起适合寡妇披的纱丽。作家写道:“她即使是寡妇,也只得每天披着这条镶着丝光蓝边的正式新娘子的纱丽,但寡妇是不能披这样的纱丽的啊”。再次,作家往往采用“卒章显其志”的手法,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作家往往像画龙点睛一样地突出地表现作家的创作意图。在作品的结尾处,作家向读者问道:“你们是站在马哈米勒桥的右边呢,还是左边呢?”作家由衷地希望所有的人都来同情、支持马哈勒米桥左边的纱厂工人、劳动群众,为他们去献身、去奋斗,让印度有一个永远光明的未来,让工人的妻子们能披上鲜艳夺目的崭新的纱丽。








